意象图式下古诗词的指称转喻研究论文
2024-01-12 09:10:33 来源: 作者:liyuan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擅长借景抒情,而认知诗学的出现为中国古典诗歌分析开辟了新视角。文章尝试把意象图式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鉴赏中,结合笔者自身经验,从不同角度探索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图式的认知关系,以便形成新的认知图式,从指称转喻出发解读古诗以求精确领悟诗词大意和作者意图,从而把握诗歌主题。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擅长借景抒情,而认知诗学的出现为中国古典诗歌分析开辟了新视角。文章尝试把意象图式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鉴赏中,结合笔者自身经验,从不同角度探索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图式的认知关系,以便形成新的认知图式,从指称转喻出发解读古诗以求精确领悟诗词大意和作者意图,从而把握诗歌主题。
关键词:指称转喻;意象图式;诗歌
Abstract: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s proficient in lyricism with scene,while cognitive poetics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e image schema theory to appreciat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combined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connection of the image schema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in order to form a new cognitive schema,to interpret the reference metonymy in poetry,to achie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poetry and poet’s aims,so as to grasp the theme of poetry.
Key words:referential metonymy;image schema theory;poetry
一、引言
近年来,认知框架下的转喻研究逐年增多。认知语言学视角是学者对转喻修辞功能进行解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诸多学者基于这一视角指出转喻的反复使用会影响这种辞格的修辞效力[8]。人类认识世界需要借助转喻,是人类发展的结果,认识现实世界事物的需要。人的大脑凭借对现存事物的存在形式去理解新事物,这不仅是人脑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人类认知转喻能力发展的成果。读者对诗歌解读的前提是具备转喻认知能力,有助于读者储存、记忆以及表达交际信息,进而为解读及赏析诗词提供一些参照。
二、指称转喻
转喻是同一认知结构空间的概念反映,这是Lakoff&Turner的观点,转喻是一种“代表”关系,其主要功能是指称,且对词汇层面的转喻修辞研究则尤为频繁[4]。不同事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时,可用事物名称代指所说的事物,这在古代修辞学理论中也可称为借代,相当于英语的转喻修辞。
Panther&Thomburg将转喻分为三类:首先是指称转喻,人们行动和思考都离不开它,在三者中使用最为频繁;而述谓转喻和言语行为转喻则比较少见。他二人不仅延伸了转喻的领域,而且促使了转喻多层面性的问世[6]。汪榕培等开展了指称转喻的相关研究[7][9],基于学者的研究,可知指称转喻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转为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认知思维方式。
三、图式理论与指称转喻
“图式”经过了数代心理学者和认知学者的不断探索与延伸,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希腊语。之后,当代认知科学将图式理论推向其他领域,并催化了“认知图式”的诞生。此外,认知图式这一认知结构是人们头脑得以反映真实世界的抽象工具,而背景常识信息对图式的构建意义非凡。
Fillmore[1],Johnson[3]等认知研究者曾讨论认知视角下的图式,且造诣颇深。在他们看来,大脑具备储存和解决信息知识的功能,如此图式便可将脑海的各种意象串联起来并与陌生新事物通过转换融合形成新的信息知识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依赖大脑固有图式协助人类完成生活中的各项新事物活动[10]。
意象图式这一概念结构形式是认知语义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意象图式在诗文中被视作诗人自身感受和外在世界想象力的集合,字面上就是“意义”和“想象”的组合体。意象是诗人借助身体感官和脑海想象力而产出的抽象空间产物,这些通过感官和情感可以被人类所感知。诗歌意象的功能是在人的多种感觉器官的碰撞下,辅以图式的帮助,牵引出了某种感情色彩,指引读者通过图式和外部世界体验的合力进入诗歌营造的情境之中,沉醉于独特的诗歌意境。诗歌意境基于读者感官和想象力而形成了诗句语言呈现的场景,这样的奇妙状态便是在图式和个体想象力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使读者易于理解诗歌升华后的人生哲理,这便是诗歌意象和图式结合而产生的魅力所在。
文章基于指称转喻在认知图式理论的研究,将认知图式作为读者反映认识诗歌意象和文本的空间结构,也是读者在诗歌中识别各种自然意象和理解诗人情趣志向的基础。在认知图式的指导下,人们可以尽情发挥脑海中的想象,构造生动的情景画面,引发无尽联想,易于解读诗人在诗歌中所寄托的情感或是哲理人生。读者对诗歌意象的解读和联想离不开认知图式,二者是密切联系的。读者作为诗歌解读过程中的认知主体在自身感官和想象力的协助下试图在源图式(即自然界具体直观的事物)与目标图式(抽象的思绪情感)之间建立“关联”。作者从意象图式着手对指称转喻再一次解读;而图式在修辞学的应用研究对指称转喻而言是新的突破,是建立在认知图式基础之上的反映。人类在认识世界,传递体验的过程中,指称转喻是人与世界交流的媒介,而且和转喻词语的关系十分密切,指称转喻的投射过程等同于转喻的理解流程。目前,用具体的语言词汇本义来呈现人类抽象的体验是指称转喻的研究前景。
认知图式的出现拓宽了转喻的研究广度,学者将指称转喻吸纳并且融入新的学术应用研究中,认知图式的贡献不容忽视。人们在生活中认识客观世界并表达自我情感离不开认知图式空间模型;不仅能将大脑中相关背景知识适时呈现,而且还可将脑海中无关的表象拒之脑外。图式理解过程被Gibbs将之概括为识别、理解、阐释和鉴赏四个部分[2]。同时,读者在诗歌赏析时也避不开这四步。因此,诗词意象解读需要对各类转喻指称项进行鉴别,即对所要鉴别客体的类型进行验证。指称转喻项就是具备比喻修辞意义词语,这些词语仅充当转喻客体媒介,并没有特殊标签,转喻本体词语在诗词中的语言运用同认知图式空间结构有联系。认知主体即便作为文本词汇指称转喻运用判断的负责人,也要借助大脑认知图式信息才可识别文本中是否存在指称转喻的词汇。读者在诗词赏析中对指称转喻的识别、理解、阐释和鉴赏需要依赖诗词文本中的词汇、文本图式乃至读者本身的个人知识图式、文化和社会图式。指称转喻在读者赏析诗词时的投射过程可以诠释为,在读者的图式背景知识和诗词文本转喻词在读者头脑中引发的词汇图式的结合下,读者脑海中生成了新的文本图式,从而理解了文本的指称转喻,进而掌握了感知和体验外界世界的新图式,加深了对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理解。
四、诗歌中的指称转喻
丰富的意象是诗歌的一大语言特色,而诗词意象中的指称转喻词汇解读离不开认知图式的帮助。此外,读者赏析诗词需要想象力和感官经验图式去构建生动形象的画面感;同时,指称转喻和意象图式的结合开辟了诗词鉴赏的新视角。因此,文章基于意象图式视角,赏析古诗词中的其中两首,即《钱塘湖春行》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意象,从新视角去诠释古诗词的独特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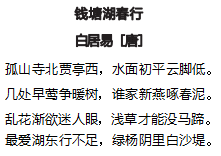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白居易在钱塘湖游历时所著,寥寥几句便将西湖春日之美景形象生动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诗人始于孤山寺庙之北的贾亭,辗转到西湖之东、白堤;诗人饱览了一路上所闻所见所听的湖光山色、莺歌燕舞之景;最终方才意犹阑珊地朝着白沙堤,杨柳树荫下离去。事后,作者回想起这西湖自然万物所呈现的画面感跃然纸上,脑海中的画面浮现,下意识地创作出这首承载着自然美景融合之趣的佳作。
《钱塘湖春行》全诗语言浅显易懂,意象朴实自然。Langacker曾指出,我们掌握的背景知识体系可看作是一个由概念组成的彼此关联的网络,词汇则是整个百科知识网络的交点、意义建构的起点[5]。诗的首联以写湖水为主,前一句借助几个地名指出钱塘湖的方位所在及其周边景观;后一句侧重湖光水色:水面与湖岸齐平,空中时卷时舒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相连,正是江南水天相接之奇景所在。本诗可以用前后意象和上下图式来分析的写景诗。前一句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意象由远及近,重点在于借助西湖周边景象来凸显西湖的地理位置;而后一句“湖面”和“白云”,上下意象图式则是一上一下,旨在呈现云水相接之景。这些简单的自然意象为后几联的情感交汇交代背景。因此,读者必须了解春日里这些自然万物的背景知识,即“图式”,才能将诗词中的转喻词意象图式与他们已有的经验图式知识相结合,并将源图式中西湖的“云水交接”和早春“莺歌燕舞”投射传输到目标图式“万物复苏,春日美好”的和谐气氛上来。这就意味着读者不能孤立地理解某些词汇的含义,否则将会桎梏他们借助自身的体验、背景知识记忆对转喻词汇新图式的构建。
颔联由静到动,先描写仰视的莺歌燕舞,着力刻画春日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信使,莺声婉转且燕子辛劳,向人们传递着春天来临的喜讯,初春的生机随处可见。诗中的“早莺”“新燕”和“春泥”这些意象皆是春日里的标志象征物。这些意象词汇烘托出了诗人对春天自然万物的喜爱之期。颔联从仰视的角度写了莺歌燕舞,而颈联则从俯视描写湖边花草。诗人看见湖岸这山花烂漫,青青绿草,心中的欢喜畅快之情呼之欲出,这些简单直观的自然景物瞬间成为诗人的精神寄托,读到此处,读者亦不觉受到感染。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莺燕燕嬉戏玩耍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来描绘花草欣欣向荣的朝气。尾联寥寥几笔写诗人喜爱的湖东白沙堤。绿杨树荫下,长长的白沙堤静卧在湖边,岸上骑马踏青的人络绎不绝,尽情享受春日美景。
诗人构建了春暖花开、莺歌燕舞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空间图式背景,同时构造欢快自然的诗歌意象。通过前后意象图式和上下意象图式的展示,读者可以更好地领悟诗人对这西湖的湖光山色的喜爱。读者赏析诗人情感态度的关键离不开“早莺”“新燕”“春泥”“乱花”“浅草”和“马蹄”这几组转喻词语。当读者难以从字面意义理解这几组转喻词语时,就必须借助其认知图式,经过细细推理后才能正确理解诗词文本的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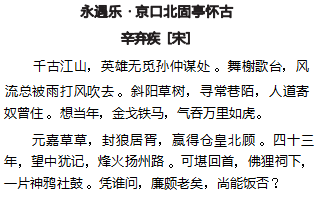
这首宋词的“孙仲谋”“寄奴”“元嘉”“封狼居胥”和“佛理祠”等意象指称转喻词是理解词人豪迈悲壮之情,渴望建功立业,保家卫国,收复河山,而又报国无门的无奈愤懑。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后,登临北固亭,感叹报国无门,凭高望远,感古怀今,于是写下了这篇传唱千古之作。
“孙仲谋”“封狼居胥”“廉颇”在读者背景知识中的源图式皆为“历史名人典故”,再结合全文通篇的“千古江山”“金戈铁马”和“烽火”等战场气息浓厚的指称意象词,读者不难构建出作者“保家卫国,收复河山希冀”的目标认知图式。这些简单的词语读者易于理解,但是要达到目标图式中的典故人物具备的情感意图,则要求读者利用头脑中的各种意象图式背景知识,对指称转喻词语的新的意义进行动态构建,如此方能真正解读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态度。
这首词开篇借景抒情,由眼前之景联想到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渴望如他们一般建立不朽的功绩。接着对主政者韩侂胄的讽刺,嘲讽其如刘义隆一般不堪大用,对挥师北伐前景的担忧。再想起如今朝廷不再起用年迈的自己,不禁仰天叹息。其中“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则是对北方宋朝国土难以收复的感慨。词的上阕怀念孙权、刘裕。孙权建立东吴大业;刘裕金戈铁马,东征西战,收复失地。不仅讴歌了历史人物的功绩,也表达了对南宋朝廷不思进取的嘲讽和谴责。下阕引用南朝刘义隆草率北伐,大败而归的历史,意在告诫韩侂胄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鲁莽从事;接着用抗金四十三年局势的变化,表达词人收复河山的毅力,结尾以廉颇自比,抒发出作者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和朝廷不能进用人才的慨叹愤懑。
五、结语
中国古典诗歌除了从文学和修辞学角度鉴赏外,还可运用意象图式理论进行赏析。由于诗词具有凝练概括的语言特点,而意象图式有助于读者领悟抽象思维概念和新领域;而诗词的意象图式是由诗人身体感知经验与客观理性知识的辩证统一。
因此,意象图式理论可以更好地把诗词中各个意象的指称转喻词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帮助读者更好地赏析中国古典诗词,并且读者可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去感悟蕴含在诗的意象中的情感。此外,读者在意象图式理论的辅助下,结合自身背景经验知识足以解读诗词中的意象,进而把握诗歌内涵。
参考文献:
[1]Fillmore C J.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In R.W.C ole(ed.),C 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
[2]Gibbs R W.The P oetics of Mind:Figurative Thought,Language,and Understanding[M].C am⁃bridge:C 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16.
[3]Johnson M.The B ody in the Mind:The B 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Lon⁃don,1987.
[4]Lakoff G,Turner M.More Than C ool Reasons:A Guide to P oetic M etaphor[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ress,1989:5.
[5]Langacker R W.Foundations of C ognitive Grammar:Theoretical P rerequisites[M].Stanford,C 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Panther K U,Thomburg L.The potentiality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 nglish and Hungarian[C]∥Panther,K and Radden,G.M 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s B enj amins,1999:333-357.
[7]汪榕培,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8]王军.再论转喻的修辞功能[J].外语教学,2011(3):5-9.
[9]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88-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