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阐释学视角下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原因论文
2024-09-27 15:21:00 来源: 作者:liziwei
摘要:一直以来,人们对译者持有偏见,认为翻译等同于背叛和不忠,即使在传统译论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会过度强调译文对原作的重现度,认为创造性叛逆会破坏原作意义的传达。本文基于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以译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创造性叛逆出现的原因,以期减少大众对译者的误会、增加其对译作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为译者和创造性叛逆正名。
[摘要]一直以来,人们对译者持有偏见,认为翻译等同于背叛和不忠,即使在传统译论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会过度强调译文对原作的重现度,认为创造性叛逆会破坏原作意义的传达。本文基于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以译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创造性叛逆出现的原因,以期减少大众对译者的误会、增加其对译作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为译者和创造性叛逆正名。
[关键词]阐释学;创造性叛逆;原因
1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译者在跨国交际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翻译一直备受质疑,“创造性叛逆”也未能幸免。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皮卡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比较文学界,后引入翻译学领域并不断发展壮大。
有的学者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一种有助于译者突破文化差异、建立读者和译文之间联系、实现原作再创作的翻译手段和策略。有的学者认为译者通过创造性叛逆产出的译作是对原作的背离,不符合翻译实践的标准(谢天振,2012)。
谢天振(2012)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中性词,并无明确的褒贬含义,以上种种理解其实是在中文语境中衍生出来的,而且创造性叛逆并非理论指导,只是一种客观描述。本质上,翻译过程就是解释过程,这与伽达默尔阐释学相吻合。本文以伽达默尔阐释学为基础,从译者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2伽达默尔阐释学三原则
瑞士语言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被誉为现代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阐释学的理论框架。阐释学又称解释学、诠释学,是一种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哲学方法和理论,主要探究人对文本、语言以及世界的理解方式,强调理解并非只是简单地获悉客体意义,还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等其他因素。伽达默尔阐释学从哲学视角提出了三个关键性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以及效果历史,共同构成了他对理解过程的独特见解。
阐释学强调,人对文本和语言的理解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所在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制约,理解者的视域会与文本作者的视域之间出现融合,而且文本对于每次理解和诠释具有效果历史(Gadamer,1975)。伽达默尔阐释学促进了翻译由侧重原作到重视译者主体性的转向,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基础。
2.1理解的历史性
哲学上,一切都是历史的,人必然处在一定的历史传统之中,会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带着自己以往的经验、意识和思想结构去理解文本。因此,理解绝不是简单、客观地理解文本与事物等其他客体意义,而是历史、文化等一切交织融合形成的自我与作者相互碰撞进而产生意义的过程。正如勒菲维尔(Lefevere,1992:14)所言,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因此,理解的历史性强调理解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过程。
2.2视域融合
视域是指一个人的理解框架,因此,视域融合是指在理解过程中,阅读者理解框架与作者的理解框架进行融合。这一思想与创造性叛逆相吻合,创造性叛逆起初是用来描述读者在阅读原作时会产生不同于作者所表达的甚至是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想到的思想情感(埃斯卡皮,1987:112)。受特定环境影响,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视域之中,因此人们尝试理解一个文本时,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先入之见和偏见进入原作的视域之内,在无法完全摆脱自身先见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视域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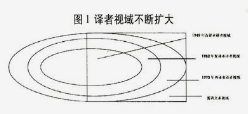
2.3效果历史
效果历史强调理解不仅是对过去的再现,还是当下重新构建意义的过程。简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多方面的影响,这包括读者对原作产生不同的理解、情感反应和文化认同。对每个人而言,文本都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对文本或艺术品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张德让,2001)。这意味着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解读,这使得理解过程成为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
伽达默尔阐释学三大哲学原则为解释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审视译文优劣提供了新的角度,除了经典的翻译标准外,人们还要考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因此,深入剖析伽达默尔阐释学三原则有助于各界人士对译文以及创造性叛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对重新定位创造性叛逆以及审视译者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3译者创造性叛逆出现的原因
3.1理解的历史性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影响
译者和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受到历史状况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会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从而决定了理解性差异。
以《红楼梦》中“世人都晓神仙好”这句话的不同英译为例。杨宪益等(2021)的译文为“All men 1ong to be immortals.”,Hawkes(2014)的译文为“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杨宪益等将“神仙”译成immortals,是受中国道教“长生不老”文化的影响;而Hawkes将之翻译为salvation,这和深植于其思想中的基XX文化有很大关系。
再比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的译文是“君子协定”而非“绅士协定”,这是因为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君子”,西方文化中的“绅士”。另外,castles in the air被译为“空中楼阁”要比“空中城堡”更合适。因为城堡是西方建筑特色,而中国建筑是偏古风古韵的楼和阁。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历史性文化偏见的限制,产生了不拘泥于词对词翻译的叛逆现象。埃斯卡皮(1987:137)曾言,“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因此,原作在转换成译作时必然会受到陌生参照体系的影响,跨越时空的思维碰撞注定译者无法摆脱理解的历史性影响,译作必然会发生创造性叛逆。不过,这种叛逆却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真实含义,使其更易为读者所理解,因此读者更应该体会到这是形式上的叛逆、意义上的忠实。
3.2视域融合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影响
无论是人还是文本,其存在都具有历史性,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带着自己的前见从当下的情景出发和文本的“视域”相触碰,去把握文本的意义,从而发生解释者的视域、文本的视域和当下情景的视域相融合的景象(谢飘飘,2022)。但是,由于译者和作者所受到的当下环境的影响不同,自我视域有差异,因此双方理解事物的框架存在无法相融的部分。
以《圣经》的翻译为例。《圣经》是基xx的经典,对西方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圣经》,其译本层出不穷。然而,由于不同时代背景下译者的视角与原作视角的融合与碰撞,每个翻译版本都呈现出创造性叛逆现象。《圣经》中充斥着大量父权观点,詹姆士王译本(TheKing James Version,简称KJV)是最传统的译本,严格按照原文内容翻译,其中,用男性主义词汇he同时代指男性和女性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He that hath my commandments,and keepeth them,he it is that loveth me.”(张莉,2007)。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盛行,女性思维受到极大解放,“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当时出版的新修订标准本(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简称NRSV)充满了女性主义色彩,是两性语言兼顾程度最高的翻译版本,比如,上例被改译为“They who have my commandments and keep them are those who love me.”(张莉,2007)。其中,男性主义词汇he被改为可以兼顾两性的词汇they和those。
可见,受当时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译者形成了自己对待性别问题的视域,虽然译者以忠实的翻译标准为导向,但仍然无法摆脱所处时代对自身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重视原作中对女性存在偏见的现象,并采用改变人称等方式,消除女性歧视现象。
3.3效果历史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影响
文本和语言具有一种效果力,可以不断地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意义。每一次阅读、理解和诠释都会赋予文本新的历史性,并进一步影响未来的理解。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随着境界的变化,对作品的感知度也会有所不同,傅雷(1984:694)曾说:“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因此《高老头》被他大改过三次,《傅尔德传》则六易其稿,《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出版多年后被他全部重译一遍(曹明伦,2019:177)。
以傅雷对《高老头》中“A quelle heureuse pensée dois-je le bonheur de vous voir,ma chère Antoinette?”这句话的翻译为例,三个版本的翻译分别为:“这是什么福气承您想到来看我呀,亲爱的安多纳德!”“真是好运气,承你想到来看我,亲爱的安多纳德!”“你真好,想到来看我,亲爱的安多纳德!”(孙凯,2013)第一版较为忠实地保留了原句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但语言稍显繁琐,不符合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第二版采用三个分句形式,语言更加通顺流畅,但“好运气”一词依然不够地道。第三版语言更加简练,用更加口语化的方式表达人物的心理和情绪,使读者更容易体会到作品中的情感。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三个版本的翻译愈发成熟,且具有可读性。
这三个版本的翻译代表了傅雷在不同时期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每次重译都是一次创造性叛逆。同一位译者在不同阶段对同一作品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出现不同于原作的思想更属正常。译者出现创造性叛逆并非不以传统的忠实翻译标准为导向,而是译作与原作并不存在完全等同的关系,文本的意义并不仅仅取决于作者最初的意图,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黄源深在其译著中提道:“一部文学巨著犹如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极对它的开掘。多个译本就是多次的开掘……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次的阐释,人们才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勃朗特,1993:514)如今,呼吁著作重译便是译者一步步向原作靠拢,力求向读者传达原作思想的表现。因此,读者应该多去深入了解;而译者应当更加深有体会。
3.4思维意识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影响
理解文本是一种意识活动,意识反作用于实践,因此译者的文本理解会影响文本翻译结果。理解绝不是与对象的绝对吻合,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相反,理解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它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在理解者前见中照亮文本,在文本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张德让,2001)。因此,译文并非源语文本直接呈现在译者大脑中的一种输出,而是译者有意识打磨而得的产物。
谢天振(1992)认为,“通常以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仅是译者。其实不然,除译者之外,读者和接受环境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会产生独特的想法和观点,当读者化身译者,所产出的译作自然会有偏离原作的现象。林纾在翻译《记惠斯敏司德大寺》这篇文章时,考虑到当时民众知识水平不高,为方便读者理解,采用节译等手段略去了大量细致景色的描写,比如,他将“From between the arcades,the eye glanced up to a bit of blue sky or a passing cloud and beheld the sun-gilt pinnacles of the abbey towering into the azure heaven.”简单地译成了:“高墉修直,仰望蔚蓝,直类井底观天;而本寺塔尖直上,半在云表。”(欧文,2013)
环境也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之一,外界环境会影响译者翻译结果。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他在翻译“One year with another,an average population,the floating balance of the 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mong the indigenous plants,maintained itself.”时增添了原句没有的含义:“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赫胥黎,1981)严复的翻译创造性地表达了自己对山河破碎的悲切以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愿望。
林纾和严复在翻译时受到当时读者和时代背景影响,其译文于原作来说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时代的需求和读者的反应会唤起译者强大的责任感,在翻译作品时,译者的思维不免受到外界的影响。创造性叛逆不单单是译者个人行为,更是多方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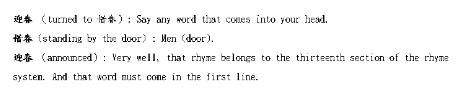
4结语
译者受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以及思维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而选择违反原作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或缺的。世界瞬息万变,要走在时代前列,不被时代的滚滚洪流裹挟,就要推陈出新,化旧的内容为新的思想,创造性叛逆为原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让译文获得了二次生命。
译者在翻译时要超越自身视域,向原作靠拢、与文本对话,尽量忠实地还原原作的意图和风格,但在受到各种限制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中另一种深层次的忠实。
参考文献
[1]BALZAC H D.Le Père Goriot[M].Paris:Le livre dePoche,1834.
[2]GADAMER H G.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1975.
[3]HAWKES D.The story of the ston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4]LEFEVERE 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5]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6]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
[7]曹明伦.译者要甘于并善于“悔棋”[J].中国翻译,2019,40(1):177-181.
[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9]傅雷.论文学翻译[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欧文.拊掌录[M].林纾,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2]孙凯.从三版《高老头》看傅雷的“翻译冲动”[J].法国研究,2013(1):52-60.
[13]谢飘飘.现代解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研究[J].新纪实,2022(11):26-28.
[14]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12(2):33-40.
[15]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报),1992(1):32-39+82.
[16]杨宪益,戴乃迭.A dream of red mansions[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
[17]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4):23-25.
[18]张莉.女性主义和《圣经》翻译——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0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