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菌群影响结直肠癌治疗的研究进展论文
2024-03-26 15:09:43 来源: 作者:hemenglin
摘要:人类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微生态系统,在结直肠癌(CRC )的发展和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热点。 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测序技术
【摘要】人类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微生态系统,在结直肠癌(CRC )的发展和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热点。 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人们不断地从不同层面认识肠道菌群和结直肠癌的关系。本文通过对肠道菌 群对 CRC 治疗的作用及影响进行综述,旨在为 CRC 的治疗提供更多思路。
【关键词】 结直肠癌; 肠道菌群; 靶向细菌; 研究进展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一种常见的消 化道恶性肿瘤, CRC 的发生、发展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 素共同驱动。而人体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 在肠道结构、免疫及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随着高通量 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人们从不同层面 认识到肠道菌群和 CRC 的关系,肠道菌群也逐渐成为 学科热点 [1]。有研究表明,随着肠道菌群组成的变化引 发菌群失衡,不仅会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还会影响 CRC 抗肿瘤药物的疗效和毒性,以及免疫和化学治疗的 效果 [2]。通过研究肠道菌群对 CRC 的发生及治疗的影响 可以为肿瘤治疗提供新思路和方法,在维持肠道菌群平 衡与多样性的同时,提高 CRC 的治疗效果及改善患者的 预后等方面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对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对 CRC 治疗的影响展开综述,以期为 CRC 的治疗提供不同 思路。
1肠道菌群与 CRC 的关系
肠道菌群是定植于肠道内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微生物 群落,在肠道微生态系统中意义重大。据人类微生物组计 划研究显示,肠道内存在超过 100 万亿个微生物,相当于 人体细胞总数的 10 倍;肠道菌群分布并不均匀, 定植菌体 最多的部位在结肠和直肠, 不仅寄居着约 3× 1013 种细菌, 还包括真菌、病毒、原生生物及古细菌,因此常被称为人 体的另一大“器官”[3]。不同种类的细菌按照一定的比例 组合分布,彼此依存又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但肠道菌群微生态结构又存在不确定性,肠道菌群定植、 疾病、益生菌及药物的使用、不同的饮食结构等因素均可 导致致病菌入侵或机会致病菌异常富集,引起菌群失衡。 有研究结果表明, 肠道菌群失调与 CRC 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 一旦肠道菌群失衡,肠道益生菌类群减少,致病菌 数量增加,致病菌分泌许多毒性因子,损伤肠上皮细胞, 引发慢性炎症反应, 促进 CRC 的发生、发展 [4]。目前,肠 道菌群与 CRC 的关系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司机 - 乘客 模型;② Alpha Bugs 模型;③大肠腺瘤癌序列模型;④生 物膜模型。根据司机 - 乘客模型理论,某些肠道细菌及代 谢产物损伤肠上皮细胞,诱发 CRC 肠道微生态改变 [5]。 在癌变过程中, “细菌乘客”(如葡萄球菌属、卟啉单孢 菌属、韦永氏球菌、链球菌属)增殖, “细菌司机”(如 肠杆菌科、假单胞菌科、奈瑟菌科、金黄杆菌属 ) 在肿瘤 微环境中失去竞争力逐渐被淘汰。在 Alpha Bugs 模型中, α 菌如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ETBF)可能通过影响肠道内 的免疫反应和微生物群落, 促使 CRC 的发生。ETBF分泌的 脆弱类杆菌毒素可以促进结肠上皮细胞中白细胞介素 -17 受体、核因子 κB(NF -κB)、抗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 子 3(Stat3)等信号通路转导,参与促癌与多步骤炎症级 联反应,破坏肠上皮屏障,引起菌群移位,触发肿瘤的发 生,并通过激活 Wnt/β- 连环素(Wnt/β-catenin)信号传导 途径, 诱发 CRC [6]。细菌致病途径可能是侵入结肠黏液层 后直接接触黏膜上皮细胞后,炎症反应增强并产生毒性细 菌代谢产物与 CRC 发生、发展相关的肠道菌群中, 以具核梭菌(Fn)、EFBF 和pks+ 大肠杆菌等为主。Fn 可产生具 核梭形杆菌黏附蛋白 A(FadA),黏附侵袭宿主细胞, 刺 激上皮细胞生长;同时 FadA 也可通过调节 β-catenin 等信 号通路诱导促炎反应和致癌效应。有研究显示, 在 CRC 患 者的结肠黏膜中pks+ 大肠杆菌普遍存在,并且在 CRC 易 感小鼠模型中促进 CRC 发生;pks+ 大肠杆菌可能通过多种 机制促进 CRC 的发生和发展, 包括引起 DNA 双链断裂、 活性氧产生和细胞周期停滞等, 这可能是pks+ 大肠杆菌促 进 CRC 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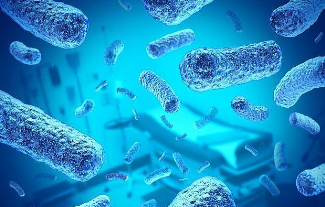
2肠道菌群对 CRC 治疗的干预及影响
2.1肠道菌群对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 目前,肿瘤免疫 治疗是 CRC 治疗中比较热门的方式。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ICIs)在免疫治疗中应用广泛,以程序性死亡受体 -1 (PD-1)/ 程序性死亡 - 配体 -1(PD-L1)为靶点的免疫疗法 逐渐成为研究焦点。推测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调节宿主免 疫系统参与 CRC 的抗肿瘤应答,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免疫治疗相关的毒性。肠道菌群拥有丰富的抗原库,具 有免疫刺激潜能,可被先天免疫细胞表达的模式识别受 体识别。研究显示, CRC 患者肠道菌群数量和代谢与健康 人群有明显不同,并且其肿瘤组织中的微生物区系多样 性降低 [8]。双歧杆菌可以通过调节菌群的构成和白细胞 介素 -10(IL-10)抑制调节性 T 细胞(Tregs 细胞) 来缓 解 ICIs 相关结肠炎。脆弱芽孢杆菌能够刺激树突状细胞 (DC)成熟,而后增强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蛋白 -4 (CTLA-4)阻断的抗肿瘤活性。SHI 等 [9] 指出,肠道菌群 可以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TME)和肠道免疫来影响抗 CD47 免疫治疗的疗效。积聚于 TME 的双歧杆菌可激活 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信号通路,刺激抗 CD47 抗体的产生,从而改变肿瘤微环境,达到免疫治疗的效 果。在一项综合分析研究中招募了接受抗 PD-1/PD-L1 治 疗的晚期胃肠道癌症患者,研究结果发现,其粪便中普 氏菌属 / 拟杆菌属的比例上升,意味着其可能会有更好 的抗 PD-1/PD-L1 治疗反应,且其中某些特定菌群的亚组 可能会表现出更高比例的普氏菌属、毛螺菌科及瘤胃菌 科,而拟杆菌、粪球菌等在治疗反应差的患者肠道中富 集 [10]。另有研究表明, PD-1 抑制剂的较好疗效与高丰度 的普雷沃菌属、狄氏副拟杆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等有 关,而 PD-1 抑制剂对 CRC 无效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高丰 度的拟杆菌属 [11]。特定的肠道细菌在免疫治疗中可以提 高肿瘤的应答。有研究提出,在 CRC 和黑色素瘤小鼠模 型中,口服鼠李糖乳杆菌可激活环鸟苷酸 - 腺苷酸合成酶 (cGAS)/STING 信号通路,触发 DC 活化,增强抗肿瘤细 胞功效,从而增强抗 PD-1 的疗效 [12]。
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对 ICIs 疗效起着关键作用。 ZHANG 等 [13] 研究发现,在应用 PD-1 抑制剂前,使用广 谱抗生素耗竭小鼠肠道内源性菌群会影响其抑制癌细胞的 作用,这表明肠道菌群的的种类和数量可能是抑制癌细胞 生长并影响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进一步研 究发现,在接受肿瘤免疫治疗反应良好的小鼠体内,乳杆 菌数量显著上升;此后,研究将筛选分离出的副乳杆菌株 作用到肠道菌群缺乏的小鼠体内,结果表明,小鼠接受抗 PD-1 抑制剂治疗, 也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 且这些小鼠的 身体也未受到任何疾病影响。LV 等 [14] 研究发现,在具有 微卫星稳定(MSS)的 CRC 患者中, 可以通过肠道菌群的 重构来增强 PD-1 阻断的有效性;结果还发现, 中药葛根芩 连汤可以增强抗 PD-1 抗体免疫治疗的疗效,并在体内抑 制肿瘤生长;通过结合多种药物的应用还显著提高了肿瘤 组织和外周血中 CD8+ T 淋巴细胞的比例, 促进干扰素和白 细胞介素 -2(IL-2)的表达;这些结果表明,肠道菌群相 互作用并诱导细胞因子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提高 CRC 免 疫治疗的疗效。
2.2肠道菌群对化疗效果的影响 CRC 患者的肿瘤复发 和转移主要源于化疗耐药性。因此, 阐明 CRC 患者化疗 耐药机制并寻找新的治疗目标对于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 要。Fn 以 TLR-4 和 microRNA 为靶点,通过激活自噬途径 诱导 CRC 细胞对 5- 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耐药; 同时提示 Fn 的丰度可以作为预测 CRC 患者预后的重要 指标之一。肿瘤干细胞被认为是 CRC 化疗耐药和转移的 一个来源。有证据表明,Fn 通过促进脂肪酸氧化和 Notch 信号的激活来促进 CRC 干细胞的自我更新 [15]。这些发现 揭示,Fn 是一种旨在克服 CRC 患者化疗耐药的潜在干预 目标。
肿瘤组织内细菌可调节肿瘤化疗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从 CRC 患者体内获得的大肠杆菌分离株也具有降解 5-FU 的能力,这可能导致治疗效果下降。根据 GELLER 等 [16] 的研究, 揭示了采用吉西他滨治疗 CRC 小鼠, 通过依赖胞 苷脱氨酶的长异构体可将药物转化为无活性的形式,进而 导致吉西他滨耐药;此外, 体外将 CRC 细胞与含有胞苷脱 氨酶的细菌共同培养,后将其定植于同种异体移植的小鼠 体内,可引起对吉西他滨的耐药性,这一效应可通过使用 抗生素来消除。
2.3靶向细菌调节对 CRC治疗的影响 CRC 患者放疗 后肠道菌群明显变化,可能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生活质量 严重下降。通过对接受过放疗的 CRC 患者进行肠道微生 物组研究,结果表明,共生细菌如双歧杆菌、粪杆菌和 梭菌属减少,而类杆菌属和肠球菌属增加 [17]。最近的一 项研究探讨了口腔微生物群对 CRC 放疗疗效及预后的影 响,Fn 可通过食物或其他方式进入肠道后可能会在肠道 中定植并大量富集,影响放疗疗效和预后,在这种情况 下,使用甲硝唑进行干预可有效阻断 Fn 在肠道中的定 植和繁殖,从而降低其对放疗疗效和患者预后的不良影 响 [18]。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可改善肿瘤放疗后胃肠 道功能和肠上皮的完整性。近年来,肠道菌群的靶向调节 是 CRC 治疗领域中的新兴方法。临床试验已经开始试图 操纵微生物群以达到治疗目的,靶向细菌调节,如 FMT、 益生菌及益生元和工程细菌的调节,已经显示出优化癌症 治疗的潜力,逐渐出现在胃肠道癌症的治疗中。
2.3.1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 即用健康供体的粪便通 过内窥镜或口服胶囊等方法转移到患者的肠道中,可辅 助恢复微生物稳态,这可能有助于优化肿瘤患者的预后。 FMT 联合 PD-1 阻断剂可克服抗 PD-1 的原发性耐药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抗 PD-1 治疗有反应的患者的粪便重 建无菌小鼠,相应的小鼠也对 PD-1 阻断有反应;相比之 下,用无反应患者的粪便重建的无菌小鼠对 PD-1 阻断无 反应。小鼠的这种无应答表型可通过来自应答患者的额外 FMT 来逆转。FMT 的另一种作用形式是补充一种确定的 细菌组,通过与宿主免疫系统协同作用,改善治疗疗效。 TANOUE 等 [19] 通过从健康人群粪便中分离出一个包含 11 株细菌的特殊联合体, 该联合体可以促进肠道内 CD8+ T 淋巴细胞的形成,而且将其应用到 MC38 肿瘤小鼠模型 上,不仅显著改变了小鼠肠道的生态结构,也提升了 ICIs 抗癌药物的有效性。MONTALBAN-ARQUES 等 [20] 选择了 4 种梭菌菌株,定植在 MC38 小鼠模型中,补充这种混合 菌株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且比单独抗 PD-1 治疗更有效。 显然,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生态结构,可以有效地预防和 治疗一些癌症,或许这种微生态结构的调节不仅能够提高 免疫力,还能作为更加广泛的癌症预防和治疗的靶标,有 效地改善患者的预后。
2.3.2 益生菌及益生元益生菌在调节肠道菌群、增强 肠道屏障的完整性、抑制致病菌生长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 用。益生元是食物中难以消化的被选择性发酵的成分,可 引起胃肠道菌群组成和 / 或活动的特定变化,从而有益于 宿主健康。由于益生菌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广泛的健康益 处,可作为 CRC 的预防及治疗药物。通过使用益生菌疗 法,可以提高肿瘤免疫治疗的安全性, 一种新的益生菌 罗伊氏乳杆菌已被确认能够阻止 CRC 进展,其独特的代 谢产物导致蛋白质翻译受抑制从而抑制体内外 CRC 淋巴 的生长。在多种小鼠模型中,益生元丰富了某些细菌属 及其代谢物,从而提高抗 PD-1 抗体的活性,诱导抗肿瘤 免疫,并促进对 ICIs 的反应性。包含于益生菌制剂中的 微生物可产生多种益生菌,其代谢产物对 CRC 的治疗有一定疗效。短链脂肪酸(SCFA)如丁酸盐、丙酸盐和乙 酸盐不仅被认为是肠道菌群的必需营养素,而且还发挥 着多种不同的功效,例如调节局部免疫反应、保护肠道屏 障和抑制肠道炎症反应,尤其对于维持结肠黏膜的正常 生理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SCFA 可在体内外直接促进 CD8+ T 淋巴细胞的抗肿瘤作用,改善抗肿瘤免疫反应。 丁酸盐可通过阻断 DNA 结合 2 依赖性白介素 -12 通路直 接提升 CD8+ T 淋巴细胞对抗肿瘤的毒力。
研究显示,特定的肠道菌株如幽门螺杆菌、Fn、pks 等在 CRC 患者肠道中富集 [21]。因此, 筛查并评估 CRC 患 者术前肠道菌群的基本状况,可以更好地了解患者的肠道 菌群,从而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来改善预后,减少围手 术期不良事件的发生。口服乳酸菌和双歧杆菌活菌制剂等 益生菌疗法在 CRC 治疗中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CRC 术 后感染率明显降低。根治性切除肿瘤是 CRC 最佳的外科 治疗方案,尽管外科医师在术中尽量采取恰当的吻合口技 术预防吻合口漏的发生,但术后吻合口漏仍然是一个需要 关注的问题。研究结果发现,粪肠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以 及pks+ 大肠杆菌可能会导致吻合口漏的发生, 这些细菌都 会分泌明胶酶以分解胶原蛋白,而胶原蛋白是促进吻合口 愈合的关键物质。 HAJJAR 等 [22] 学者的实验发现, 在提供 益生元,如菊粉、半乳糖的情况下, SCFA 的产生会显著 增多,从而使得围手术期小鼠模型吻合口周围组织的胶原 蛋白含量相应提升,达到加速吻合口愈合和促进肠道屏障 修复的作用。这些研究结果提示,益生菌的补充对于术后 的恢复至关重要, 其代谢产物如 SCFA、丁酸盐等对于术 后的恢复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结肠上皮的增殖、组织修复 及黏膜连续性均有影响,通过补充益生菌或其代谢产物, 有可能预防和治疗术后吻合口漏。
ZHENG 等 [23] 制备了益生元封装的益生菌孢子, 将作 为益生菌的丁酸梭菌和作为益生元的右旋糖酐(经化学修 饰) 相结合, 并在 CRC 模型中评估了其抗癌活性。丁酸梭 菌在病变中发酵葡聚糖, 可产生具有抗癌活性的 SCFA。此 外,孢子可以增加产生 SCFA 的细菌,并显著抑制肿瘤的 生长。产生 SCFA 的细菌通过在肠道内建立一个抑制肿瘤 的微环境来阻止肿瘤生长;结果证实,口服给药后,结肠 癌的孢子指数增加, 产生 SCFA 的细菌抑制肿瘤生长效果 明显。 HO 等 [24] 通过改造可将天然成分转化为具有抗癌活 性的代谢物的共生微生物, 后与 CRC 细胞上的硫酸乙酰肝 素蛋白聚糖结合, 用改造后的共生微生物及食物喂食 CRC 小鼠,发现肿瘤显著消退。
具有增强功能的工程益生菌可能提供一种安全有效 的辅助治疗方法。工程益生菌被开发出来,试图改善大 多数 MSS-CRC 的免疫微环境。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名为Nissle1917 大肠杆菌菌株的益生菌,该菌株表达靶向 PD-L1 和 CTLA-4 的单域抗体片段,具有用于肿瘤特异性 的释放机制。在 MSS-CRC 的小鼠模型中,表达抗 PD-L1 和抗 CTLA-4 抗体, 以及粒细胞 -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的三工程大肠杆菌,降低了肿瘤的生长速度,患者生存率 有所提高, 突出了基因工程益生菌在提高 CRC 治疗疗效方 面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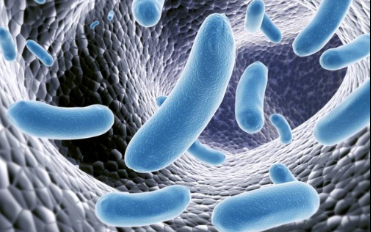
3小结与展望
调节肠道菌群作为预防和治疗 CRC 的潜力巨大, 通过 免疫治疗、放化疗、益生菌及其制品以及 FMT 等不同的治 疗方式可能对肠道菌群在 CRC 治疗方面产生影响, 其中包 括免疫调节功能、恢复肠道生态失调、提高药物生物利用 度、降低药物毒性、提高杀瘤活性和产生抗癌物质等。虽 然目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鉴于技术、研究方 法、环境条件等客观原因,对肠道菌群的研究仍然充满挑 战, 例如, 克服 CRC 相关致病菌诱导化疗耐药性的难题, 确保 FMT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合适地筛选菌株等。 因此,为了获得可靠且全面的结果,还需要通过大量的实 际操作,包括严谨的动物实验、临床实践,来评其治疗作 用、安全性及预后,为临床应用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陈玉茹 , 陈豪 , 龚普阳 , 等 . 四君子汤防治结直肠癌的药理作用 机制研究进展 [J]. 药物评价研究 , 2023. 46(12): 2671-2676.
[2] 赵正奇 , 梁玮钰 , 杨楚琪 , 等 . 从 " 瘀毒互结 " 探讨结直肠癌的病 机特点和治疗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 2023. 46(6): 869-873.
[3] 李晶晶 , 朱成章 , 史新龙 , 等 . 基于 16SrDNA 测序分析胆囊结石 及胆囊切除对结直肠癌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 [J]. 中国普外基础 与临床杂志 , 2022. 29(12): 1573-1582.
[4] 姚望, 李和根, 田建辉 . 菌群的黏膜免疫调控与恶性肿瘤防治 [J].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 2021. 28(3): 306-310.
[5] 姜志怡 , 孙佳春 , 赵琪 , 等 .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进展中的研 究 [J].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 2023. 29(1): 56-60.
[6] 胡洲 , 武永胜 .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 [J]. 中 华消化外科杂志 , 2021. 20(6): 708-712.
[7] 王晶晶 . 基于炎症性肠病的天然产物与肠道菌群互作的数据集 建立与应用 [D]. 大连 : 大连理工大学 , 2021.
[8] 彭强 , 李利发 , 周何 , 等 . PD-1/PD-L1 抑制剂在晚期结直肠癌中 应用的研究进展 [J]. 山东医药 , 2022. 62(1): 86-89.
[9] SHI Y, ZHENG W, YANG K, et al. Intratumoral accum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facilitates CD47-based immunotherapy via STING signaling[J]. J Exp Med, 2020. 217(5): e20192282.
[10] 刘恩瑞 , 王贵玉 . 程序性死亡受体 -1 及其配体抑制剂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 [J].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 2019. 26(5): 620-624. [11] 徐新建 . 肠道菌群通过代谢途径影响 PD-1 抑制剂治疗结直肠癌疗效的研究 [D]. 石家庄 : 河北医科大学 , 2021.
[12] SIW, LIANG H, BUGNO J, et al.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induces cGAS/STING- dependent type I interferon and improves response to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J]. Gut, 2022. 71(3): 521-533.
[13] ZHANG S L, MAO Y Q, ZHANG Z Y, et al. Pectin supple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anti-PD-1 efficacy in tumor-bearing mice humanized with gut microbiota from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J]. Theranostics, 2021. 11(9): 4155.
[14] LV J, JIA Y, LI J, et al. Gegen Qinlian decoction enhances the effect of PD-1 blockade in colorectal cancer with microsatellite stability by remodelling the gut microbiota and the tumour microenvironment[J].Cell Death Dis, 2019. 10(6): 415.
[15] 张越 , 王伟 , 尹琦 . 抗生素与 5- 氟尿嘧啶治疗结直肠癌患者肿瘤转移的关系 [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 2023. 48(12): 1520-1523.
[16] GELLER L T, BARZILY-ROKNI M, DANINO T, et al. Potential role of intratumor bacteria in mediating tumor resistance to the chemotherapeutic drug gemcitabine[J]. Science, 2017. 357(6356):1156-1160.
[17] 宋德心 , 王伟东 , 高瑞祺 , 等 .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和 诊断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J].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 2022. 31(4):527-536.
[18] 陆雅蓉 , 贾婧 , 彭锐 , 等 . 具核梭杆菌参与结直肠癌进展机制和 疗法的研究进展 [J].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 2023. 28(2): 139-144.
[19] TANOUE T, MORITA S,PLICHTAD R, et al. A defined commensal consortium elicits CD8 T cells and anti-cancer immunity[J]. Nature,2019. 565(7741): 600-605.
[20] MONTALBAN-ARQUES A, KATKEVICIUTE E, BUSENHART P,et al. Commensal Clostridiales strains mediate effective anti-cancer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solid tumors[J]. Cell Host Microbe, 2021.29(10): 1573-1588.e7.
[21] 梁思远 . APC 基因突变的结直肠腺瘤患者肠道特征菌群的分 析 [D]. 南宁 : 广西医科大学 , 2018.
[22] HAJJAR R, OLIERO M, CUISINIERE T, et al. Improvement of colonic healing and surgical recovery with perioperative supplementation of inulin and galacto-oligosaccharides[J]. Clin Nutr,2021. 40(6): 3842-3851.
[23] ZHENG DW, LIR Q, AN JX, et al. Prebiotics-encapsulated probiotic spores regulate gut microbiota and suppress colon cancer[J]. Adv Mater, 2020. 32(45): e2004529.
[24] HO C L, TAN H Q, CHUA K J, et al. Author correction: Engineered commensal microbes for diet-mediated colorectal-cancer chemoprevention[J]. Nat Biomed Eng, 2020. 4(7): 754-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