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恨海》中作者自评论文
2024-05-17 14:41:19 来源: 作者:hemenglin
摘要: 吴趼人借用传统小说点评模式,但评点内涵和 评点术语明显不同,他弱化早期小说评点注重篇 章结构和文法的做法,进而增加小说评点道德观 念、社会情怀等方面内容
吴趼人借用传统小说点评模式,但评点内涵和 评点术语明显不同,他弱化早期小说评点注重篇 章结构和文法的做法,进而增加小说评点道德观 念、社会情怀等方面内容,把作者自评融入小说 创作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强了文章 表现力。
深化主旨,强化作者创作意图
《恨海》讲述了张棣华和陈伯和这一对青年男 女在庚子事变大背景下逃难过程中相互扶持的情 感经历和悲剧结局。在小说开篇,吴趼人就用大 段文字阐述了“情”字内涵: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 生,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对于朋友施展起 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 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 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
吴趼人理解的“情”是广义、多方面的,他 将“忠、孝、慈、义”等道德化观念一并纳入其 中,并不单指男女之情、夫妻之爱。吴趼人在《说 小说》(杂说)中谈到《恨海》这部作品时说: “然其中之言论思想,大都陈腐常谈,殊无新趣, 良用自歉。所幸全书虽是写情, 犹未脱道德范围, 或不致为大君子所唾弃耳。”吴趼人有意识地从 正统道德立场来解释他所说的“情”,对“情”做了泛道德化的解释和说明。吴趼人的这种言论 和认识在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和肯定。
在《恨海》第一回,因京城“拳匪作乱”,陈 戟临想让两个儿子一起南下避难,但仲蔼不肯离 开。他认为“父母都在这里,当此乱离之时,岂 有两个儿子都走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张伯母出京, 孩儿留在这里,侍奉父母,万一乱事起了,也同 父母在一处避乱”。此处眉批是“此情施于父母者, 谓之孝也”。仲蔼不愿抛下父母南下避祸,即作 者崇尚的“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故作者 在眉批中特别点明,这也是对其“情”理论的最 好诠释。逃难途中,棣华与伯和失散,夜半时分 心中却有无数个“他”:
棣华心中七上八下,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样 了。他若是看见我们的车子,自然该会寻来 … … 他是一个文弱书生 … …他病才好了 ……他是一个 能体谅人的 … …伯和弟弟呀,这是我害了你了! 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是好?这会你倘回来 了,我再也不敢避什么嫌疑了。左右我已经凭了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与你的了。
在这段内心独白中,棣华不再避讳男女之防,内心波澜一览无余。她不仅称伯和为“他”,甚 至直呼“你”或“弟弟”,把压抑心底的儿女情 思一股脑地和盘托出,完全不似现实中的娇羞之 态。吴趼人在此处眉批中说:“口中偶露一 ‘他’ 字便顿住不肯说,意中偏有许多‘他’字;许多‘他’ 字犹以为未足,要提其名而呼之曰‘弟弟’、曰‘你’,真是体会得到,描摹得出。”吴趼人把自己对“情” 字的理解和态度通过棣华、仲蔼等一众人物形象 表达和发散出来,并通过作者自评的方式多次点 明和加深,这种处理方式既丰富了故事人物性格 和形象特征,又强化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情感表 达,使作品内容和点评文字浑然一体,相辅相成。
正所谓“有些评点就与作品浑然一体,难解难分, 评点靠作品而生发,作品得评点而生色。一些优 秀的评点作品往往能一针见血地点出作者的匠心 和作品的奥妙,画龙点睛地引导读者去领悟,去 欣赏,去再创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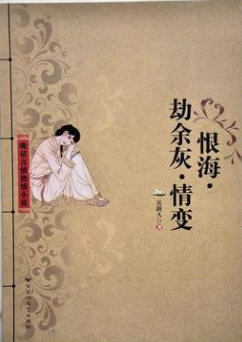
明暗交错,揭示未明写之内容
吴趼人在《恨海》创作中故意将“真事”隐藏 起来,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艺术效果。然后,再 借助眉批的形式告诉给读者,把作者自评融入小 说文本,形成一个整体,起到辅助、补充小说文 本的作用,以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内涵。
信物互赠,埋下伏笔。在小说第二回, 因逃难 路上携带金银不方便,又容易丢失,棣华一行便 把所带贵重物品缠在身上。棣华将自己的十两金 叶子交给了伯和,伯和也将家传的白玉双喜牌交 给了棣华。表面看似逃难途中,情急之下简单的 物品交换,甚至还有棣华母亲白氏在中间转交的 过程,实是这对有情人之间“信物”互赠的情节, 只是作者没有明说出来罢了。后来,继续南下逃难, 两人意外失散。张棣华不知道多少次对着白玉双 喜牌流下眼泪,只是没有明写出来。直到第十回, 陈伯和病重住院,张棣华拿出白玉双喜牌意为宽 慰伯和,可在读者看来是多么讽刺。可以说,他 们对待爱情“信物”的态度就是他们对待爱情的 态度,两相比较,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串联时事,互为补充。《恨海》全文以庚子 事变为背景展开叙述故事,是战乱状态下晚清社 会现实生活的重现,阿英把《恨海》收编在《庚 子事变文学集》中。比如第七回, 走散后的伯和, 误打误撞地躲进一家米店,避难了一个多月,“忽 然一天,听得外面炮声震天,比从前响得格外厉害, 隐约听得外面有许多哭喊的声音”。吴趼人眉批道: “此联军破天津城也。用暗写法, 令读者自明。” 第六回,张棣华用了伯和的被褥,不禁浮想联翩,作者批注道: “如卿此言,则庚子之变身经其难 者何止千万人, 岂皆前程万里者也? ”《恨海》 小说十回正文没有一处明说故事背景为“庚子事 变”,作者自评文字时多次提到。作者采用了暗 写的方法并未直接挑明而已,却用眉批的形式将 故事情节和时事串联起来,互为补充、相互印证, 既显示了作者对战乱下普通民众生活的深层关照, 也拓展了文本的表达空间。
深化人物形象塑造。作者多次对人物进行评 价,有力服务了人物形象塑造。比如,伯和在逃 难途中躲进一家药店避难,意外发现了八口皮箱, 他谎称是这家药店的主人并将财物据为己有。携 带皮箱出逃之时,原本伯和因与亲人走散还“愁 眉双锁,短叹长吁”,转而想到这些金银财宝, 真是发了笔大财,不觉得暗暗快活起来。后来, 他携带皮箱至烟台,找来铜匠打开,看到里面多 是“细软、衣服、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不觉 大喜”。这里眉批中写道“善读者不俟终篇,己 知伯和为人矣”。相对于亲情,伯和更看重的是 钱财,与“不以物喜”的君子之风大相径庭。吴 趼人不齿于伯和撒谎诓骗、贪不义之财的小人手 段,他通过点评早早让读者看明白这一切,也向 读者暗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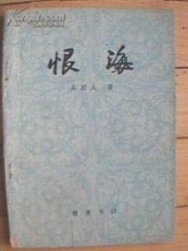
炫技弄彩,展示独特的写作技巧
吴趼人曾在《说小说》一文中讲:“吾前著《恨 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 广智书局。出版后偶取阅之, 至悲惨处,辄自堕泪, 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恨海》本就是作者 得意之作,他对自己的写作技巧很满意,所以他 采用作者自评的方式将小说独特的创作技巧传达 给每一位读者。
对于梦境的描写。吴趼人对自己心理描写的手 法非常自豪,在眉批中多次点评出来。如第五回 中,伯和与棣华等人走散后,棣华夜有所梦, “见” 到了伯和。在描写这段梦境文字时,连用了四处 眉批,他将自己写梦境的手法与其他小说家比较,
“凡小说家写梦境,入梦时似真似假,一至出梦, 总不脱豁然惊悟等语。此却别具一格”。吴趼人 这段梦境描写将现实与梦境联为一体,似梦如幻。 入梦时,张棣华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进入梦境就非常自然贴切;出梦时,也没有用写梦境 的套语“猛然惊醒”之类,而是将梦中牲口嘶鸣 与现实中驴子嘶叫交织在一起,水到渠成。
相关叙述技巧的描写。小说是叙事文学作品, 所以小说家都十分注重小说叙事艺术手法的运用。 第九回突然有一天张鹤亭气冲冲回来,把伯和如 何诓骗钱财、讨妓女、吃鸦片,最后沦落为浪子 的事情从头到尾交代出来。此处眉批道: “补叙 伯和以前之事,全用鹤亭口中述出,并不费事, 倘从伯和一边叙来,则嫖妓、娶妓,种种丑态, 未免有累笔墨矣。”可见,经过这样艺术化的提 炼和加工后就可以省却大量无用的笔墨,集中精 力来描绘主要故事情节,表现主要人物的形象特 征。再如第十回, 一次朋友聚会之时,仲蔼偶然 席间遇到堕落为妓女的娟娟,并拿旧话试探她: “‘难道还是表兄表妹么? ’那妓女听了,登时 面红过耳,马上站起来,对那客人说道: ‘我还 要转局去,你等一会来罢。’说罢,拔脚便跑。”。 这时眉批道:“一部书中,伯和浪荡,娟娟卖*, 岂无可写之处?观其只用虚写,不着一字而文自 明,作者非不能实写之,不欲以此等猥屑污其笔 墨也。其视专模写狎亵之小说相去为何如也? ” 作者难道不知道“伯和浪荡,娟娟卖*”的内容 更易于迎合部分读者和书商的需求吗?只是作者 不齿于多着墨于男盗女娼之事罢了,故而一一省略。
关于赞赏写作技巧的描写。吴趼人在创作《恨 海》时,每当写至得意处会自己跳出来“自我赞赏” 一番。如第五回棣华离开店家时赠送五姐儿一枚 金戒指,五姐儿吓得连忙道谢并声称来世必报大 恩,作者批注道:“不喜而吓,所谓受宠若惊也。
不道谢而言报,亦是意外喜极而惊语。亏他写得 出来。”再如第九回,鹤亭找到伯和,告诉伯和 他的父母已经遇害了。这时:
伯和大惊道:“这是几时的事?”鹤亭道:“可 见得你是昏天黑地的过日子,连父母信息都不去 打听打听! ”说罢,取出李富的信给他看了,也 不免留下泪来。
此处眉批说:
父母惨死,为子者得信, “流下泪来”四字之 上加上“也不免”三字,其孝可知。世间真有此子, 令人一叹!
作者在“流下泪来”之前加上“也不免”三字, 真切写出伯和堕落为浪子之后的“混账”作为和“非子”行径,完全不似仲蔼以“孝义”为先的品行。 当仲蔼听鹤亭说“令兄已经不在了”时,看仲蔼 的反应: “仲蔼听说,放声大哭道: ‘哥哥!不 道果然是你也! ’哭倒在地。良久,鹤亭含悲劝 住了。”两相比较,相差何其远也。
增强趣味,突出阅读的娱乐性
文学是具有审美教育作用的,当然也要有一定 的娱乐功能,尤其是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近 代时期的小说创作被某些政治家“拿来”用作宣 扬“救国救民”的理论工具,小说本身的娱乐性、 可读性不受重视。
吾国昔尚记诵,学童读书,咿唔终日,不能上 口。而于俚词剧本,一读而辄能背诵之。其故何也? 深奥难解之文,不如粗浅趣味之易入也。学童听 讲,听经书不如听《左转》之易入也, 听《左转》 又不如听鼓词之易入也。无他, 趣味为之也。(《月 月小说》序)
吴趼人非常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不是 只把小说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如第三回 棣华一行人被流民冲散,骡子向西奔去,车夫边 追边“㖞!㖞!㖞!”乱叫,其声其境,如在目前, 滑稽可笑。眉批道:“百忙中添此一句,令人失笑。” 作者在传达小说主题思想的同时,也增强了文章 的娱乐性、可读性, 使小说更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恨海》中的自评文字看似独立于小说创作之 外,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自觉创作行为,已成为 作者文学表达的一部分,有着很强的目的性、自 主性。他将《恨海》的“情”字内涵在作者自评 中不断加深和强化,增强了写情小说的情感主题, 同时也将作者自己的情感、态度纳入其中;把小 说创作中不易明写的“隐语”提炼出来,通过自 评方式告诉读者,明暗交错,交相辉映;对文中 独特的表达技巧和写作手法也加以提示和赞赏, 扫除了阅读障碍,帮助读者理解小说内容;他追 求小说的趣味性,也在小说创作中不断实践,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