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武者》影子的隐喻解析论文
2024-05-15 14:37:41 来源: 作者:hemenglin
摘要:《影武者》(又名《影子武士》)是黑泽明在历经创作低潮后推出的鸿篇巨制,是 黑泽明后期最为重要的电影之一。从动静结合的镜头,别出心裁的场景构图
摘要:《影武者》(又名《影子武士》)是黑泽明在历经创作低潮后推出的鸿篇巨制,是 黑泽明后期最为重要的电影之一。从动静结合的镜头,别出心裁的场景构图,再到浓郁独特的 色彩运用,都可以说是黑泽明电影美学的集大成之作。文章重在对《影武者》进行文本解读, 从身份矛盾、若干镜像以及影武者之梦的角度出发,探究片中有关“影子”的隐喻设计。
关键词:《影武者》;镜像理论;精神分析;黑泽明
几次票房惨败后,已没有公司愿意继续为黑泽明投 资,而后由科波拉和卢卡斯牵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向东 宝株式会社投资,黑泽明最终拍出了耗资巨大但也空前成 功的彩色电影—— 《影武者》,这也是黑泽明后期转向的 一个重要标志。《影武者》作为黑泽明的代表作,这部影 片通过从动静结合的镜头,独出心裁的场景构图,再到浓 郁独特的色彩运用,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恢宏壮丽、深入人 心的故事世界,极致地展现了属于黑泽明独特的电影美 学。本在《影武者》上映前很长一段时间,黑泽明备受煎 熬,一方面市场失败的连续打击,另一方面天才也最恐惧 “江郎才尽”。痛苦与欲望是黑泽明电影永恒不变的话 题,笔者认为在《影武者》中这种痛苦最为强烈,黑泽明 电影一向同西方戏剧交融,而其表述的内涵也多充斥着从 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延续下来的悲剧气息——由欲望带来的 痛苦,但在《影武者》中黑泽明却更偏向一种东方化的悲 剧——一种生命本质上的癫狂。
影片主要讲述了在架空的日本战国时代,名将武田 信玄死后告诫家臣三年内禁止发丧,而后,信玄的影武者 逐渐被塑造成真信玄最后殒身的故事。故事是简单又常见 的以“身份倒置”为出发点的设计,而如何叙述这一“倒 置”则成为全片的关键。
一、真信玄与假信玄
武田信玄在日本的战国历史上被称为“甲斐之虎”, 在后世的艺术创作中信玄是骁勇善战、精通兵法的名将, 与“军神”上杉谦信齐名。当然,黑泽明在片中并没有着重渲染武田信玄的传统形象,只是选取了“其疾如风,其 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武田家兵法,在片中主 要塑造了武田信玄“不动如山”的形象。
武田信玄的影武者则是被信玄之弟从刑场救下的无名 盗贼,同“甲斐之虎”相比较只是“乡野之虫”。当然, 电影的戏剧张力也主要在这个矛盾中产生。但笔者想探讨 的并非这对显性的意象。通观全片可以看到真信玄并非 真正的“不动如山”,在得知盟军朝仓家的背叛时勃然大 怒,家臣说“您是武田家家主,‘不动如山’的信玄”才 冷静下来;而相反,假信玄反而在代替真身的三年间恪守 “不动如山”的信条,甚至打赢了几场重大战役。
这一 “矛盾”之下的“矛盾”才是本片区别于同类 剧情的特征。简而言之,即是“为了成为某人而将某人的 特征做得更加极致”,其背后的逻辑是:被社会关系、他 者凝视所建构出来的人(“不动如山”的名将武田信玄) 脱离了人自身(会大发雷霆会放声大笑的武田信玄),逐 渐独立成了一套社会编码(他人所希望看到的“武田信 玄”)。影武者与其说是成为武田信玄,不如说是侵入了 这套社会编码。依此来看,真正的武田信玄亦是在“不动 如山”的社会形象中将自身限制,囿于其中。
在伊藤润二的一篇漫画《窃脸贼》中, 一个人拥有 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的模样从而取代他的能力(从外貌 到性格) [1] 。这种社会位置被顶替、自我在边缘迷失给人 带来的本能上的恐惧,其核心问题是“他是我,那我是 谁?”,在《影武者》这部影片中预设了真主体(武田信玄)的死亡,问题就变成了“我是他,那我是谁?他又 是谁?”这一成为他人的过程,黑泽明将矛盾主要表现 在行为上,片中最为有趣的一幕便是当假信玄被接回府上 与真正的武田信玄昔日的侍从接触。当假信玄抓耳挠腮不 知所措时,原本谨慎的侍从也随之大笑并席地而坐;但当 假信玄收敛沉思静坐时,侍从立即回想起了旧主的形象而 恭敬跪坐。这便是居伊•德波所说的“姿势取代了行为本 身的内容”,在此处就是假信玄的姿态回归也象征着“武 田信玄”这一威严的在场。这种权力的异化历史悠久,无 需权力者在场,自其异化的一切都制约着权力体系下的个 体。中国古代的尚方宝剑、诏书,或乔治奥威尔在作品 《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老大哥”文学形象都是这种异 化的产物,而黑泽明在此处将其作为制造讽刺笑点的矛 盾。
假信玄以姿态所带来的权力回归也依赖于侍从的记 忆,这也牵涉到此片乃至所有“身份错位、倒置”剧情的 共同点: 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并非其个人的事。这类身份 替换最为典型的历史形象便是马丁•盖尔的故事[2] 。于马 丁•盖尔而言,能彻底代替另一个人生活是基于妻子的瞒 报;而对于作为武田信玄的影武者, 一众亲信、家臣的帮 助必不可少。即便是再相似的两人,完全代替某人存在的 可能性,也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弹性上。而这种弹性既 是这类故事得以开始的条件,也是终结一切的助推力量, 因为无论是马丁盖尔的妻子还是武田家臣,他们帮助主角 成为另一个人都不是为了主角,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 要。当假马丁•盖尔被法官宣判死刑,假信玄从黑马坠落, 所有曾经的帮手都会无情地抛弃主角。而对于主角本身而 言,“成为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情感又如何将其撕 裂?

二、成为他人
被他人顶替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成为他人是一种莫大 的无助。“成为他人”这类题材最为著名的当数卡夫卡的 《变形记》,如果说成为怪物还带有生物性的恐怖,那么 成为另一个人则完全是身份错位与倒置带来的自我消弭。 如果说曾经那个贫穷却又自由的“乡野之虫”身份是影武 者得以站稳的地基,那“甲斐之虎”的身份无疑是将他倒 吊在半空中的绳索。
理解影武者成为“武田信玄”的过程,最重要的破 题点便是那一场梦。梦在黑泽明的任何电影中作用都举足 轻重,《影武者》片中经典地采用了诡谲扭曲的背景作为 梦的提示,再加上暗红色的夕阳色调,展现了黑泽明独特 的构图、色彩美学。对于这一场梦境戏的主要关注点在 其置于全片结构上的承上启下。在此前的研究中,有学 者以精神分析理论将此梦境看作“自我”与“超我”的 对子[3] ,有的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将其分解成欲望的一 对“镜像”(大他者的凝视与对象a) [4] 。笔者认为“自 我”与“超我”的对子将问题复杂化;以拉康的理论理解 此梦,更多是从黑泽明的角度出发,认为导演掌控全局为相同的新能指(影武者)植入旧所指(真信玄),姑且不 论拉康对于所指的批判(拉康不会承认将所指植入能指的 说法),此梦为剧中人假信玄所梦,无法延展到对黑泽明 的精神分析。此梦本就拥有非常简练明显的结构:第一部 分影武者被死去的真信玄追逐;第二部分影武者追逐死信 玄无果。成为他人所带来的恐惧在此非常清晰明确地被梦 解构成了“无法倒退回到自我”和“更无法前进触碰到实 在”,所呈现出为极为典型的佛教“无间地狱”的结构。 而以此梦为节点,本片结构也非常完美而清晰明了。
成为一个人的前提是放弃此前的自我,这种双重紧 逼的痛苦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假信玄。最终可以看到,相比 于被逐出武田家失去权势名利,“信玄之死”(实际宣布 死亡)才更让影武者悲痛不已,自己所追逐成为的那个人 已经确实的消失。而本片最后的高潮便是武田家“风林火 山”军的殉道自杀,残破的家旗与横陈的士兵让假信玄几 近疯狂,他既成了也没有成为武田信玄,影武者延续了武 田家三年的威严与势力,在此意义上他满心欢喜甚至自满 到去骑真信玄的坐骑;他所有的成功被简单的否定,仅仅 因为从黑马坠身就再次落为草民,但他此时回到草民生活 中并无法找回自我——那个成为武田信玄前的“乡野之 虫”。武田家与象征着信玄精神的“风林火山”的溃败也 让那个一直徘徊在无间的影武者走向死亡。
假信玄原是无妻无子的浪人(影片没有明确交代,无 论如何看得出他并不关心),但在进入真信玄的社会关系 时,觊觎的并非权力、钱财、美色、名声,而是真信玄的 孙子竹丸。这实质上是“成为一个人”最可怕的一点—— 对私人情感的侵入。假如此前仅仅是成为“甲斐之虎”, 那在竹丸之后影武者似乎想真正成为“武田信玄”——从 这个形象再到这个真正的个体。但这其中是否涉及镜像与 视点的设计观众不得而知,究竟是成为武田信玄让他逐渐 形成了新的自我认知,还是原本就有渴望亲情的情感,黑 泽明在片中并未说明。但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影武者从一 开始“被成为”武田信玄,到后来主动成为武田信玄,便 是其欲望的体现。以黑马为标志,影武者被宣判他永远也 无法成为武田信玄;在走出信玄家门后也再无法找回自 我。
三、几组重要镜像
影不等于镜像。本片中出现了至少三次镜像, 一是梦 中的浅水倒影、二是终幕河中相向而流的军旗与假信玄的 尸体,此外还有一处跨越时空的镜像——随大瓮沉入河底 安眠的真武田信玄与浮在河面上的假武田信玄。
第一组镜像的隐喻较为明显。梦中在一个远景镜头内 同时出现了真信玄与假信玄,真信玄追逐,假信玄逃窜; 而当假信玄发现真信玄消失不见时, 一个全景镜头展现了 在诡谲梦境中茫然的假信玄走在浅水中,水中倒映着他的 影子。此时,梦与现实颠倒,假信玄成了本体,而消失的 真信玄则映在水面上。假信玄慌乱中踏碎了水面,飞溅的 水花乍看如泥泞,镜像也完全消失了。梦中假信玄暴力性破坏了二者的中介(水面), 一方面成了之后影武者决心 成为武田信玄的伏笔,另一方面也是假信玄一生的心结所 在。
第二组镜像则以一种时空咬合的方式呈现,迈向河 岸、满身是血的假信玄缓慢坠入泛蓝的河川,而风林火山 之旗则以半浮的姿态流动在水中。最终镜头切到垂直的俯 角慢慢拉远,相向而流动的旗(真武田信玄毕生的兵法精 髓)与尸体(延续武田信玄的影武者),这一幅画面显示 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戚感。假信玄为了主公之梦(或说此 时已将其化成自己的梦)殉身,对于影而言他的殉道死亡 已经完成了对自我的谅解——此时他已自认为与真身紧密 的缝合,完美的受难赋予了死亡以意义。但黑泽明此时没 有选择从一个小景别去展现,而是以近乎冷酷的角度观 看,同时正向观众宣告最可悲的事实:现实不会给予假信 玄以救赎,他永远无法沉入河底,也离“风林火山”之旗 越来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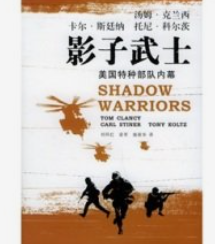
四、物哀与复活
虽然本片处在架空的日本战国时代,但除了人物命运 之外基本也与史实符合。其中的几处日本元素也令人印象 非常深刻。 一是日本特质的佛法,二是能剧《敦盛》,三 是水的物哀。
佛法本身就在战国非常流行,在本片中也着重强调 “无间”的痛苦。在信玄之弟给影武者介绍武田信玄的诵 经房时,影武者只是呆站着看,想进去看时却又被叫走 了,此后影武者与佛法就再无交集。身为乡野强盗的他起 初应是不信佛法,但他却切身实地地处在无间轮回的痛苦 中。
《敦盛》在片中出现过两次,皆是在武田信玄死时的 节点。第一处是武田信玄肉身死亡沉入瓮底后假信玄和家 臣观看《敦盛》,古朴的弦乐与凄惨的唱腔,以及那一句 “人生在世五十年”非常具有表现力;第二处是在武田信 玄的死讯真正公布后,得知此消息的织田信长起身唱了一 曲《敦盛》,对于豪杰殒身的惋惜之情表露无遗。“人生 在世五十年”同时也暗示了日本战国一众名将的结局,既 悲惨又豪迈。
物哀必然是日本文化无法避开的话题,本片最大的物 哀意象是水。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水带走逝者、淹没记忆。 片中三次重要的死,武田信玄尸体沉入湖底,湖边赴死的 武田家军队,河川中的影武者尸体,正如佛教中的忘川, 那一方湖和一条河流分隔了生者与死者。
此外本片一个颇为有趣的元素是基督教。第一次出现 是顶着天主教式的传教士。为何黑泽明要在战国时代片中 插入基督教看似这么突兀的元素?这个教士对于剧情没有 任何推动作用(给信玄看病可以用普通医生),那设计其 难道是为了展现此片的“国际性”?而后,片中第二处基 督教象征就是织田信长同德川家康谈话时的葡萄酒。葡萄 酒即是基督之血。在此笔者认为此片中的基督宗教指向的 应是复活者耶稣,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少于无》中论及耶稣的殉身时说上帝此举并非为了拯救世人而是展现“多 余的爱”,因为“为世人做完全不需要做的事情”显示出 上帝无限的余裕[5] ;而在此处,身为人类的武田信玄无法 借由神迹复活,却以一种与“多余的爱”完全相反的方式 复活了,反而是人对于“缺失”的欲望构建了这次复活。 武田信玄不再是名为“武田信玄”有着喜怒哀乐的个体, 而是成了社会的共同观念、权力景观、以不在场构建在场 的威严,他便以一种复活者的姿态成为时代、社会的共识 (无论是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都畏惧于武田信玄未死而不 敢贸然进攻武田家,对于全天下的将领皆是如此)。
五、结语
本片值得思考的细节还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 概念便是“影”,“影”是颇具哲学意味的意象,同镜像 不同,它并非“存在”,而恰恰是因为“不存在”才被人 们认知。构成影的条件有二, 一是本体、二是光。在《影 武者》中我们能很迅速地指出本体是武田信玄, 但却无法 确定一个确定的光源,它可能是社会结构、他者凝视、自 我预设,最终建构出了“影”,无论如何可以较为肯定的 是以单纯的“镜像理论”来研究“影”是不足的。镜像的 建构来自社会交往,我们正是将他人的情感同自身相联系 才建构出自我的镜像;而光源却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结 构,我们被迫勾勒出我们有限的边界。
影武者并非“影”本身,而是在本体死亡后企图维 持“影”的人,因为只有“影”存在才能证明此人的实 在(如同传统恐怖故事中鬼魂没有影子的说法)。但问 题在于,立体多彩的人可以被光源构建出平面纯黑的影 (“有” → “无”),又如何从单调的影还原一个生动的 人呢?这便是影武者的悲惨,最后他失去了原本“乡野 之虫”的自我,在有与无的边界中模糊成了一个单纯的符 号。即使是自以为凄美的殉道,也只是旁人眼中的癫狂与 悲剧。
参考文献:
[1]伊藤润二.伊藤润二恐怖漫画精选4:窃脸贼[M].台北:东立 出版社,1997:3-32.
[2]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
[3]曲雯,韩强.以精神分析理论解读电影《影子武士》[J].新闻 传播,2014(05):296.
[4]刘潇.试论黑泽明电影的精神发生与结构延展[D].苏州:苏 州大学,2014:49.
[5]Zizek,Slavoj.Less than nothing: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M].London:Verso,2013:6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