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瑞麟书法观研究论文
2023-05-17 09:15:57 来源: 作者:xiaodi
摘要:贺瑞麟作为晚清关学的代表人物,一生恪守程朱理学之立场,复兴关学是其毕生理想,对于其主流研究也大多围绕于此。然先生在治学之余也精于书道,现仍有许多书迹遗留关中,本文旨在通过对集中体现其学术思想的《清麓丛书》关于书论题跋的梳理,理解其将书法作为经世致用工具的原因,阐释其“书如其人、书以传神”的人格美学品评观,并试分析儒学思想对其书法观的渗透。以期了解以贺瑞麟为代表的传统儒士对于书法的观点及态度。
摘要:贺瑞麟作为晚清关学的代表人物,一生恪守程朱理学之立场,复兴关学是其毕生理想,对于其主流研究也大多围绕于此。然先生在治学之余也精于书道,现仍有许多书迹遗留关中,本文旨在通过对集中体现其学术思想的《清麓丛书》关于书论题跋的梳理,理解其将书法作为经世致用工具的原因,阐释其“书如其人、书以传神”的人格美学品评观,并试分析儒学思想对其书法观的渗透。以期了解以贺瑞麟为代表的传统儒士对于书法的观点及态度。
关键词:贺瑞麟;书法观;程朱理学
一、贺瑞麟生平与理学思想
贺瑞麟生于道光四年,字角生,号复斋,陕西三原县人。自幼喜读经书,道光二十年,在三原县孝廉王次伯先生处求学,《先君行略》中记载:“先生教士,先器识本经外,每日讲《小学》及《道学辨》一二条,先君亟是之。”道光二十二年,肄业宏道书院,次年,参加科考一举成名,秋季乡试未中。道光二十七年,受学于名儒李元春门下,但此时并未放弃科举求仕途之心。后多次考试失利,直至在《答原坦斋太守》中表现出弃科举、圣学须在程朱理学中求得的想法。他写道:“麟之始学亦尝不废举业,而心辄厌之。知学求为己,乃泛滥诸讲学之书,卒不得其门而入。中间闻师友之绪论,退而求之《小学》《近思录》,始稍有以窥程朱之学,真得孔孟以来相传之心法,其所以致力则必居敬穷理为纲要,于是屏去世俗之陋习,而惟程、朱是守,不敢有他途之趋。”此时贺瑞麟已对早年追求的科举之路心生厌倦,认为应为己而学,摒弃其他学说,唯有程朱一脉是孔孟正流。此后一生以维护儒学正统为使命,通过经世济民、以礼化俗方式重建社会伦理秩序,重视儒学经典文献的整理与传播,以清麓精舍为基础,创办正谊书院,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办学宗旨,注重实学,着力以正学正人心、正世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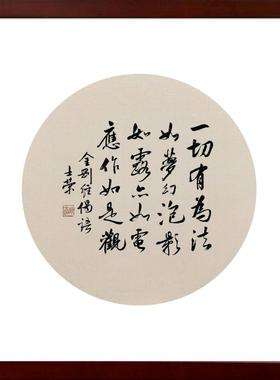
《共学私说》一文中,从本体、工夫、知行等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贺瑞麟的理学思想内涵,其核心内容可分为六个方面:“天性本原、圣学标的、涵养要法、格致实功、身伦交修、出处合道”。“人性之纲,乃复其初”,圣学的实质就是复初人的本性,使人向善、成善。具体做法便是:“居敬穷理、存养察省”,通过格物知言通晓义理,便能不致身心放逐,慎独慎行,存心养性,最终将“理”在治学处世中体现。由此,不难从中看出他对克己向善、存养修身人性要求及成己成物、有体有用的经世之精神。
二、“道为之上,书为末技”的经世致用思想
晚清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为救亡图存,更多人从偏重学术本身向关注时务转变,总体学风充斥着功利主义的思想,而书法恰恰是不带有功利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基本并未涉及政治现实,主要是诉诸个人性格、传达精神、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于是,这两者间便产生了矛盾,但由于毛笔依旧盛行,书法不至于顷刻消失,于是产生“应酬书法”这一概念。白谦慎先生在《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中,将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种。应酬即是为了应对各种社会场合而作书。尽管贺瑞鱗并未为官,却与县令及乡绅保持密切联系,其意在筹集款项、积攒人脉,进而可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清麓文集》收录了大量贺瑞鱗字画题跋,大部分便是给这些县令乡绅帮忙题跋,旨在“礼尚往来”,维系人情关系,“应酬书法”为晚清书法发展的重要形式。如今遗存的贺瑞鱗作品,以对联为体式的不在少数,而对联正是应酬书法最主要的形式,其最重要用途便是作为生活中的礼品相送。因而可以看出,贺瑞鱗的这些作品可能不是为了获得审美享受,不是为提高书法艺术水平,而是为了基本的书信交流、人情交换。书法作为其传播理学思想的一种工具,是为了使用和实用。
从儒家哲学理论出发,可以产生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一种把书法看作与六籍同功;一种把书法看作无关大旨的末艺。显然,这一时期,大多文人选择了后者的立场。与贺瑞鱗同一时期的晚清官员阎敬铭便认为:“吾乡读书人无论其他即写字末道亦无真用者(心用力)。”清末康有为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贺瑞鱗也不例外,他在《论书偶存跋》中提到:“余窃读程子(程颢)‘王虞颜柳,诚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每思之,辄觉汗下。学者读此书,余谓尤不可不进此一解也。”“王虞颜柳”为晋唐书画大家,贺瑞鱗没有对其进行肯定,而是认同程颢所言“一生经历全用在(书法)上,不仅浪费时光,也丧失学道之志”,劝诫善书者也应知“道”。正所谓“书虽小技,其精者也通于道焉。”
清初顾炎武有云:“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贺瑞鱗看来,力挽狂澜的救世良方肯定不是书法,而是传统儒学笼罩下的纲常名教,是对“礼”的推行,用“道”来治理世界。所以,《清麓文集》中字里行间是对“道”“理”的推崇,“习礼”“修德”才是第一要义,而“书”只是追求这一目标的工具,是追求“功利性”的一种应酬,因此书艺并不被士人所重视,使用这种手段,最终目的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贺瑞鱗的书法品评观表现出对书家“人格”的重视。
三、“书如其人、书以传神”的人格美学观
(一)书以立品为先
古语常言:“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从古至今,在中国总有这样一派艺术家,他们认为艺术不仅仅是玩弄技巧、纯粹抒情的事,艺术创作虽是个人活动,但含有社会意义……艺术家应有正确的道德意识,通过作品,把这一道德意识感染给别人。明代傅山在《作字示儿孙》诗中,一开头就说:“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清代朱和羹在其《临池心解》中也指出:“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正如苏轼所言:“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显然,贺瑞鱗也属于这样一派书家。他所题跋的这些墨迹书者多为国朝重臣、秦地高士、乡贤学者,其中不乏左宗棠、林则徐、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有方孝孺这样杀身成仁、无惭名教者,也有王弘撰、李雪木这样的关中大儒,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多可被称为“士贤”“君子”,他们重气节、真性情、有风骨,人品高洁,德行高尚,题跋中无一不对其品性啧啧称赞。
《邑侯赵孚民所藏来阳伯先生墨迹跋》:“吾乡来阳伯先生以书法名一时,后世多争宝之。然其性情气节之高,经济文章之美,则固鲜知者矣!……翊良友于青云之上,道义之途,则赤衷可暴。”《三原县志》记载:来阳伯先生“曾参藩大梁,迁山西右布政使,治兵云中,北虏数万骑突至城下,来复着戎装登城指挥,战守七日夜,虏回退惓。偕饷修城,司农告匮,忧愤成疾,卒于官。”可见来阳伯是一位气节坚贞、赤诚务实的文人,但却因书法出名,而被人淡忘其性节之高、文章之美,有经世济民之才干,这是贺瑞鱗所怅然的。
《刘石庵先生墨迹跋》:“顾先生人品事业继述文正,为国朝贤宰相,而独为书名所掩。岂知先生固能重书,非书能重先生也……”刘(石庵)墉为国朝宰相,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世人曾赞誉其“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可见品行之高,而却因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贺瑞麟为此抱不平,认为先生品行高尚因而书艺高超,而不是书法令其人出名。
“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法,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表白,是入世出世的心灵图示。在贺瑞麟看来,书者的人格、气质才是应被首先关注的,因而这些题跋中常出现“又非独其书之玩而已也”“又不独书法之妙而已也”“独字画而已哉”的论断,提醒观者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二)书如其人,书以传神
中国人自古便极讲求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的追求。孔子曰仁,孟子曰义,老子曰道,庄子曰心,无一不是对人格对精神的高度凝练和追求。书法,作为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独特艺术形式,自然也徜徉在人格追求与传统精神的视野中。刘熙载《书概》言:“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总之,如其人而已。”作品可以反映创作者人格魅力,传递书家志向、学识、精神。
《温纪堂画跋》:“吾邑霸昌公文学政事已见邑乘,书画亦重一时。画师王麓台识者谓其浑厚苍老。此幅虽非极,然亦得其人矣。”温纪堂师学王原祁,识其画者多谓:“浑厚苍老”,虽然所跋画不是极品,但因其人品格高尚,其画也深得其精神。
《李雪木帖跋》:“雪木先生在国初为吾秦高士,其所着槲叶集,学士大夫争欲快睹。而字画真迹传者实罕。……不惟笔势奇逸超出尘,而文亦雅类漆园,心境洒脱自可相见。至其发挥淡字,尤非先生高识远见未易有此。因此益思淡而不厌,吾儒下学为己之功,知先生之所得深矣!”李雪木为明末清初的颇具影响的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共称“关中三李”,他的思想继承了张载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提倡赞扬精神的能动性。贺瑞麟以为其书不仅笔势奇异出尘,文章也雅似庄子(所写),可见其超然外务洒脱心境。董其昌说:“撰述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极才情之变,可以无所不能,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浅者,终莫能近……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谓之淡。”“发挥淡字,平淡天真”的作品出于雪木先生性情的自然,薄名利、远世俗的心态,高识远见的个人修养。
《林文忠公书跋》:“林文忠公当成庙末年以身系国家安危,天下想望其风采。至心画之妙,世亦莫不宝贵。兹临所谓致爽轩数十字,秀劲之气溢于楮墨,贤者固无所不能也。子余中翰勒石以传,盖慕公之为人。而其词意若萧然物外者,亦公有深契焉,又足见公之雅致矣!谨缀数语以志仰景。”林则徐办夷务、剿粤寇,身系国家安危,其字秀劲有力,其词意超脱绝
俗足见公之高雅情致,贺瑞麟仰慕其为人,并感叹“贤者无所不能”。这里的“贤”显然不单指艺术上的才能,而是指向其接人以诚之人品、视死如归之气节、经世济民之操守、大义凛然之情怀。
《左侯相所书正气歌跋相国》:“相国左侯所书文文忠公正气歌,笔墨亦挟风霜,可敬而仰。仇伯学教元刻之清麓,学者读诗歌亦有资于养气,独字画而已哉?”唐时张怀瓘便将“风骨”与书法审美相融合起来:“然智则无涯,法不固定,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主张抒发真性情、传递风骨的作品称之为佳。“左宗棠”“文天祥”“正气歌”,仅见三词,已经感受此帖之气势磅礴,加之笔墨亦含风骨,足有资于养气!
《方正学书跋》有言:“尝读所著侯城集者亦皆磊落俊伟,直追昌黎。至于心画之妙,世所罕见,往见石刻行书,气魄实类晦翁。合阳王君捷三所藏兹幅七绝一首,其意亦非苟然,或为太祖伐暴救民而发欤!而真楷端严尤可宾贵,刚正之气凛凛逼人,真可畏而仰哉!”名儒方孝孺石刻行书,气势恢宏,楷书有刚正之气、大义凛然之感,贺瑞麟将其与“圣人之徒”韩愈相提并论,慕其磊落俊伟。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涵、由内而发的宽博气象是贺瑞麟更为敬慕的。
《岳忠武书出师二表墨刻跋》:“横逸奇秀,生气逼人,两贤心事俱出纸上,展卷敬观,不胜忠义之感,为题其后,怆然者久之。”诸葛亮当年“出师未捷身先死”,岳飞“直捣黄龙志难酬”,我们可以猜想“两贤心事”或许就是岳飞《五岳祠盟记》里所言:“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土上版图”,明初,太祖朱元璋得此墨本,亲笔撰写赞其书曰:“纯正不曲,书如其人。”忠勇之气概,悲壮之情怀具出于纸上,令人难以释怀。
纵观这些题跋不难发现,贺瑞鱗对作品的赏评很少在狭义技法层面论述,基本无涉笔法、章法、结构,而始终离不开对书者人格的欣赏,在艺术美与人格善之间,其更偏向对于“善”的探讨,因有善,才有美,尽管他所题跋的这些书者大多未能在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多德胜一筹,积极入世,以作品为媒介表达忧国忧民情怀与卓尔不群的精神,而这才是贺瑞鱗最为关注的。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写道:“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这一观点也适用于书法美学。自古至今书法审美批评史上,人格品评经常作为评价作品及创作者的标准之一。”明末清初傅山、与贺瑞鱗同时期的刘熙载,都存在“书如其人”的书法审美倾向,贺瑞鱗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统治的更迭,深感学术之坏渐浸人心,因此希望复初人的本性,使人向善、成善。刘熙载也试图用孔孟之道提高道德修养以挽救世道人心,傅山身处社会动乱之际,明亡后他一直以“遗民”自居,他十分抵触“二臣”身份的赵孟頫,认为其学术不正,痛恶其书浅俗、软媚无骨。贺瑞鱗在《王无异荣弆帖跋》中也表示认同其观点:“今人学书不学颜柳而学吴兴(钱选、赵孟頫等被称为吴兴八俊),无怪乎世道之日下也”,在他们看来,“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以闲圣道也。”相反,作品也常被视为书家人格化的产物,人的品德、抱负、见识、学问也会映射在作品当中。
将人品和书品联系起来固有其伦理价值,敦促了书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但也会因此导致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混为一谈,带来书法品评的片面化,过分夸大伦理的力量,并减缩艺术的含蕴,客观上削弱了对书法本体的评析力量。实际上,书品和人品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包含着对象的人化,又包含着人的对象化,是一种主客观统一的活动。“人格”应与“笔墨”相统一,德艺双馨、尽善尽美是书法人格品评的最高境界。
四、儒学思想对其书法观的渗透
无论是经世致用、书为一技,还是书如其人、性情为先思想,不置可否都受到了儒学的影响,《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是儒家思想核心,而适情消遣,有利于修身养性,然有主次轻重,但四者皆不可或缺。可惜,这种超功利主张,被孔子的后学们加以发挥,过分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礼记乐记》)的成分,把艺当成志于道的余事了,逐渐形成“重大道,轻小术”的观点。因此大多文人不愿将书法作为主业,书法的艺术地位并不被重视,认为专攻于此是玩物丧志的表现,是世道日下征兆。“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吟诗饮酒戏谑度日。”朱熹反对苏轼、黄庭坚的放浪纵情,愤恨其饮酒作诗,虚度光阴,不务正业。更有观点甚至认为书法是一种“害道”的存在,因为在儒学学者来看,“艺术”无“真理”,是表达私意的方式,儒者以诚敬为天理,倡导持敬克己,正与贺瑞鱗“专心持志以居敬,诚心克己以改过”的持敬涵养工夫论观点不谋而合,即圣贤之学要在存养省察处下功夫,敬统动静,持敬是根本。也是因为这种持敬克己思想,使文人生命的情调与儒者人格理想之间所存在的尖锐对立施之于书法,形成两种对立的艺术观念,出现前文所讨论的德与艺两种书法品评标准问题。
尽管书法于道无所裨益,但文人却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尊德性而道学问,为人类社会寻找“圣道”是有学之士的毕生追求,“内圣外王”是其修身为政的毕生理想,内圣成己,指的是自律克己,提升个人道德意识,以期达到人格的圆满。在内圣之学的指引下,避艺术之短,扬道德所长,卒合文人于其身,也使得书法艺术重心逐渐转移对书家的关注。“书虽一艺,亦不可无本。览者其尚知此意夫!”字体,字体是人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标志。此外,其还可以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改善单调无趣的发展模式,充分展现文化知识的应用价值。由此可见,在未来社会建设发展过程中,既要关注书法教育的实施情况,又要根据现代革新方向提出全新的教育管理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在潜移默化中继续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书法教育革新发展中,唐代楷书笔法的学习传承非常关键,其既可以为现代楷书发展提供丰富资源,又可以让学习者掌握更多优质的传统文化。因此,在现代书法教育工作中,要依据全新的观念去欣赏和研究唐代楷书书法作品,积极学习其蕴含的笔法渊源,注重结合时代审美需求,创作出更多楷书作品。这样既能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可以在借鉴中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书法艺术作品。因此,在我国书法创作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要加强书法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对现代书法基础教育体系的探讨,以此在传承唐代楷书的同时,取得更为优异的艺术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李贵亭.唐代书法与雕版印刷术的关系研究[J].艺术品鉴,2020(06):242-243.
[2]祝帅,丛文俊,杨吉平,等.弘扬唐楷正大气象——“唐代楷书研究与当代楷书发展”学术论坛纪要[J].中国书法,2020(10):162-164,166-167,169-171,173-179.[3]曹文韬.现代科技融入诗骚传承与草木认知的实践探索——以“拾色方物”小程序为例[J].文学少年,2021(15):385-387.
[4]胡安宁.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传承:实践—认知图式导向的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20(05):135-155.
[5]卢致达.文化传承视域下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及发展趋势研究[J].绥化学院学报,2021(06):102-104.
[6]周金声,陈慧颖.认知中华语文价值勇担传播中文使命——“新时代重新认识中华语言文字的价值与使命”线上学术研讨会综论[J].语文教学研究,2021(03):1-2.[7]李占涛,李超.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09):81.
[8]李梦婷.当代美育教育背景下中国钢琴作品传承与艺术研究[J].艺术评鉴,2021(14):134-136.
[9]华永明,李芳.技术知识传播影响下的民艺生态变迁与传承路径研究[J].西部皮革,2021(21):126-127.
[10]赖翩京.文化理解与传承:语文教学的应然取向[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20(12):3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