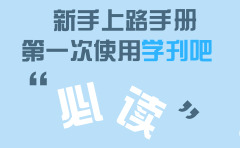在胡志明港的三十五天论文
2025-11-10 16:45:58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钻石号”货轮此次来胡志明港,是准备卸一万八千吨散装化肥。作为船长,刚靠好港,并不能马上休息,必须接待港口多个部门的来访官员,填写各式公文,办好入关手续。
把如此怪异的喷嚏跟那个女孩的电话联系起来,是在第三次喷嚏后。
“钻石号”货轮此次来胡志明港,是准备卸一万八千吨散装化肥。作为船长,刚靠好港,并不能马上休息,必须接待港口多个部门的来访官员,填写各式公文,办好入关手续。忙完这些,已过中午,很是疲惫,我准备躺在软椅上小憩一下,但这时,传来了“嗒嗒”敲门声,声音柔和,颇有节制。我只好提高声音说:“请进。”门推开后,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颇有风度地站在门前,臂上挽着一只红色精致小包。她对我稍稍弯了一下腰,礼貌地说:“船长好!”我知道,她是名做伙食的越南妹。我虽是初次来胡志明城,但此前去过越南多个港口,每次靠好码头,总免不了这样的靓妹登轮。她们一般戴着宽边软布遮阳帽,身穿蓝色紧身牛仔短裤和白色无袖衫,伸出白生生的长腿细臂来——越南虽终年阳光强烈,但奇怪的是总晒不黑她们的肌肤。她们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特别在越北),乍一看,你会以为是个中国人,其实很可能写不出一个汉字。她们会长时间缠住船长,要你买这买那。于是就会有些风流韵事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点点头,她就进来了。
近了看,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明亮灯光下,那张看似未经妆饰的脸完全可以用“俏丽”来形容。五官精致,线条柔和,生动布置在她小小脸庞上,一个微小变化都能传递出某种细致情绪。她的肌肤光洁如瓷面,我相信凑近了一定能在上面清晰地看到倒映的光影,右耳下方的一颗心形红痣因此夺目而出。她隆重地穿着粉色国服——奥黛,使得窈窕身姿毕现无遗,散发出别样气度,以致房间内的物品和空气似乎都跟着摇曳了起来。
她见我看着她,开口道:“船长先生,我叫春玉儿,是这里的伙食供应商。初登贵轮,希望照顾一下我们哦。”声音虽有点娇嗔,但很有分寸。
但“钻石号”轮几天前刚在湛江港上足了食物和淡水。我还未吱声,她接着说道:“我查过,您船是第一次来,可能不太了解哦,我们是这里做得最大的,一贯注重信誉,所有菜品都保质保量,价格公道,而且服务一流。”她眉梢轻挑,笑道,“这些,您能打听到的。”
相信对于任何正常男性来说,无视“美丽”的存在都是件困难的事。它如同一种特殊气味,只要吸入,就会身心愉悦、神清气爽,甚至精神亢奋,类似于某种化学反应。何况对于我们这些长年离家似乎母猪都能琢磨出双眼皮的水客呢?我颇后悔当时采纳了公司的建议,在国内上了太多的生活物资,尽管那里东西的确实惠。
她站在那里,略带俏皮地微笑。
可我还是说道:“抱歉,我们刚在国内上足了补给,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
她伸手捋了捋垂在耳边的几缕发丝,说:“没关系的,后面还有机会呀。”
似乎只是一个转念,我问道:“废品,你们要吗?”
她当即笑着说,“当然,要的呀。”
“那你找一下我们大副试试。”我说。
她点点头,随后又是莞尔一笑,道了声“谢谢”,转身出去了。
她在我房间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但出乎意料,据晚饭时了解,船上废品竟然已被水头在湛江港处理了。我倒是有些失落。
当晚我就接到了她的第一个电话,问为什么明明船上有不少废品(下船后从同行那里知道的),却对她说没有?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因为不清楚实情,电话里我一时没法回答。后来问了大副才知道,下午船员确实说谎了,是作风比较浮夸的水手长当时联系了一个报价比较高的买家,于是搪塞了大副。这是我们的问题。可就在我放下电话时,左侧鼻腔忽然痒了起来,我抽吸了一下,没有用,瘙痒感更甚,接着右鼻腔也痒起。随之,第一个喷嚏登场了。它那么猝不及防,仿佛一次突袭,我的胸腔猛地鼓起,腹部和颈部肌肉倏然收缩,一股热乎乎气流直喷出来。接着,五六个喷嚏连贯而出。但奇怪的是,过程中,我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感觉是有的,我感到一阵腹痛、喉咙干裂和轻度耳鸣,可鼻腔内真的没有明确感觉,连该有的那点快感都没有,只有气体疾逝留下的一点肌肉记忆,就像飓风扫荡后的原石通道。不过,后面没有继续。

我并未在意——只是一次怪异的喷嚏罢了。
昨天上午十点半,她来了第二个电话,是想得到上个电话的回复。我解释并表达了歉意。
但之后,第二次喷嚏产生了。
这次喷嚏足足打了一分钟,几乎是一次气流喷射表演,胸腔如一只巨大气泵,强烈气体不断涌起,我的机体放下一切,全身心投入这场喷嚏中。事后副作用是明显的,我精疲力竭、腹肌剧痛、头昏眼花。但喷嚏虽强烈,恢复却较快,除了腹肌、喉咙还有些异样,“半小时前曾有过强烈喷嚏”的迹象几乎消失。这次我忍不住登录了百度,搜索与喷嚏相关的词条,发现看似简单的喷嚏并不简单,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统计后,大概有以下几条:喷嚏是由于多种原因(过敏、气味、疾病及心理)刺激后身体不自主做出的保护性动作,人为无法控制,有人因为故意抑制喷嚏引起了胸腹肌撕裂、肺部穿孔,甚至因呛气窒息而亡;喷嚏是一种巨大生物能量释放,瞬间气流时速可达一百八十五公里,等同于中高级台风。过多或过分强烈的喷嚏可导致身体衰竭,甚至死亡;鼻腔神经受疾速气流刺激,会产生强烈快感,但也因此耗去巨大体能;《邶风·终风》有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喷嚏是来自情人间的思念,属于吉兆。莫非我有好事将近?
今天,是她打的第三个电话,想邀请我明天下去走走,我们的行话叫踩地气,说愿意做我在胡志明城最好的导游。面对一个美妙女孩的邀请,说不动心是假的,我眼前甚至瞬间浮现出跟她一起慢慢走在胡志明城充满风情老街的光景。尽管我知道其实是做不到的,至少以她供应商的身份。
可一放下电话,第三次喷嚏来了。一股气浪突然箝住我,让我大幅度不停仰俯,如同祷告中的虔诚信徒。喷嚏声澎湃激昂、滔滔不绝,飞扬在船舶傍晚的宁静中,突兀而怪诞。船员们应该听到了。
平息后,我终于陷入了迷茫,疑窦丛生,这些怪异的喷嚏从哪里来的呢?似乎并未经过怎么思考,“电话”两个字就跳进了脑海,电话——是的,每次喷嚏前,我都接到了她的电话呀!电话导致了喷嚏!得出这个结论时,我的血液既似沸腾,又似凝固了。
答案如此荒唐!几乎匪夷所思。电话与喷嚏完全无从联系,遥不相及呀。我努力克制自己,一切还得验证,不过不难,只需等待下一个电话——她应该还有电话过来。第五天上午十点,手机响了,看到号码,我心跳猛地加速,手脚发胀。她果然来电了!
“船长先生,下午可以去拜访一下您吗?”声音里有种楚楚之情,我紧绷的神经竟忽地松弛了下来。
“呃,下午?可是——有点忙。”
“没关系,可以再约的。我是重感情的人,生意嘛,终是随缘的,就像我选择你们船。当然,如蒙您照顾,就更好啦。”
又闲聊了几句,我们放下了电话。
我随后闭上眼睛,开始等待。
一股气流忽地从胸腔处以雷霆之势向上逆冲,随之在鼻腔中连续爆破,如一挺连续点射的马克沁重机枪,持续了一分多钟。我的身体在强烈震荡中不断下蹲,最后瘫坐到地板上。头脑里一片模糊,双耳不住嘶鸣,满面涕流,身疲力竭,最后气若游丝。再打下去,十有八九要一命呜呼了。
这次喷嚏差点要了我的命,是名副其实的能量爆炸,尤其后面几个喷嚏已达到我生理和心理的极限,生命被悬于生死关头,随时可能丧命,以致后来每每想起,总有九死一生之感。但惊惧之余,一个事实无疑确立了:女孩电话的的确确导致了我的喷嚏!不管谁怎么想,它都如真理般存在。我需要做的是:后面怎么办?或许这个女孩的电话不必再接了。删除她,不,拉黑她!从此山陬海澨,相忘江湖。可待平静后,我的想法却变了,心里有了不甘,想弄清这件事的缘由。朋友,如果是您,会怎么做呢?因此,毫无疑问,我得跟她保持通话。从此以后,隔上一两天,我就会接到她的来电,喷嚏自然每次都不可避免。胡志明港的散装化肥需现场打包成五十公斤装的市售小袋,又因处于雨季,频繁降水,卸货变得极其缓慢,完货日期一再推迟,于是,喷嚏基本成了常态。船员们也知道了,见怪不怪。但这些喷嚏并非持续加重,而是时强时弱,没有规律,或许跟女孩当天心情有关。我渐渐陷入了一种困境——越怕接她的电话却越等待她的电话,如同身陷泥沼,越挣扎越深。
不久,另一个让人不解的现象出现了,她的来电慢慢失去了理性,涉及内容越来越光怪陆离,游移出一个女孩的常识范畴。有一次她跟我谈起肉体疼痛——一种切割加撕裂的凌迟之痛;还有一次提到了梦境,里面有风暴巨浪,漆黑恐怖的深海以及长满獠牙的白面食人鱼;一次她竟谈起女人的放荡,电话里不时传出令人春心摇曳的呻吟声;又有两次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哭哭笑笑,我的手机仿佛成了她的发声器。她似乎在为电话打电话了。
但每次喷嚏,无论轻重,都是对我的折磨。我默默承受着,如同一个赎罪者。我觉得自己与她,已有了某种默契,为着某种不明的目的。
为了排解困扰,第二十一天上午,我约了代理,让他带我下去走走。
安(ANN)是一个热情且严谨的四十岁男人,中等身材,体态微胖,有点秃顶,宽宽的脸膛总是一片潮红(该是个嗜酒者),远看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除第一天办理进港手续外,这是他第二次来船。我们驾着车,去了建于十九世纪的圣母大教堂,去了西贡中心邮局和胡志明市政厅,这些法式殖民建筑如今成了胡志明城的著名景点,成了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战争已被忘却,人们走出大厅时,脸上都带着笑容。人的记忆天生带有选择性,最后留下的一定是他们想要的那部分。
天黑后,我们去闹哄哄的范五老街吃了越式春卷,还有带饭烤肉。切成薄片的猪排肉被烤得外焦里嫩,掺上罗勒嫩叶,清香四溢,又喝了几听西贡啤酒才回来。
但当晚,竟做了个关于春玉的梦。我跟她走在胡志明城深夜老街上,灯火一片辉煌,霓虹闪烁,各种嘈杂声簇拢过来,又奔突而去。她依然穿着粉色奥黛,身材高挑,走着富有弹性的步调。偶尔回头时,脸部线条那么柔美,简直像一种设计,强烈街灯下,脸颊上似敷了金,高贵而神秘,右耳下方那粒红痣不时地放出璀璨之光。可是后来,走着走着,她的身影却慢慢变薄透明,最后竟完全消散了,无从寻觅。
“钻石号”卸货一再受阻,完货时间持续推迟,这期间春玉还是不时打来电话,喷嚏依然如故。那种持续又难以确定的痛苦,并非一句话就能说完。我只能坚忍。第三十五天中午,货终于卸完了。安通知了我,计划在当晚开航。
下午三点,安上船办理出口文件,过程顺利,半个小时搞定了。我让服务生泡了咖啡,在安对面坐下。要离港了,觉得该跟他说点什么。
“安,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春玉儿的女孩?”安抬起头,诧异地看着我。
“二十来岁,做伙食生意的,挺漂亮的。”我补充道。
“你——遇着她了?”安放下杯子,嗓音有些沙哑。
“她来过我们船。”“有啥特征吗?”
“呃,右耳下方有粒心形红痣。”
安靠着椅背的身子矮了下去,神色变得不安,嘴里念叨着,“红牡丹——又来了。”“红牡丹?”我也紧张了。
安闭上眼睛,再次睁开时,双眼已然猩红,如嵌入红脸膛的两粒炭火。只听他低声说:“红牡丹,就是春玉儿。她是这里的供应商,但——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更加困惑。
半晌,他才慢慢说道:“我讲讲她的故事吧。”他挪动了一下身躯,“她其实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越南人,母亲是中国广西人。父母当时做港口生意,日子过得不错,因此在她七岁时,又给她添了个妹妹。”
“但十三岁那年,她父母一次送货回来的路上被一辆重型货车撞了,父亲当场去世,母亲拖延了一个来月。母亲放心不下她们姐妹俩,特别是妹妹,在尚能说话时,一直叮咛她要照顾好妹妹,临终前更是一直不闭眼,她在声嘶力竭般哭喊中再三答应了母亲。或许我们会低估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承诺,但实际情况不是。在族人的帮助下,靠着父母的一些积蓄,姐妹俩相依为命,而照顾好妹妹似乎成了她与生俱来的职责,尽管她自己还是个孩子。为了保证妹妹上学,虽然自己成绩优异,初中毕业春玉就弃学了,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制衣厂打工。制衣厂工作非常艰辛劳累,尤其对一个小女孩,但春玉坚持了下来。妹妹长得很像妈妈,她常常会在妹妹睡着后长久地盯着看,妹妹的存在几乎成为她生活的最大动力和寄托。她如一个小母亲那样照顾着妹妹,尽力让她如正常孩子那样长大。妹妹生活中的一点进步都能给她带来说不清的喜悦与安慰。就这样,姐妹俩慢慢长大了。”
安抿了口变凉的咖啡后接着说:“十九岁那年,命运出现拐点,她决定重操父业,因为她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命运。她的选择是正确的,那时中国过来的货船慢慢变多,春玉不仅会一口流利的汉语,人长得漂亮,而且货品价格公道、质量保证,所以局面很快打开,只一年多的时间,她就开始雇佣工人,生意上了规模。她在港口的名气渐渐变大,因为右耳下有一颗显眼的红痣,大家都叫她‘红牡丹’,但同行里,很多人称她‘牡丹花’,传闻她跟不少船长不清不白,甚至有人说她在出卖色相。”
“虽然生活中不乏追求者,或许由于长期的母亲角色,春玉一直排斥婚姻。但二十五岁那年,她认识了一名中国班轮船长,那人三十二岁,未婚(出事后才知道其实在中国已有太太和孩子)。班轮每周六准时到港。男人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以各种令人瞠目的方式向她表明衷心,最终,她被打动,陷入了爱河。女人真是个感情动物,一旦投入,就很难回头,春玉为这个男人几乎付出了一切。她堕过两次胎,用自己很大一部分收入给他买各种奢侈品。她跟这个男人说,只要他愿意,她可以带着妹妹嫁到中国去。那船长也很爱她,每次都从中国带来礼物,为了能见到她,竟连续在那条班轮上工作了近两年。这样的服务期对一个船长来说是罕见的。春玉觉得找到了真爱。”
安的脸上不知何时浮现出一层粉色的油光,像一枚将要成熟的苹果。
“那一年,妹妹高中毕业,无处可去,被她带来了港口,一起做生意。可半年后,她发现形同女儿的妹妹渐渐疏远了她,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很担心,追问过几次,可妹妹总是一言不发。但不久,答案揭晓了,原来妹妹也爱上了那个男人。不,是那个男人以惯用伎俩勾引了她,而且已让涉世不深的妹妹怀孕了。”
安再次闭上眼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下面的讲述。
“情况的糟糕超出了应有想象,一切无异于晴天霹雳,春玉根本无法相信,精神几近崩溃,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她冷静下来,做出了决定:自己彻底退出。倘若妹妹真的幸福,她愿意这样做,哪怕因此终身不嫁。可此后时间不长,她从另一个船长那里得知那男人国内竟已有妻儿,这次她真的疯了,等那班轮再次到港,第一时间赶去了责问。就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时,妹妹进来了,不明就里的她以为姐姐竟欺骗自己,还暗中在争风吃醋,爱之极就是恨之极,这里有多个版本,最后法院认定的是妹妹趁姐姐不注意从背后用棒球棍(正是姐姐以前买给那个男人的)打晕了她,失去了心智的妹妹在男人的帮助下,一不做二不休杀死并肢解了她。他们把春玉的心脏掏出,包上帆布坠上重物,沉入了西贡河,或许出于最后一点善心,把春玉的心留在了故乡,其他部位被男人在回航途中抛入了大海。但这颗心竟奇异地在某一天浮出了水面,成了侦破案件的唯一线索。两人很快被捕并供出了实情,由于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妹妹半年后被执行了死刑(被捕前,胎儿已经流产),男子判了无期,但在第二年妹妹祭日那天,不明缘由,暴死于狱中。”
不知何时我手心已渗满汗水,不,我已浑身大汗,全身都在不自觉地颤抖,像忽然患了大病。我无法相信安说的一切!正如我无法相信电话里那些温柔的话语竟是“鬼语”,那么窈窕曼妙的身姿却为魅影,那些悦耳动听的电话铃声居然是阴俯叩击之音!但我又忽然想起“她”说过的——肉体的撕裂疼痛、深海的漆黑恐怖、长满獠牙的食人鱼,我的汗毛彻底倒竖了。
此刻的安似乎也异样了,成了一个模糊幻影,只听他用一种空洞的高声继续说道:“在此后几年,时常有红牡丹现身传闻,有人在西贡河边或码头堆场看到过她,也有人在各类货轮上看到过她,但她的出现日无一跟她妹妹的忌日重叠,之后就会有船长失踪或发疯的报道,类似喷嚏的传闻也偶有耳闻。没人知道她何时会住手。这成了胡志明城长久以来的治安事件,‘春玉儿’也因此恶名远扬,在民间成了恶毒女巫的代名词。今天是她妹妹十周年祭日。我刚刚看了您手机上的来电号码,正是她生前使用的。”
我已彻底瘫倒在椅子上,汗如雨下,气喘如牛。原本亮如白昼的房间迅速暗沉了下去。
傍晚,临开航前,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不看来电,我知道一定是她。这应该是她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了。对于这个来自“地狱”的电话,我力图平静,却因此更加紧张。我止不住两眼发黑、双手颤抖、呼吸急迫、神志混乱,但依然接通了。手机里先是一片寂静,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静”,如枯海古墓,如世界尽头,忽然一道沉重的“呼”气声从耳旁一扫而过,似乎从未知来,又消逝于未知中,随之又是死亡般的寂静。大概三分钟后,我听到一声长长“嗳”音,眼前奇异地闪出一条幽深隧道来,那洞壁破败而潮湿,映射出一片幽蓝之光,一缕灰黑色尘烟正从洞道下源源不断地上升,接着在狭窄阴暗的空间里不住旋转、汇聚,如傍晚时刻刚出巢的蝠群,渐大渐密,最后形如梭、墨如黛、径若尺。这个黑球继续加聚加密,旋转也越来越快,终于达到某个极点,就听“轰”的一声,如墨瓶爆裂,又似积压已久的愤怒爆发,一股浓密黑烟似汹涌乌水沿着幽暗隧壁向前肆意奔腾,速度越来越快。我知道它是冲我而来的。我虽已紧张到了极点,却依然手握手机,做好了一切准备。忽然,我的胸腔开始快速扩张,瞬间膨至最大,喉咙如狮口大张,鼻翼若鹰翅尽展。我打出了平生最大最响的一个喷嚏,两股黑烟从鼻孔里急遽射出,瞬时迷雾毒瘴般弥漫了整个房间。在世界彻底从眼前消失前,我听到房间里传出残酷凄冷却又柔媚至极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