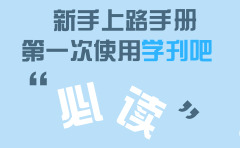重构都市伦理:阿尔比《在家在动物园》中的城市异化与人性救赎论文
2025-10-09 17:59:40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城市是现代性悖论的缩影。爱德华·阿尔比的《在家在动物园》以纽约为背景,通过家庭场景与公共空间的对照,揭示都市生活的精神异化与阶级区隔,并探索都市伦理重构的可能。
摘要:城市是现代性悖论的缩影。爱德华·阿尔比的《在家在动物园》以纽约为背景,通过家庭场景与公共空间的对照,揭示都市生活的精神异化与阶级区隔,并探索都市伦理重构的可能。彼得、安娜与杰瑞的互动揭示人际隔阂与伦理失序,剧作借此反思城市空间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规训,呼吁在城市复杂性中重建人性尺度。
关键词:《在家在动物园》异化;区隔;都市伦理
亲密的溃散:家庭空间中的隐形裂痕
城市既是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亦为权力结构的生成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空间不仅“体现、包含并掩盖”社会关系,也不断被其所“再生产”。①在《在家在动物园》中,私人公寓与中央公园分别成为家庭伦理崩解与公共领域冲突的缩影。家庭空间内,情感疏离与性爱隔离构成了中产阶级“冷暴力”的典型图景。彼得与安娜是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装修考究的住宅中。尽管生活优渥,两人却缺乏有效沟通,日常交流陷入重复且空洞的对话,情感隔阂日益加深。
安娜:我们应该谈谈。
彼得:什么?我们应该什么?安娜:哦。我们应该谈谈。
彼得:对不起。我在阅读。安娜:你总是这样。②
简短几句对话已勾勒出彼得与安娜形同陌路的关系。彼得借阅读逃避家庭责任,实则陷入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状态——本应自主的行为沦为外在的压迫力量。安娜的失眠、自残倾向以及对动物性本能的渴望,则进一步揭示了亲密关系的结构性瓦解。
城市空间通过时间规训与消费逻辑,将个体分割为孤立的存在,促使传统家庭伦理让位于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文明秩序”。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说:“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我们始终不可能在抓住并且拥抱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的同时不厌恶不反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现实。”③彼得的行为正是对现代生活厌恶的一种无能为力的不满。
相对丈夫的冷漠,安娜一直试图主动交流并采取一系列行动,但家庭重压下的种种诡异行为,也将她与丈夫区隔得越来越远:
安娜:你只知道我可以穿着睡衣出门,下楼梯,走出大楼,走上七十四街,来到街角,站在那儿,尖叫。……安娜:下次夜里,我起来,你跟着我。我在厨房,喝杯茶。一天夜里我坐了一个小时……我在考虑割掉我的乳房。(山羊:80)
从失眠到自残倾向的蔓延,安娜的思维逐渐失控。她特别关注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刻意展现真诚的一面,然而彼得并未有反馈。安娜越对亲密关系抱有憧憬,就越意识到彼得对自己的“抛弃”。异化成为狭窄空间的主旋律。

随着城市现代化推进,物质集中带来了身份趋同,却也加深了个体之间的精神隔阂。彼得与安娜的亲密关系逐渐失去激情,变成了机械而空洞的例行互动。正如安娜所言:“也许我们相互爱得太安全了?我们安全吗?我们太……文明了?”(《山羊》94–95)身体的疏离逐渐消磨了彼此间的激情。安娜并非指责彼得在性爱上的无能,而是在渴望一种原始、陌生且直白的性欲关系——一种“成为动物、成为陌生人”的本能冲动。她并不期望通过性爱重建夫妻间的情感联结,只是希望唤醒人身上那被压抑的“动物性”。
阿尔比通过对家庭场景的细致刻画,展现出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层困境:生活空间一方面塑造了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逐渐滋生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异化。在彼得的公寓中,性爱被发配到了空间的边缘。他回忆起年少时的第一次性爱,野蛮粗暴疯狂如同野兽的行为造成了“鲜血直流”的后果,促使他开始自我怀疑,并温柔、周到地对待妻子。在彼此不同的认知背景下,二人丧失了能动性,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浪漫之爱不得不与日常生活展开竞争,并“发出对世间日常事务的同等怨恨”④。
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被无情解剖,即便是亲如夫妻,也存在巨大隔阂。由于内部区隔的不断放大,进一步造成了自我认知的谬误。正如汉娜·阿伦特所强调,自由人的生活需要他人在场。然而正是这块他人在场的空间,使得自我的身份认知被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中,被遮蔽的自我猛烈进攻共同空间,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隔离。
城市的长椅:公共空间里的阶级碰撞
如果说家庭空间的异化反映了私人领域的危机,那么公共空间中的冲突则揭示了城市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在家在动物园》第二幕“动物园”将冲突从私人领域延伸至公共空间。中央公园长椅上的彼得与流浪汉杰瑞的对话,成为阶级区隔与文化符号权力运作的戏剧化呈现。
在中央公园这个“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依然受到隐形区隔,美国中产阶级和流浪汉的偶遇呈现出消费社会中社会阶层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文化符号隐现于其中,无形中发挥着城市文化空间区隔的功能,其主要手法是通过趣味、文化上的差异“区隔”出阶级差异。正是这种在场与缺席的互动中,文化符号权力不仅加深了地理空间上的区隔,而且加大了人际关系上情感空间的断裂。
文化符号权力首先造成了地理空间上的区隔。布尔迪厄指出,审美趣味作为文化资本的外显,具有“聚集与分隔”⑤的双重功能。杰瑞主动与长椅上看书的彼得交谈,不断挖掘交换信息。对于身处贫困的流浪汉杰瑞来说,他在对话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弱势状态。从家庭背景、住所、收入等信息来看,彼得“一年收入二十万,住七十四街,莱辛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山羊:104)他在不经意间说出“哦,你住在格林威治村!”(山羊:105)这从地理区分来看,格林威治村是美国六十年代反文化的聚居地。杰瑞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开始描述自己的居所,是在“上西城哥伦布大道和中央公园西边之间的四层楼公寓,而且是用纤维板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周围还住了一口烂牙的黑美人、拖家带口的波多黎各家庭”。(山羊:106)
面对杰瑞对住所的描述,彼得显得尴尬,这一反应无意中揭示了空间分配背后的阶级排斥机制。作为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他始终维持着礼貌回应,却难以掩饰由空间区隔带来的身份差异。即便两人身处同一公共空间,文化背景的悬殊仍让对话变得艰难,人与环境之间的疏离感愈发明显。
杰瑞反复提及“华盛顿广场”“第五大道”等纽约地标,试图借助这些城市象征唤起与彼得的情感共鸣,拉近彼此距离。然而,城市意象背后的文化背景却构成了新的隔阂。彼得对“阶层”话题感到不适,杰瑞渴望理解与认同,却在文化与阶层差异中遭遇冷漠与拒斥,矛盾反而被激化。更深层的隔阂来自情感空间的断裂。阿尔比关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缺失,而情感本应是跨越阶层的重要纽带。杰瑞试图用共同的城市意象打开彼得的内心,却未能成功。在彼得看来,只有与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空间才承载真实情感,对喋喋不休的杰瑞,他更想逃离而非靠近。
杰瑞的独白进一步揭示了底层生存的残酷逻辑。他开始融入自己的情感讲述生活:邻居总是在哭,“每回我出去进来走过她门口时,总听到她的哭声”;房东太太“又坏又蠢”并且想要拉自己“泄欲”。通过彼得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的事件引发他的好奇,彼得开始对杰瑞的生活有所评价:“你对她的描述……很生动”“太恶心,真是……可怕”。(山羊:109-110)
从杰瑞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他对生活中的日常交往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开始对身边的动物产生兴趣,给彼得讲述“杰瑞与狗”的故事。发自内心的孤独让杰瑞感叹:“动物对我没有感觉……人们也是……大都对我没有感觉”,他决定“讨好这只狗,如果不行……我就杀了它”(山羊:111),最终却爱上了那条狗。杰瑞强调:“如果你无法与人相处,你必须从头学起。与动物相处!”(山羊:114)
杰瑞陈述后内心激动,然而彼得却不理解。在杰瑞真诚的情感攻击和强迫性叙述中,彼得“被迫”投入了“同情”。作为一种独立的情感,同情不会因自己未曾参与而发生变化。无论是房东的性压迫、邻居的压抑哭声,还是“杰瑞与狗”的寓言式关系,彼得的反应均指向城市边缘群体的情感荒漠化。个体人格在进入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使人们感到不安:对情感不自觉流露的担心,私人想象对公共情况的不恰当叠加,都是为了在公共场合保护自己。
事实证明,尽管杰瑞叙述本身就是强烈而有效的情感表达,但在情感差异、文化差异的背景下,不同阶级之间的理解、沟通几乎不可能。在几番尝试后,杰瑞想要被理解的愿望变得愈加渺茫。彼得大呼:“我不想再听。我不理解你,或者你的女房东,或者她的狗……”,而杰瑞似乎也到达了情感的低谷:“我永远是个过客。我的家在上西城那幢恶心的寄宿楼里,在纽约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山羊:116)
当彼得提出要离开时,杰瑞再次重申自己的“动物园理论”,并从言语叙述上升到行为击打。在争夺中央公园长椅的过程中,彼得忍无可忍,两人为长椅决斗,最终杰瑞死于彼得手中的尖刀。杰瑞感慨道:“谢谢你,彼得。这是真的,非常感谢你。”(山羊:121)杰瑞和彼得在生死的最后一刻似乎有了联结,打破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冷漠。
阿尔比以彼得刺杀杰瑞的荒诞结局,象征性地揭示了公共空间中阶级矛盾的难以化解。在物质文明光鲜外表之下,城市早已变成一个矛盾交织的场域——既开放又排斥,既连接人群又制造隔离,如同一个看似包容却充满张力的都市迷宫。
在动物园之后:都市伦理的重建可能
尽管《在家在动物园》描绘了家庭异化与阶级隔阂的尖锐矛盾,阿尔比的戏剧美学并未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他更关注在人与人疏离的裂缝中,寻求人性救赎的可能。正如罗伯特·阿尔特所言,“城市是一种幻景,其消解过程中,一切都被视为持续的、无定向的流体,感受与幻想、清醒与迷梦的界限趋于模糊”⑥。阿尔比笔下的纽约正是这一多元混杂现实的具象呈现——稳定与不安、自由与规训并置交织,构成现代都市不可回避的矛盾。
阿尔比的重构路径植根于城市的戏剧传统与伦理功能。在他看来,城市不仅是物质结构的堆叠,更承载着伦理的重量。通过戏剧语言,他揭示了城市空间如何塑造个体与社会关系,并呼吁重新思考其道德结构。《在家在动物园》在延续奥尼尔、威廉斯与米勒的严肃传统之上,面对消费文化的浪潮,通过新增“在家”一幕深化了都市家庭的情感危机。安娜的呐喊——“我不是一个普遍性,我是个人”(山羊:90)——既是对自我主体性的坚决申明,也是对现代性同质化趋势的强烈抗拒。
在剧中,安娜与杰瑞分别承担了破局者的角色。前者试图唤醒彼得,让他走出内心的密闭空间,直面混乱与本能;后者则通过讲述自身的琐碎生活与情感挣扎,努力让彼得理解底层的真实处境。中央公园的长椅既是彼得的庇护所,也是阶级冲突的交战地。在最终的生死对峙中,物质秩序之外的情感联结隐约浮现。安娜的“动物性”唤醒与杰瑞的“动物园理论”,共同构成对都市理性逻辑的深刻挑战。彼得在临界时刻的顿悟,则暗示了超越工具理性的人际沟通可能。
阿尔比从人的存在出发,用现实主义细节铺陈出人与城市之间的复杂互动。他并未全然否定都市现代性,而是试图通过冲突的展演,架起人性与异化之间的桥梁,召唤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伦理。从这一角度看,纽约既是“美国梦”破碎的现场,也是新伦理生成的试验场。
伟大的城市不应成为切割人性的机器,而应是多元文明交汇的共同体。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言,城市的活力源于其交错与关联的多样性。⑦《在家在动物园》的伦理意涵正是在于,从日常的“陌生化”中解放出真实的个体,使人在回望自身“动物性”的同时,重新发现“人性”的可能。
结语
《在家在动物园》以文化符号权力的隐性运作,展现出城市中不同阶级间难以逾越的隔阂。表面上,城市文明似乎正塑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图景,然而现实中的贫困、混乱与暴力却始终如影随形。正如城市学家芒福德所说,“城市的改进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来观看,而城市的恶化则主要从社会价值的层面来衡量”⑧。唯有在不安、焦虑与误解中坚持对话,真正包容与开放的城市精神才有可能生长。
阿尔比通过描绘纽约中产家庭的冷漠日常与公共领域的阶级冲突,并非一味批判现代性的疏离现象,而是在探寻超越二元对立的都市伦理重构之路。这条路径既非对“田园牧歌”式前现代的怀旧,也非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对城市复杂性的理解,肯定其发展逻辑的同时,呼唤一种以人性为核心的共同体重建。城市不仅是物质的集合体,更是精神与道德的剧场;它既是权力运作的场域,也是反抗与革新的舞台。《在家在动物园》不仅揭示城市的病灶,更为伦理重建提供了参照,让我们在面对都市异化时,得以跳脱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转而以辩证目光理解城市的张力与可能。
阿尔比对纽约的书写,不仅反思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困境,更以戏剧为媒介,为世界戏剧史中的城市书写注入了深刻的伦理意涵与人文关怀。在《在家在动物园》中,阿尔比通过彼得、安娜与杰瑞三个角色的互动,展现了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与情感区隔,同时也揭示了超越这种区隔的可能性。城市的未来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人性之间彼此的磨砺与重建。只有在承认城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一种包容、开放的都市伦理,让城市不仅成为物质繁荣的象征,更成为人性自由舒展的空间。
注释:
①[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4、189页.
②[美]爱德华·阿尔比:《山羊:阿尔比戏剧集》,胡开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75页.所引文本全部出自此书,后文引用均不列出处,仅标页码。
③[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张辑、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页.
④[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5页.
⑤[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2页.
⑥[美]罗伯特·阿尔特:《想象的城市:都市体验与小说语言》,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⑦[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⑧[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郑时龄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