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红与黑》中玛蒂尔德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论文
2025-09-30 15:07:32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塑造了三个重要的角色—于连、德瑞纳夫人、玛蒂尔德。波伏娃曾评价司汤达是女权主义者,玛蒂尔德的人物塑造上鲜明体现了司汤达的女性主义思想。
摘要: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塑造了三个重要的角色—于连、德瑞纳夫人、玛蒂尔德。波伏娃曾评价司汤达是女权主义者,玛蒂尔德的人物塑造上鲜明体现了司汤达的女性主义思想。文章以《红与黑》为研究范本,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从玛蒂尔德与德瑞纳夫人差异性下的权利追求、与于连的相似性下的冲突博弈两个角度,探讨《红与黑》中司汤达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权利追求;冲突博弈
司汤达被评为是个“十足的女性主义者”[1],他的作品中涉及很多对女性主义的思考: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女性的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红与黑》中玛蒂尔德的形象塑造体现司汤达对于女性主义的思考,玛蒂尔德的形象不是简单的直接描写,很多特质是在人物的对比冲突中展现出来的。本文通过玛蒂尔德与德瑞纳夫人、玛蒂尔德和于连的人物对比来分析司汤达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一、玛蒂尔德和德瑞纳夫人:差异性下的权利追求
玛蒂尔德和德瑞纳夫人是《红与黑》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形象,两个女性的形象塑造具有差异性。德瑞纳夫人是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女性,她葆有着自然状态:纯真、质朴,却也混沌、迷茫。德瑞纳夫人是在于连的爱情中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是被排除在社会体系之外的觉醒。而玛蒂尔德比德瑞纳夫人更加独立、自由,具有社会属性。她拥有许多社会属性的特质:显赫的家世、惊人的美貌、丰裕的财富。她追求自我幸福的权力,渴望做出一番“伟大激情”的事业。玛蒂尔德社会属性比之德瑞纳夫人自然属性具有进步性。
(一)差异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司汤达对卢梭尤为崇敬,把他视为“思想最高尚、才能最伟大的人物”。卢梭强调“自然状态”[2],认为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人们不受社会和文明的约束,过着本真、质朴的生活:强调“自然的善”[2],认为人的本性和自然一样,人在自然状态下是本真的、善良的、纯洁的。德瑞纳夫人的自然属性可以从她的“自然的美”和“自然的善”中窥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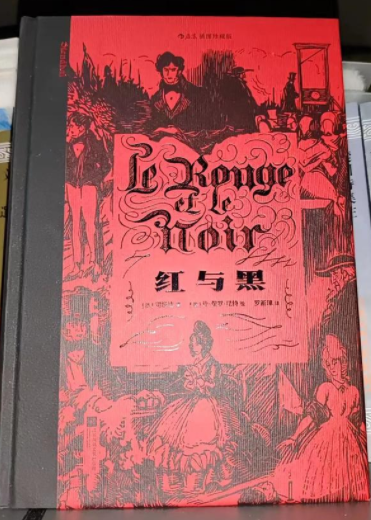
在发掘对于连的爱情前,对德瑞纳夫人美貌的描述是一种“自然的美”,因为此时德瑞纳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她只有“淳朴的天性和灵敏的头脑”,她几乎没被文明污染,将从修道院学来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她又有那么一种纯朴的情致,步履还像少女般轻盈。风韵天成,满蕴着无邪,满蕴着活力。”她的美貌浑然天成,质朴、天真,是带着自然属性的美貌,这也与她“自然的善”相呼应,德瑞纳夫人的善像自然一样具备广阔的包容与怜爱,她最初对于连的爱情起于对他的怜爱,哪怕于连枪杀自己,也还是选择包容,爱着于连。
将德瑞纳夫人的自然属性作为对照组,德瑞纳夫人是排除在社会体系之外的觉醒,那么,玛蒂尔德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就被归入到社会体系中了。玛蒂尔德天生就带着一系列社会属性,它拥有一系列男性才能从社会体系中获得的特权:高贵的血统、偌大的财产、超人的才情。玛蒂尔德有着强烈的性格,内在极其强大,有很强的主体性与意志力,这赋予她敢于挑战外在社会舆论与既定习俗的勇气,甚至以此为乐,[3]她处在社会体系里积极追求女性权利,体现了女性主义进步思想。
(二)差异性:被“圈养”的觉醒和积极追求权力
德瑞纳夫人从“被圈养”走向反叛,自我意识觉醒是女性主义思想进步性的一大体现,但她从封建道德观念中探出头,却自始至终没有彻底冲破封建宗教观念的束缚,和于连偷情的罪恶感一直萦绕着她。并且,德瑞纳夫人仅仅从自然属性出发进行觉醒,她的觉醒局限在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中——家庭里附庸丈夫的妻子、孩子们无微不至的母亲。依旧被放逐在社会权利体系之外,这是一大局限。
在发掘与于连的爱情之前,德瑞纳夫人的自然属性让她没有“自我意识”,一个拥有自然属性的女性在资产阶级文明社会里只能是被“圈养的”,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心灵的独立和自由被隐藏的很深,她本人不懂爱情,不知道自己难以忍受自己的命运,甚至懵懂无知的自我安慰、麻痹着。“她心地纯朴,从来没想到要去品评丈夫,嫌他讨厌。在她,虽未明言,但想象中,夫妇之间也不见得会有更温馨的关系了。”但直到于连的出现,德瑞纳夫人意识到了什么是爱,从懵懂、混沌的纯粹自然状态中开始剥离,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首先体现在对自身美貌的认识,她开始注重打扮,欣赏自己的女性魅力。德瑞纳夫人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她开始享受生活,在意自己的着装,她重新找到了现实的活力。“您从来没有这么年轻过,夫人”,她的朋友这样说。[4]其次,体现在她对丈夫的反叛,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对自身欲望的承认,一直依附丈夫的德瑞纳夫人,选择了与于连偷情,在忏悔中承认自身欲望,放纵欲望。
玛蒂尔德在社会体系中追求权力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女性从被排除在社会体系之外的觉醒到追求在社会体系中进行觉醒。与德瑞纳夫人的自然属性相比,玛蒂尔德的社会属性更能体现她的社会权利追求的进步性。
玛蒂尔德大胆追求自己的社会权利,追求自我决定的权利。伊曼纽尔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理论》写道:“女人不仅仅是为了成全他人幸福或完美的手段或工具。相反,女人是目的,是理性的主体,她的尊严包括有自我决定的能力”[5]一方面,体现在玛蒂尔德对爱情自我决定权利的追求。玛蒂尔德拥有着极强的“配得感”。上天给了她许多恩典:财富、身世、才情、美貌,但她说“我就该享有幸福”“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命运就该不同寻常啊”,所以她积极寻找自己生命里缺失的部分——爱情。她不满于自己的爱情幸福权利无法掌握,与德瑞纳夫人不同,德瑞纳夫人的自然属性迫使她在爱情中处于被动的位置,所以糊里糊涂的嫁给丈夫,对于连的爱也是被动接受的。玛蒂尔德瞧不上周围的贵族子弟,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去经营一段“发困的爱情”。她用自己的爱情为饵,不将自己的爱慕者们放在心上,她要自己去追求符合自己心中“英雄情操”的爱人,她对于连的爱,其实是对自己欲望的选择。在与于连相爱时,她会寸步不让,不愿将自己幸福的权利完全交予于连手上,还没表白前,玛蒂尔德就有些犹豫“玛娣儿特性格里也不乏骄矜的成分,看到自己的幸福要取决于他人,所以,在这种感情滋生之初,就有种莫名所以的惆怅”而在和于连偷情后,她也警惕于连掌握自己爱情幸福的权利,当她察觉到于连“以我的主子自居”,她就开始疏离于连,反倒让于连欲罢不能。但最后,玛蒂尔德还是没能跳脱出女性“感性”的陷阱,将自己幸福的权利交了出去。另一方面,体现在玛蒂尔德追求社会荣誉和社会政治权利。虽然身份高贵,但玛蒂尔德依旧有自己的社会荣誉追求,她想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出来,但即使处在社会体系之中,玛蒂尔德依旧受到女性身份的限制,没法亲身投入社会政治权利的追求中。因此,她对社会政治权利的追求就折射到她对爱人的寄托上,她对于连的追求就体现了这一点。“假如有像路易十三那样勇敢的国君,拜倒在我脚边,看我不教他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来!我就把他指向旺代……而且,于连与我能桴鼓相应。”这其实是玛蒂尔德自己想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但当时社会不允许女子摄入社会政治权利体系,因此,玛蒂尔德的社会政治权利追求只能通过对于连的寄托来实现。
二、玛蒂尔德和于连:相似性下的冲突博弈
突破性别局限进行人物比较,会发现玛蒂尔德几乎就是于连性别转换的理想人生,她有于连自卑又渴望的——高贵的血统、偌大的财产。跳脱出性别隔阂,玛蒂尔德与于连有许多相似性,同时,在这样的相似性下,司汤达将于连的理想人生置于女性社会角色中,制造了一次天然的伟大冲突。于连拥有追求权力的社会身份,却没有家世血统等社会资源,玛蒂尔德拥有于连缺少的名望财富等社会资源,却没有追求权力的社会身份。在这样相似性前提下,通过男性女性的冲突博弈展现女性的斗争,这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更是熠熠生辉。
(一)相似性:个人奋斗者的反抗与欲望
于连作为一个典型的个人奋斗者,[6]让很多人都忽视玛蒂尔德其实是个女性个人奋斗者,在这里,对个人奋斗者的定义不是底层人民的个人奋斗,而是指具有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对自己的目标进行持续追求。于连和玛蒂尔德在反抗意识与欲望追求层面都具有极大相似性。
于连和玛蒂尔德具有相似的反抗意识,他们反抗的阶级相同,但是辐射角度不同。于连是从下向上的反抗,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轻视,这是他对上层阶级的一种反抗。他在父亲让他去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说,“如果要降低身份,和仆人一起吃饭,我宁愿死”;和对自己轻视的人决斗;对凯琉斯、夸泽诺、吕茨等贵族公子瞧不上。而玛蒂尔德的反抗意识同样也是对上层贵族阶级的不满,但她出生于这个阶级,是从上对上的反抗,与于连的角度不同,除了女性身份,玛蒂尔德还有相同阶级立场身份,她的反抗比于连更加深刻。她没被这个阶级异化,将目光投射在了别的阶层,这主要体现在她对追求者们和自己哥哥的态度上,“等革命再起,看夸泽诺和我哥哥能扮个什么角色?那是已经前定的了:堂而皇之地逆来顺受。他们会是英勇的绵羊,一声不吭地延颈待戮。”但她的反抗是有局限的,她厌恶所处的社会阶级,却也没能跳脱出来,如让父亲赐给于连爵位钱财,摆脱索雷尔这个贱姓。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这不光是在社会体系中女性对自我的认识,更是女性的反抗和斗争意识的体现。
于连和玛蒂尔德都自视很高,都对自己欲望主体进行模仿,都野心勃勃,有着对追求目标的持续行动力。[7]于连和玛蒂尔德都有着自身追求的目标,于连的追随目标是拿破仑,他自己对拿破仑进行欲望模仿,他希望能像拿破仑一样凭借个人奋斗获得地位;玛蒂尔德的追随目标是她的姑母——玛蒂尔德·特·瓦罗亚,她希望能像姑母嫁给拉穆尔一样嫁给时代的杰出人物,能够鞭策丈夫作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两人都有着追随的目标,然而在行动力上,玛蒂尔德更胜一筹。在枪杀德瑞纳夫人未遂后,于连似乎将追求放下来,“说实在的,他对英雄行为已感到倦怠。也许一种天真淳朴的。近乎羞怯的柔情,更能拨动他的心弦,”他感到怯懦,只想向德瑞纳夫人倾诉;但玛蒂尔德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追求,在于连入狱后,她感到一种更大的追求,更大的挑战,让她持续为营救于连而四处奔走,依旧为心中伟大的激情四处奔走,“玛娣儿特为一种她引以为豪的,比骄傲更强烈的情绪所激励,不愿此刻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未作任何惊人之举就白白过去。”在于连对英雄主义厌倦时,玛蒂尔德却没有放弃,依旧野心勃勃、雄心壮志,在这方面,玛蒂尔德作为女性角色,展现出了更大的斗志。对于玛蒂尔德这样的女性角色来说,外界社会体系束缚更深,却更能展现出超人的激情和刺激,她的斗争也就更加迷人,更能展现女性主义思想的魅力。

(二)相似性:身份错位下的冲突和博弈
正是玛蒂尔德与于连的相似性使于连不能受到吸引,于连感到厌恶、疲倦,或是不由自主地怀着某种恐惧。因为他在个性上不如她强悍,在追求上不如她坚韧,在反抗上不如她彻底,于连在玛蒂尔德面前自卑心理会更强烈,所以她需要德瑞纳夫人母亲般包容、温暖的爱,而不是和他旗鼓相当的妻子。在这样相似性下,于连和玛蒂尔德各自拥有对方缺失的社会身份或社会资源,又具有天然的冲突。作者赋予了玛蒂尔德许多和于连一样的品质,也就让他们二人能够同台竞技,最为突出的就是二人的爱情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玛蒂尔德作为女性角色,并不是和传统社会女性一样是一个被动、弱势的接受者角色,她手握相同的筹码,努力主动掌握自己的爱情,虽然也有陷入“感性”陷阱的时候,但在这儿,司汤达尽力将男性和女性放在平等的爱情位置上进行博弈,展现了他对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思考。
于连和玛蒂尔德两人的爱情是以征服与反征服为基础的[8],她们二人都有着追求挑战和冒险的性格,两人爱情的初步形成阶段,两人都性格高傲,将自己视作这场爱情里的主导方,“敢于爱一个社会地位与我相去甚远的人,就已经够伟大,够有胆量的了。他能一直配得上我吗?只要在他身上看出软弱的苗头,就把他甩了。”“不管怎么说,她是够漂亮的,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然后一走了事。我脱身之际,谁要给我找麻烦,那他等着倒霉吧!”
在相爱时,他们又是各有优势和劣势的,两人不断将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最先占据优势的是玛蒂尔德,她大胆且热情,在意识到自己的爱后,先递了情书,作为这场爱情博弈的发起者。她对于连的第一场考验是靠在窗子上的梯子,这容易被发现、不同寻常的方式,是玛蒂尔德骄傲的不谨慎行为,是她追求不同寻常的激情,对束缚自己的外界的一次挑战。于连接下了这份挑战,他带着手枪和暗器爬上梯子,作为这场挑战的勇敢者,他抢占了优势。然而,在他幻想着“情妇必定温柔体贴,只要能使情郎快活,可以不再计及己身。”玛蒂尔德好胜的一面让他怨气冲天,“想到这一点,玛蒂尔德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她性格里,敢作敢为是最大特点。除了拿自己的一生孤注一掷外,再也没有什么能使她感奋,能治她经常兴起的烦闷。”玛蒂尔德很快又占据了优势,此时于连好恶爱憎全都乱了套了,处于劣势。接着,他们各自用技巧让自己成为这场爱情博弈的优势占据者。玛蒂尔德通过向于连夸大自己对凯琉斯、夸泽诺、吕茨等的爱,让于连嫉妒,迷失自己,最后又提出不再爱于连。于连也通过采取柯拉索夫亲王的建议,假意写信追求同社交圈的元帅夫人,换回了玛蒂尔德的爱,甚至让她向父亲承认自己怀孕。这场爱情博弈里最终究竟是谁胜谁负,似乎难以界定。于连最后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是德瑞纳夫人,但对于玛蒂尔德,就像于连自己说的,“她也许已哭了一整夜,但是将来有一天,她回首往事,说不定会引以为耻!”将来,玛蒂尔德也会去寻找自己新的“伟大的激情”。通过这场爱情博弈,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对女性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的考量,将玛蒂尔德塑造在与于连同等的位置上,让她们二人同台竞技,不再将女性放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
三、结语
玛蒂尔德与德瑞纳夫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差异性下,女性从被放逐社会体系之外到在社会体系中追求社会权利,体现女性主义思考的进步。玛蒂尔德与于连作为个人奋斗者,相似的反抗意识和欲望追求,玛蒂尔德和于连在天然的身份错位下进行爱情博弈,难分伯仲,看到玛蒂尔德身上女性的进步。玛蒂尔德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司汤达的女性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1[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09.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3]潘丹.自我、革命与爱情:《红与黑》中的“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J].社会,2021,41(04):156-181.
[4]何羽.权杖下的枯玫瑰——《红与黑》中的爱情观[J].名作欣赏,2022,(17):120-122.
[5]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才艺佳.《红与黑》于连秘书形象探析[J].名家名作,2025,(04):54-56.
[7]高海雁.浅论《红与黑》中于连的爱情发生[J].名作欣赏,2022,(26):142-144.
[8]叶皖林.《红与黑》中的女性形象[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109-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