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艺术治疗”实践研究论文
2025-09-30 10:59:16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文章立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借助拉康“镜像阶段”与“三界”结构对主体分裂与无意识机制的解析,重新审视艺术治疗在高校心理支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梳理了“房树人”(HTP)绘画在传统结构主义框架下的运作逻辑。
摘要:文章立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借助拉康“镜像阶段”与“三界”结构对主体分裂与无意识机制的解析,重新审视艺术治疗在高校心理支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梳理了“房树人”(HTP)绘画在传统结构主义框架下的运作逻辑,指出其在符号解读中的中心化权力倾向与单一化意义压缩问题。进而提出以“漂浮能指”观照HTP图像,赋予其多义性、生成性与开放性解释空间,倡导通过“多轮绘画”“小组对话”“绘画+写作”等实践路径,将来访者从被动的受测者转变为意义的共建者与主体性修复的参与者。文章旨在为艺术治疗提供后结构主义理论精神的解释框架,并回应当前高校教育中对“人”的整体关怀的诉求。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艺术治疗;象征机制;高校教育
一、艺术治疗的现实背景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提出“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用以描述那些既是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又承载着对主流社会空间的映射、颠倒与重构的场所。高校正是这样一种异托邦:它在地理上有明确位置,却游离于社会日常生活之外;校园内部有别于外部社会的规则和文化,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它既提供了一个与外部生活“绝对性断裂”的空间契机[1],让学生得以暂时脱离家庭与社会的既定角色,又将外部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权力机制潜移默化地引入其中,形成对现实的映照与象征。
高校以特殊的制度(校规、生活规范等)规训着学生的身份角色。其次,在“象征秩序”层面,校园内部有其独立的一套符号体系和话语结构。踏入大学校园,学生便进入了一个新的符号网络——专业领域的学术资源、校园文化的隐喻、师生关系的角色定位,都构成了独特的象征秩序。这个秩序为学生提供了身份认同的蓝本,例如“新生”(freshman)、“社团社长”“毕业生”等身份标签成为自我认同的重要坐标。然而,这种象征符号也可能引发秩序的混乱与碰撞:一方面,大学的价值观和象征体系往往与学生先前所习得的家庭或社会价值产生差异,令他们在旧有秩序与新符号体系之间感到迷茫;另一方面,大学阶段价值观多元且不断流变,学生面对多元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可能性,原有明确的意义框架可能被解构。当象征符号不再稳固时,学生会经历一种象征秩序的混乱,无所适从,不确定何谓“正确”或“有意义”,导致心理上的迷惑与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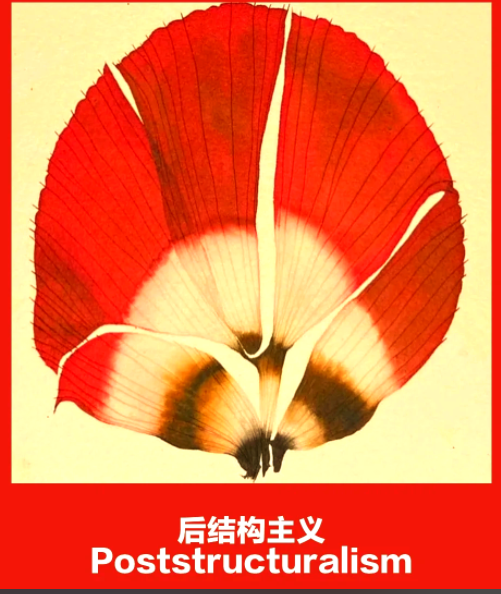
“大学时期”凸显出人类学所谓“阈限性”的特征——如同一种现代版的“过渡仪式”[2](rite of passage)。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标志着个体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开启;而毕业离校则象征着这一仪式的完成。在大学这个“异托邦”空间里,学生处于一种阈限状态:他们暂时脱离了原有家庭和社会身份,又尚未完全承担社会成人的职责。这种身份上的过渡性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空间上构成了一个与社会相对隔开的世界;时间上,大学生活被限定在数年内,有固定的学制和学年循环,当这一异托邦时间耗尽时,个体必须“回归”于社会。大学生活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延迟踏入社会的缓冲期和实验场。在此阈限阶段,个体拥有探索自我的自由,也面临着身份未定的困境:旧有身份已模糊,新的身份尚在生成,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容易引发内在的不安与不确定感。大学的过渡性给予学生身份重塑的机会,同时也伴随着方向迷失和自我认同危机的风险。
二、“房树人”结构化象征图式的引入
拉康强调主体受到无意识欲望的驱动,而无意识“如语言般运作”。艺术作品恰似无意识的语言载体,它以象征形式记录和传达出主体深层的情感与欲望。表达性艺术治疗鼓励来访者通过绘画、雕塑、音乐等媒介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在体验,这一创造过程本质上是无意识内容的象征性转译。正如有学者指出:“艺术创作是一种自我表达”,治疗师与来访者可借助作品中的象征语言进行沟通[3]。色彩、形状、意象等在作品中呈现的符号,往往对应着言语难以企及的情绪和记忆。拉康的符号学视角认为,在主观言说抵达之前,图像先行一步将无意识之意涵寓于其中。这使得艺术成为一种“不经语言而语言”的途径。尤其对于那些难以用言辞表露的情感和体验,艺术提供了更自然的表达方式,不受日常语言逻辑的限制[4]。
表达性艺术治疗由于整合了多种艺术形式而使主题领域极为宽泛。这种高度灵活性固然有助于来访者以非语言、象征性的方式及时将被压抑的内在内容自由表达出来,且阻抗较小。但宽泛的主题和媒介也带来了结构性的挑战,治疗师往往难以在纷繁的艺术表达中找到清晰有效的介入路径。如果治疗缺乏语言的介入,即缺席象征界的组织,那么来访者的治疗体验可能陷入“想象界的泛滥”与“真实界的沉默”。前者表现为大量意象的涌现却缺乏提升至言语层面的提炼,导致疗愈过程停留在主观幻想的循环;后者则意味着那些最深层、难以言说的创伤性内容依然留在无法言表的沉默之中。正如拉康所指出的,真实界往往与创伤紧密相连,而治疗的关键正在于把创伤“象征化地说出来”。没有象征性言说的参与,艺术表达所触及的真实痛苦可能仍旧停留在语言之外,无法被社会意义所承载和消化。
“房树人”(House-Tree-Person,HTP)绘画主题更具焦点性——来访者需要绘制出房屋、树木与人物,既保留了创作想象的空间,又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支点。这样一来,治疗师能在三种意象之间梳理和追踪来访者的投射线索,及时捕捉其潜意识呼唤。作为一种经典的投射性人格测验方法,HTP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巴克(John N.Buck)于1948年首创。测验要求受试者分别在纸上绘制一幢房屋、一棵树和一个人物,然后由施测者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图画进行分析和解释。
传统HTP绘画分析实际上建立在一种符号对应的范式上,假定绘画中的形象和细节可映射特定心理含义,例如房子象征家庭氛围,树代表自我成长,人物体现自我形象,细节如窗户大小、树根深浅等都被赋予固定解释。这种解析方式源自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能指-所指稳定关系的信念,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的“解读密码”。治疗师仿佛是破译者,将来访者的图画转译为既定的心理指标。这种机械式的“读码”也使得HTP绘画面临多重“困境”。
符号学式解读将绘画视为被动传递内心内容的载体,默认绘画者自己对图像意义无充分发言权。正如罗兰·巴特所批判的“作者中心”:意义被视作由绘画所呈现的符号所单向决定,而来访者俨然成了无声的“作者”,他的绘画一旦完成,其意义就由解读者全权接管。这正是巴特“作者已死”观点所反对的倾向——巴特认为,应当让读者(在治疗中可对应为来访者和治疗师双方)参与赋予作品意义。在HTP传统解释中,绘画者的意图和体验被边缘化,来访者无法主动阐释自己的图画,因为权威的解释手册已替他说出了“真相”。这种情况无疑剥夺了来访者的主体性和诠释权,使其沦为被动的“被分析对象”。
结构主义解读假定符号意义的单一确定性,因而扼杀了图像的多重含义和开放性。德里达的“延异”揭示了每个符号的意义都因对其他符号的参照和差异而延迟生成:绘画中的一个形象(如一棵树)并不存在一个终极所指来锁定其意义,它的含义取决于语境、观者视角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无穷无尽的关联网络。结构主义的测验话语蕴含了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正如福柯所强调的,所谓“知识”从来与权力纠缠在一起——在心理测验情境中,治疗师凭借专业知识处于话语权力的上位,能够对来访者的绘画进行命名和定义。而来访者的叙述则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在典型HTP解释中几乎失声。
面对传统HTP阐释的僵化,需要引入后结构主义视角下对符号的重新理解:将绘画中的图像元素视为“漂浮的能指”,而非恒定指涉某意义的固定符号。拉康就曾形象地描述能指的运作如同一串浮动的链条:每个能指的意义并非由某个所指一劳永逸决定,而是通过与其他能指的差异关系来暂时生成。对于HTP绘画而言,这意味着“房”“树”“人”这些形象不应再被看作心理内容的透明载体,而应被视为蕴含多维意义可能的符号节点。在这一观念下,一幅房树人画作不再提供一个供治疗师读取的答案,而更像是一段有待共同书写的“文本”。来访者作为绘画的创造者,也是此文本首要的“读者”和解释者。他对自己画中符号的理解,可以也是应该在阐释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要在治疗情境中赋予来访者“重新命名”其图画元素的权利:鼓励来访者用自己的语言和联想去命名房子的意义、树的象征、人像的故事,而不是直接套用通用符号含义。通过参与式诠释,图像的意义不再由外部权威赋予,而是在治疗师与来访者的互动中生成。来访者获得了对自身图画的话语权,可以主动解释、改写“符号”的涵义。这正体现了巴特“读者、观者的诞生”——意义的创造权向来访者倾斜,使其不再只是被解读的客体,而成为积极的意义共建者。
HTP绘画应被看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空间:房屋、树、人等图像并非某种心理真相的终极指证,而更像是提供了一系列起点,引发一串联想、叙事和情感反应。在来访者开始赋予它个人意义之前,这些图像处于未定之流——它们可能是温暖的、安全的,也可能是孤独的、叛逆的,一切取决于交流语境。通过引导来访者表达对自己画作的看法、情绪和联想,既尊重了符号的多义性,也鼓励了来访者去探索内心多重声音。当治疗师不再急于给每一元素贴上确定标签,而是和来访者一起沉浸、游历于图像的意象联想,那么每一幅HTP画都可能演化出独特的叙事和意义网络。
通过将HTP符号视作漂浮能指,由此实现了两重赋权:其一是对符号本身的赋权——符号获得了摆脱所指桎梏的自由,可以生成新意;其二是对来访者的赋权——来访者获得了参与诠释的自主地位,不再受制于量表和权威解释。这种转变有助于消解治疗师的阐释垄断,防止过度诠释对来访者主体性的侵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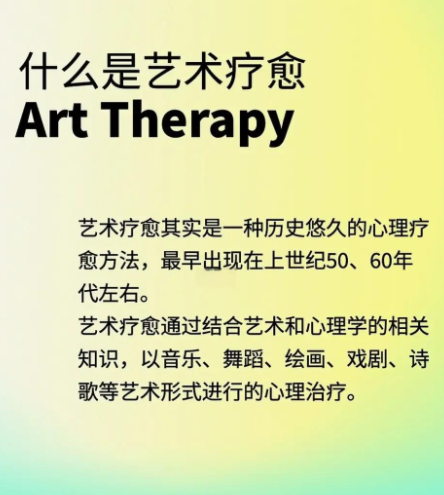
三、创新范式,后结构主义精神在HTP中的应用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选取吉林艺术学院作为试点院校,并于2024年3月开设了“绘画疗愈”创新课程,以将前述理论精神付诸实践。基于HTP绘画的基本框架,致力于探索多种新的操作范式,摆脱以往一次性、封闭式测验的流程,转而强调更具开放性、动态性与多主体参与的创作与阐释过程。
1.多轮绘画
通过打破HTP“单次绘制”的操作惯例,鼓励来访者在多个时段、多轮次中反复进行“房、树、人”主题的绘制,或对既有作品进行拓展与修改。多轮绘画强调“过程即意义”,意在使绘画成为一个连续展开、不断演化的象征性叙事轨道。例如,在第一轮创作完成后,治疗师与来访者共同讨论图像中呈现的情感与符号线索,随后邀请其带着新的理解进行再创作。某些来访者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图像的变化正映射其内在体验的转化——如原先断裂的树干在下一轮中生出枝丫,从象征破碎转向修复。这种以绘画为媒介的象征流动,为来访者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表达维度,使其在反复创作与修正中感受到自我建构的能动性,逐步挣脱被“定格解释”的束缚。
2.小组对话式阐释
将HTP引入小组艺术治疗或团体辅导语境,使作品不再只面对单一治疗师,而是在群体语境中生成多重意义。参与者带着各自的情感经验和文化视角,围绕绘画展开对话:有人关注图像结构,有人回应情绪氛围,也有人产生移情式共鸣。在这种多声部语境中,图像不再是静态文本,而是一个被不断重写的象征体。意义由“专家解读”转向“共建讨论”,权力结构由单一话语垄断转向流动的解释网络。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人在作品中的发现往往激发其自我理解的新视角,有助于打破固化的叙事回路,重新界定自身处境。而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观看与阐释他人作品的过程也构成一种镜像式的自我探索。治疗师在其中的角色不再是权威诠释者,而是对话引导者,保障讨论的开放性、安全性与生成性。
3.绘画+写作的跨媒介连缀
为了打破单一表达通道的限制,课程引导来访者在完成HTP绘画后,辅以文字形式的回应,包括自由书写、信件表达、短诗创作或图像命名等。写作不仅是对图像的解释,更是一种重新“命名”与“再创造”的过程——文字延展了绘画的意义,而绘画又反过来激活语言的情感张力。符号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游移、互文,构成一个不断生成的意义链条。例如,一座被封闭的房子可能在文字中演变为“记忆的容器”或“情绪的避难所”,而后再被转化为图像中的动态场景。此种跨媒介实践,既拓展了表达的层次,也激发了来访者在多重能指系统中对自我经验的再命名与重组,促使其主体性在流动中逐步浮现。
四、结论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艺术治疗”实践并非单纯地在技术层面对传统方法进行修补,而是对潜藏于心理测验与治疗话语背后的主体—客体关系进行了根本的重审,其强调的“去中心化”与“符号漂浮”并不意味着在治疗过程中对所有表达加以无限制的放任或追逐。唯有在这一自觉下,治疗师才能积极倾听并与来访者共同创造意义之网络,从而使艺术治疗更充分地触及隐匿于语言与意识边界之外的主观体验。因此,重新定位“房树人”绘画的象征机制,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关怀提供了一条兼具理论启示与实践操作的可行路径。通过赋权来访者,突破传统解释的限制,使“房、树、人”成为不断生长、富有弹性的象征节点。艺术疗愈在高校这个“异托邦”中所能发挥的创造力与疗愈潜能,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代高校教育中对“人”的整体关怀诉求。
参考文献:
[1]Read B.The university as heterotopia?Space,time and precarity in the academy[J].Access:Critical explorations of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2023,11(1):1-11.
[2](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张一兵.从自恋到畸镜之恋——拉康镜像理论解读[J].天津社会科学,2004(6):12-18,74.
[4]吴琦.表达性艺术治疗在高校育人体系中的应用[J].艺术教育,2024(12):11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