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 口述史料问题实践论文
2025-09-26 16:35:53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为进一步倡导口述史料著作,还应当加强对口述史料的了解和认知,用当前人们生活中感兴趣的内容去对过去的事实进行研究,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口述史料的发展,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说,当代文学口述史料的相关著作较少,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进一步倡导口述史料著作,还应当加强对口述史料的了解和认知,用当前人们生活中感兴趣的内容去对过去的事实进行研究,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口述史料的发展,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口述史料价值被更多人所承认,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开始出现口述史著作,整体来看这部分著作依然较为匮乏,大多是因为需要耗费过多时间,但无法在现行体制中获取成果。从某一方面来看,可将口述史理解为过去的声音,但其又是在当代所采集、公布的内容,这就会涉及现实、过去中人和事的不同,无法再现沟渠的客观性,而是需要从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出发,来对过去的事实进行研究。在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口述史料的问题需要去探索“现在生活中的兴趣”这一概念,对其的研究更有利于推动和倡导口述史料著作的发展。

口述史的相关内容
基本介绍。口述史是国际上的一门专门学科,是通过采集、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口述史产生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是人们通过口头转述的方式来记录历史;从狭义上来说,口述史最先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我国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并没有过多的学者或是机构专门进行口述收集和整理工作。虽然口述史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方法上面还未形成一套科学系统。
特点和价值反映。口述史并没有统一的命题,其以多数的观点进行讲述,叙事者的偏好似乎取代了历史家所谓的公正传统。相较于文献史料来说,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更多。口述材料中涵盖了由人们自己所述说的全部信息和主观性说明,也正是如此,口述材料才具有非客观性。口述的陈述没有重复性,即使是对同一个人进行访谈,不同的时间讲述着所述说的版本也可能发生变化。
可将口述史看作一种应对艺术,其与正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能够让人们知道另一种历史叙事,容易使人产生共鸣。也不像文字史一样有强势主义,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的表述,能够超越分类技术的控制。
口述对象的选择。不同于其他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前期需要做大量准备,准备工作时间相对来说较长,其需要划定历史时期并确定课题。在选择口述人的时候,可通过两种方式开展。一是针对某一阶段或是历史课题,去寻找亲身经历的有表达愿望的人,对其进行口述调查,做好记录。无论是亲历者或是旁观者,抑或是否为重要人物,其所述都应当进行记录,这主要针对一些距离现实较远时期的史料;如若距离较近,那么可以对口述人物进行一定的筛选,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口述内容进行记录。二是历史事件发生在某一地区,可直接在这一地区中寻找见证人,通过媒体来发布口述人征集广告,以确定适宜的口述采访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
认识口述双方的身份。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口述史料的“现在生活中的兴趣”,需要进一步认识口述双方的身份。我国的口述史著作最开始出现于30年前,大多都是1988年后,这一时期作品中的受访者常自认为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采访者则认为自己是反对者,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身份共识。
从受访者“受害者”身份来看,目前口述著作中的“受害者”大多都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批评家,而西方口述史主流中的受访者则多以底层人物为主,致力于利用底层人民的记忆去重建和还原历史的多样性。有外国学者认为当代一些记载下来的历史,反映的都是权威者的观点,而口述史能够让这一历史显得更加公平、现实,可通过一些失败者、污权威、特权者去重构历史,挑战既定的记述。基于此,可发现口述史应当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描述,但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采访的人员大多都不是底层人民。虽然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所谓的失败经历,但其“受害者”身份也并不彻底。从整体上来看,“革命民众主义”理论是导致社会无法公平对待知识阶层的主要原因,新的权力机制建立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开始显现,其获取了一定的文化领导权,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在新的时代跃身成为成功人士。而且失败大多是从政权方面来说,而不是对于底层而言。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底层,其在心态上有所不同,知识分子仍然有机会重新恢复地位。在这种观念下,受访者的口述会让人产生纠结,其无法判断受访者讲述的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经验,能够被采访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已经在自己的阶层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采访者的“反对者”身份来看。口述著作者大多都自居为过往政治运动的反对者,需要搜集证据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去探索人性。这种身份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尊敬,但是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早就成为了过去,当下的中国正在探索新的特色化社会主义;二是文化思潮中去权威化是一个部分,部分人的叙述中似乎又开始了阶级化,底层被抛弃,新的时代下如若仍然用悲情方式去反对过去的政治,会有一些假想敌嫌疑。另外,在对过去政治运动的批判中,虽然能够伸张正义,但也会掩盖社会中新的不平等,“反对者”身份的塑造,是否能够真的适应当代的新环境,这一身份下的口述者是否能为底层人民带来积极作用,这是需要思考的部分。
过于混杂的身份,会让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变得复杂,虽然口述史料的产生和形成本身就来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层面社会结构的制约,但是口述者若无法意识到文化生产机制,其所传达的工作价值便难以实现。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成功者”,或是“权力者”“反对者”,其最终涉及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兴趣”,过往的记忆会被兴趣唤起。
“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德国自传体著作《童年回忆残片(1939年—1948年)》中有着大量的纳粹大屠*证据,引起了读者极大反响,但是其中部分所谓的证据并不是真实的,在情节上进行了伪造,这种被伪造的记忆为何能够被读者所接受呢?德国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些情节的写成基于一种社会期待态度。虽然著作中的情节不够真实,但人们认为其“正确”,他们从有用性和社会接受性两方面都承认了幸存者的意义,这使得幸存者的视角被特权化,成为了公认的回忆。
在这其中需要区分“真实的”和“正确的”,幸存者在纪念性阐述的时候似乎有一种特权,即使其所阐述的内容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会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了人们重构历史的方式。
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著作同样存在着“幸存者”特权问题。如在《浩然口述自传》这一著作中,大部分的口述均在当时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身上。从“幸存者”身上去采集过去政治运动的反人性证据,似乎有着人们无法辩驳的“正确性”,这是因为其见证了朴素的良知,也记录了当时的暴行,符合改革开放年代下人们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就将历史的“真实性”掩盖了。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幸存者”口述的均不真实,而是从其视角上来看,需要进行真实性的分辨,涉及明显的约束、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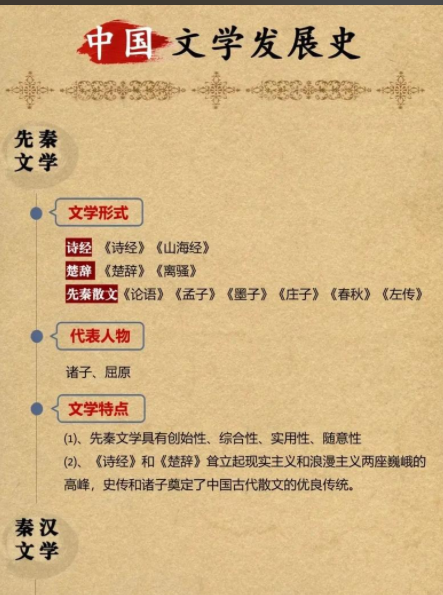
大多数口述对象都是“幸存者”,这是因为历史本就是不同人共同遭遇和经历的,有的人落难,有的人幸运。比如说,过去的文学体制曾经使一些青年作家变为社会最底层,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体制成就了许多重要人物。这些人物的材料虽然真实,但可能并不“正确”,也正是如此,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著作受访者大多都是一些“幸存者”,而不是“幸运者”,去除“幸运者”的阐述,会遗留许多问题,让历史变得简约化。另外,文学口述著作中对“幸存者”也有着不同的对待,许多挑选的“幸存者”都给予了读者一定的暗示,可能是对过去政治的心怀不满,也有对当时年代的深切情感。但目前的口述著作中很少有“幸存者”不是对过去反人类暴行的不满和批判,缺乏对未来的憧憬,口述是为了更好生活的“幸存者”少之又少。美国媒体学家认为“受害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无价值受害者”,第二种是“有价值受害者”,其中帝国的受害者通常会被认为是“有价值”。我国文学口述著作中同样如此,一些作者认为自己是“反对者”,因此其认为这些“受害者”才有价值,而今天的“受害者”虽然有着真实的史料,但是并无价值。
“幸存者”视角对于口述史料来说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当被选定的口述者经历的生活,并没有和一些受迫害情节相符,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从事电影人口述工作的启之先生,在采访某位先生的时候,所阐述的都是一些秘辛逸闻,对于启之先生来说其所述内容不高雅,但这些内容是否就毫无价值呢?受访者可以是“幸存者”,但其应当有这一视角之外的思想,采访者需要具备历史的驳杂性。
“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历史的真实性产生影响,在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发展中需要面对这一问题,其目的并不是否定“幸存者”的价值,而是希望在讲述“幸存者”故事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想空间,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
在我国当代文学口述研究中,还需要从知识分子视角来分辨“现实生活中的兴趣”。这部分内容与“幸存者”视角的分析有着一定的重合,但本质上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每一个人在回忆过去时间时,都不值得信任,即使是知识分子出版的文学口述也是如此。我国当代史并不产生于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但当代文学口述多是从知识分子视角呈现的历史感受。这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代表着某阶层诉求的普适化,会有部分历史的删除和压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视角的二元关系想象历史。在这种认知下,知识分子均认为自己是过去政治运动下的不幸者,其很多时候都是利用社会权利逻辑对过往历史进行推断,但事实上可能更复杂,并不只是进行印象化判断。理论上来说,知识分子的二元视野客体化了社会主义。当代文学口述中知识分子视角同样也客体化了政权,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著作中可窥探一二。这些著作中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欲望,也展现出其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这些被看作“人性”的主要内容,但农民对于改变贫困状态的诉求,以及工人的尊严感并未被承认,其并没有关注体制对底层人民生活和人格尊严的影响。二是知识分子对底层存在着误读和利用。知识分子常常在二维关系中纪念性思考,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著作很多都忽视了底层。知识分子常常用自己的“自信”来阐释底层,其对底层人民的真实诉求产生了误解。如何理性发声,真正了解底层的真实想法和需求,是当代文学口述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知识分子视角的普适化并不利于当代文学口述中对政权、底层的理解,容易出现误差。
对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进行研究,十分有必要,其是推动我国文学口述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口述研究中应当进一步认识采访者和受访者双方的身份,要处理好“幸存者”视角和知识分子视角口述所体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