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简化的他者: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论文
2025-09-26 15:03:46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文章探讨了女性作家如何在文学中重塑女性形象,并突破传统的“天使”或“怪物”二元对立。通过分析吉尔曼、门罗、伍尔夫和阿特伍德等人的作品,文章揭示了女性角色如何在男性话语的压制下寻找自我表达的空间,并通过反抗和自我认同实现主体性的转变。
摘要:文章探讨了女性作家如何在文学中重塑女性形象,并突破传统的“天使”或“怪物”二元对立。通过分析吉尔曼、门罗、伍尔夫和阿特伍德等人的作品,文章揭示了女性角色如何在男性话语的压制下寻找自我表达的空间,并通过反抗和自我认同实现主体性的转变。同时,文章结合巴特勒的性别建构理论,强调女性身份的可塑性以及社会建构的影响。最终,文章指出,女性作家不仅质疑并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也推动了女性话语权的扩展,使女性在文学与现实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与表达空间。
关键词:女性作家;女性形象;性别建构
在男性的眼中,女性似乎总是被视为静态的“他者”。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尤其是生殖功能方面的不同,女性往往被简化为温顺和养育的象征,即女性气质的符号。相应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女性的职责被大大缩减为顺从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这些符号和角色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所呈现的第一印象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然而,得益于女性作家的书写,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正在突破固有的“他者”身份,展现出独立的思想和行为。通过对多部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其中的互文性可以揭示女性形象的转变过程。
改变女性形象的第一步是厘清旧有的形象以及其对女性施加的影响。其中,对传统理想女性最典型的描绘之一,便是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Gilman)在《如果我是男人》(“If I Were a Man”)中塑造的莫莉(Mollie)。这一角色不仅在生理上符合所谓的“真正的女性”(“a true woman”),在社会层面上亦然。在女性外貌方面,女性被要求符合同一模式:“个子当然要小——真正的女性绝不可能高大。长相当然要漂亮——真正的女性绝不可能平庸。要任性、反复无常、迷人、善变,热爱漂亮衣服,并且总是‘穿得得体’,正如那句晦涩的说法所描述的那样。”[1]19在社会规范与期待之下,女性的角色也被固化并简化为“慈爱的妻子和全心奉献的母亲”,她们“拥有‘社交天赋’,并喜爱随之而来的‘社交生活’……就像大多数女性一样”[1]19。一旦这些固定形象被塑造,女性便难以摆脱刻板印象,例如家庭主妇的身份,因为大部分女性已经被孩子、丈夫以及家庭琐事所占据。而那些被迫成长于这些社会约定俗成中的女性,往往逐渐失去自我意识,最终变成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所形容的“纳粹集中营犯人”[2]363,正如吉尔曼在另一篇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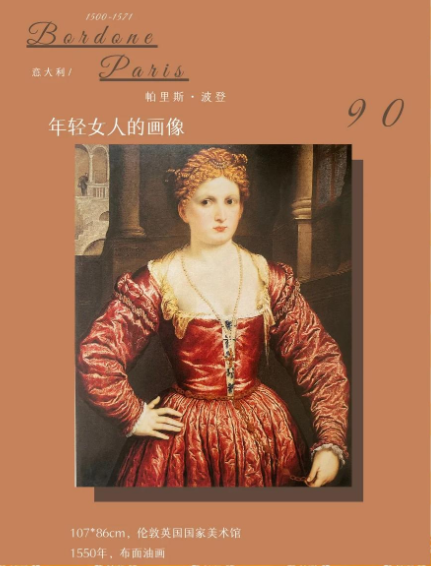
在吉尔曼的《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中,叙述者“我”也是一位顺从的妻子,凡事皆听从丈夫约翰(John)的安排。然而,与莫莉等家庭主妇形象不同,“我”渴望“合适的工作”,包括思考和写作,并认为这“会对我有好处”[1]2,因为它能够“缓解[约翰的]思想压力,使我得到休息”[1]5。但每当“我”表现出自主意志,或未能满足约翰的期望,他便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称“我”为他“可爱的小傻瓜”[1]5,同时加紧对“我”的监视,完全无视“我”真正的需求。约翰对“我”的这种对待,暗示了男性如何哄骗女性,使她们相信自己在身体上较弱,智力上较为低下。吉尔曼所刻画的男性欺骗反映出女性被剥夺自我、变得无力甚至形同死物的现实。而这一被塑造出的“他者”也就更容易被操控,服务于男性主导的社会。
吉尔曼笔下的这两位女性角色,印证了被简化为无私、被动天使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自然特征与社会特征皆由男性标准设定[3]817。然而,吉尔曼也向读者表明,女性拥有自己的思想,并渴望掌控自身命运。所谓的“天使”形象不仅仅是男性塑造出的僵化“他者”,它也意味着女性自身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除了揭示天使形象背后的多样性,女性作家还致力于推翻另一种与“天使”相对立的女性形象。因为即使女性偏离了被期望的“天使”形象,她们仍然会成为男性眼中“死的他者”,只是换成了“桀骜不驯、疯癫失控的怪物”形象。当女性开始为自己发声、争取自主权时,她们便会被视为异类。而男性为了维持父权制的权力运作,会用简化的方式将这些自主女性拒之门外,并予以压制[3]819,正如《黄色墙纸》所揭示的那样。事实上,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便指出,拥有才智的女性往往会被归为“半巫半神”,“给人畏惧,给人嘲弄”[4]42。因此,可以说,女性并非天生聪慧且疯狂,而是男性主导社会将女性的智慧视作疯癫,从而制造出这一偏见。
女性无法从事智力工作的观念既激起了女性的内疚感,也助长了男性的洋洋自得,加剧了天使与怪物这两种刻板形象的单一化。然而,女性的内疚感似乎正随着自身的觉醒以及对女性的支持日益增长而逐渐缓解。在爱丽丝·门罗的《办公室》(“The Office”)中,叙述者“我”是一位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自我认知为作家的女性。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照顾他人和清洁房屋,她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自己身上。尽管暂时离开家庭追求个人目标的想法让她感到不安,因为那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萦绕着女性,即“一个女人如果凝视着空间,凝视着一个不是她丈夫或孩子的国度,这同样被认为是对自然的冒犯”[5]60。幸运的是,叙述者在追求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是冷淡的。相比之下,《黄色壁纸》的叙述者则在家庭环境中遭受了压迫。
然而,在努力摆脱家庭主妇形象之后,《办公室》中的叙述者仍然面临社会障碍。在与男性主导观念的房东马利先生(Mr.Malley)的斗争中,叙述者因房东几次赠送礼物而陷入社会困境:“我鄙视自己屈服于这种敲诈。我甚至没有真正可怜他,只是因为我无法转身离开,我无法转身离开那种谄媚的饥渴。而他自己也知道,我的容忍是被收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因此恨我。”[5]67
一方面,“我”仍然因拒绝男性话语而感到愧疚,因为这种话语暗示“我”应该是温顺而包容的天使;另一方面,“我”也能够识破马利先生的殷勤背后隐藏的男性优越感。此外,叙述者在守护自己的空间、思想以及“摆脱他(马利先生)的权利”[5]74方面也展现出了更为坚定的意志。最终,叙述者坚定的行动仍然引发了马利先生的男性压制,他通过质疑和诽谤将“我”从一个温顺的天使塑造成一个心机深重的怪物。
尽管改变男性对女性的简化认知十分困难,门罗或许想借由女性角色所承受的两种形象的冲突来表明,女性正在慢慢觉醒并走出男性为她们设定的形象,而男性仍然停滞不前,被困在限制女性的观念之中。通过《办公室》中的叙述者,门罗指出,女性作为“他者”的身份不仅仅是天使或怪物,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当女性拒绝被支配和固定的“他者”身份时,她们开始反思并发展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她们意识到,这些强加的形象并非她们自身,而将男性和女性简化为同质化的二元对立是一种错误倾向。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强暴幻想》(“Rape Fantasies”)中,性别关系的可能性被打开:过去不可撼动的男性支配地位不再是唯一选项,女性可以压制男性,或者两性可以达成和谐的平衡。正如阿特伍德通过艾斯特尔(Estelle)的声音提出的:“……我认为如果你能让对话进行下去,情况会更好。比如说,如果你让对方知道你也是一个人,你也有自己的生活,那么一个人怎么还能对另一个刚刚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的人做出那种事呢?……”[6]102-3换言之,沟通可以成为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种可行方式,使双方在人性层面进行平等的重新审视。通过进入彼此的“他者”身份,“他者”将变得更具活力和流动性,而非僵化和死板。
然而,在想象美好的两性关系并试图证明女性不仅仅是天使或怪物的过程中,现实仍然比理想更加艰难。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以来,女性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尤其是争取投票权方面,开启了一段新的但艰难的旅程。通过无数的考验和磨难,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男性主导职业中获得了更大的进入权[7]25。如吉尔曼笔下的女性角色所示,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听从丈夫或操持家务。而从门罗和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女性开始进入职场,无论是独立工作还是受雇于企业。然而,随之而来的反弹是,男性对于女性逐渐走出传统妻子和母亲形象感到不适,并在许多男性的攻击性态度中显露出对女性的偏见,强迫她们回归所谓的“天职”,正如弗里丹敏锐地指出的:“妇女们仍被视为二等公民”[2]444。因此,性别歧视的考察成为20世纪中后期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议题[7]42。
如同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学术界对女性的歧视也相当普遍。在她的真实生活中,辛西娅·奥芝克(Cynthia Ozick)回忆了多次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经历,这些经历让她在追求作家梦想的过程中备受困扰。她表达了对男性陈旧且简化的女性观念的愤怒。奥芝克通过寓言指出,在男性的眼中,女性都是相同的,即便是那些具有公认专业成就的女性,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或卫生署长官。对于奥芝克来说,男性无法看到女性之间的个体差异,因为她们要么被视为疯狂的同行,要么被简化为所有女性共有的生殖器官。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学者,女性都被简化并彼此同质化。

尽管奥芝克确实尝试与男性沟通,这种方式仍然未能奏效。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和诋毁,女性必须勇敢反击。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强调女性的坚韧,弗里丹给出的建议与奥芝克的观点相似:“告诉那些准备在社会中工作的少女们要预料到这种微妙、令人不快的歧视——告诉她们不要悄然从事,不要以为这种其歧视会自行消失,而应当与之做坚决的斗争……一个少女不应当以自己的性别而期望得到特别的优惠,但是,她也不应当去‘顺应’那些歧视和偏见。”[2]444奥芝克、弗里丹以及其他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女性与创造性女性,并未按照男性的标准妥协女性身份,而是试图回应女性文化。换句话说,她们质疑“定义‘女性’意味着什么”[8]31。女性是否只能被限定在天使或怪物的框架之中?抑或她们只是拥有不同特质的独立个体,无法被简化为单一类型?奥芝克的生活经历提醒我们,既定的女性文化力量不容小觑,它已渗透进男性与女性的思维之中。
奥芝克在她的作品中提出文化的特殊性,以此否认对女性的特殊标签。她认为,女性身份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历史局限性,因此女性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而每一种差异都在表明,女性是无法被简化为单一形象的人类个体。因此,奥芝克挑战这些既定形象及其来源,即所谓的“普遍文化”或“标准人性”,以摧毁旧形象并构建新的身份认同。尽管强调差异有助于防止女性被简化,但将差异本身变成标签、仅仅为了凸显不同的趋势也应引起警惕。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如果认为‘女性’这一类别只是需要被填充进种族、阶级、年龄、族裔、性取向等各个组成部分,才能变得完整,那将是错误的。”[9]21当女性逐渐摆脱旧有形象时,差异可能被用作建立新形象的工具,而这一新形象可能再次成为束缚女性的桎梏。这种威胁或许正能解释奥芝克在谈论自己小说时所提及的“无情绪叙述者”的创造。对奥芝克而言,“新女性”拥有无限可能,她们不应被旧有的情感和感性定义所限制。因此,与其执着于差异,奥芝克认为女性的核心特质应是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继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为的”这一主张之后,巴特勒进一步指出:“‘女人’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持续生成的构造,它既无明确的起点,也没有终点”[9]45。这对新一代女性而言,意味着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过去的束缚正逐渐瓦解。
重新审视过去同样可以激发新的可能性,例如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对美杜莎形象的解构。在她的论文中,西苏拆解了父权文化对自我觉醒女性的传统认知——将她们视为神秘、危险、低等的美杜莎化身。然而,西苏并未仅仅追求平等,而是赋予女性接受自身差异的权利:“在女性身上,个人历史与所有女性的历史,以及国家与世界历史交融在一起。作为一名斗士,她是所有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必须具备远见,而非局限于短暂的交锋。”[10]882西苏认为,正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美杜莎的笑声才得以产生。这种笑声不再是对失去某物的恐惧,也不再是将他者简化为自我的手段,而是作为武器重新出现:“摧毁一切,粉碎制度框架,炸毁法律,颠覆‘真理’”[10]888。因此,女性可以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神话,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面对未来的可能性,女性既感到兴奋,也充满不安。
乌苏拉·勒古恩在《她为它们取消命名》中描绘了这一矛盾的状态:当她笔下的夏娃最终决定彻底离开亚当,她拒绝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物的旧有价值观。首先,勒古恩的夏娃设法打破自己与所有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就像她从西苏的美杜莎笑声中获得了力量一般。她取消了所有生物的名称,包括自己的名称,唯独保留了亚当的名字。
通过这一“取消命名”的行为,她释放了新的可能性,构想出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获得新能力的夏娃对未知世界仍然充满恐惧:“它们[其他生物]似乎比以前更接近了,过去,它们的名字像一道清晰的屏障横亘在我们之间;而如今,它们如此靠近,以至于我对它们的恐惧和它们对我的恐惧已然合而为一。”[11]27这种“亲近感与恐惧感”正是女性觉醒所带来的自我决定意义。这种体验与门罗作品中独立女性角色的经历相呼应:在《办公室》中,叙述者在离开房东后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想有一天我会再试一次,但不是现在……当我整理文字时,我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他[马利先生]”[5]73-4。类似地,勒古恩笔下的夏娃在离开亚当之后也经历了同样的心理变化:“我的话语必须像我踏出房屋时的脚步一样缓慢、新鲜、孤立而谨慎。我穿越那片冬日下静止不动的黑色树枝间,高耸的舞者一般的景象。”[11]27当这些女性角色离开男性构建的世界时,她们不可避免地会被未知和不确定性所压倒。然而,正如勒古恩所暗示的,女性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的力量,探索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唯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女性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正如勒古恩本人所说:“我只是随着女性主义的成长而成长”[8]9。
参考文献:
[1]Gilman,Charlotte.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Other Writings[M].New York:Bantam Dell,2006.
[2]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3]Gilbert,Sandra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M].Ed.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2nd ed.Oxford:Blackwell,2004.812-25.
[4]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及其他[M].人们文学出版社,2004.
[5]Munro,Alice.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and Other Stories[M].Toronto:McGraw,1968.
[6]Atwood,Margaret.Dancing Girls and Other Stories[M].New York:Anchor-Doubleday,1998.
[7]Fraser,Arvonne.“Becoming Human: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Human Rights.”Women’s Rights a Human Rights Quarterly Reader[M].Ed.Bert Lockwoo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2006.3-56.
[8]Bernardo,Susan,and Graham Murphy.Ursula K.Le Guin:A Critical Companion[M].Connecticut:Greenwood,2006.
[9]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Routledge,2006.
[10]Cixous,Hélène.“The Laugh of the Medusa”[J].Trans.Keith Cohen and Paula Cohen.Signs.1.4(1976):875-93.
[11]Le Guin,Ursula.“She Unnames Them”[J].New Yorker.21 Jan.198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