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荆浩“图真”论与乔托“写实”理念的相似性论文
2025-04-19 15:13:39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文章旨在探讨五代后梁山水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的“图真”论与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画家乔托绘画中的“写实主义”理念之间的相似性。
摘要:文章旨在探讨五代后梁山水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的“图真”论与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画家乔托绘画中的“写实主义”理念之间的相似性。通过对比研究浅析,试揭示这两种艺术理论在文化背景、艺术理念和技术手法等角度的相似之处,主要纵向归纳为三个层面:对客观现实的忠实再现、物象情绪与精神性的表达以及技法服务于思想意境的传递,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画论及西方美术代表性观念的理解。文章还选取了荆浩《匡庐图》和乔托《哀悼耶稣》两幅作品作案例分析,从艺术实践的方面进一步体悟验证了艺术理论的相似性。
关键词:荆浩;图真;《笔法记》;乔托;写实主义
一、荆浩“图真”概念的理论基础
荆浩,字浩然,号洪谷子,唐末约850年生人,卒于约五代后梁初,河内沁水人。唐末五代后梁时期著名画家之一。早年从儒,为唐末小官,亦尤工山水,曾在长安从画多年。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社会陷入动荡之中,文人士大夫纷纷隐居深山以避祸事。彼时荆浩即隐居太行洪谷,悉心山水。期间,其创作了不朽名画《匡庐图》;理论领域,撰写了著名山水画论《笔法记》,以对答式文体阐述山水画创作见解。书中提出并讨论了“图真”“搜妙创真”、绘景“六要”、用笔“四势”和“有形之病与无形之病”,对谢赫“六法”论作进一步总结。尝自谓:“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1],将唐代“水晕墨章”画法进一步推向成熟。
在笔法构图领域,荆浩在唐代山水画基础上亦有创造性突破——山水全景构图及皴法技巧皆始于浩,尤其是皴法的成熟,成为中国山水画成熟的标志。因长期居于北方,荆浩笔下山川大都雄奇瑰丽、层峦叠嶂,被认为是五代北方山水画派开山鼻祖之一,关仝、李成,范宽都与其有师承关系,共同铸就了中国山水画第一座高峰——宋代山水画艺术,影响深远。
本文所探讨的核心之一“图真”概念便是荆浩在其代表作《笔法记》中首次提出:“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1]
何谓“图真”?荆浩明确界定了“图真”与“形似”的界限——“图真者,非形似也。”可见其所追求的“真”并、不仅仅是“形”的真,更在于内在的“度”。这就涉及“形似”与“神似”的问题。

《尔雅·释诂》定义:“画,形也。”①简明扼要,强调绘画讲求描摹外形的重要性,形准则明,反映古人早期对于绘画实用功能性一大偏重。因而私以为“形似”暂且停留于画者作为主体,有意追求审美客体之“真”的层面,而“图真”,强调“真”在“气质俱胜”,要求“真”的本源。荆浩进一步指出:“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为生,为受其性。”[1]即“物象之源”在于物以生之性,此性以神(气韵)显。所谓以神役物,“图真”之要务是基于物像之基础而高于物像的画者主体内在表达,是对所绘之物深入挖掘并赋予个人精神性寄托的求真过程,最终达到“神似”境界,气韵生动。正如高居瀚(James Cahill)所言:“大自然从来不会创造出矫揉造作形态错误的树石,艺术家当然创造不出千真万确的大自然,比真山水都要真的山水画图”[2]。
由此可得,“图真”的本质“真”在传神与“得气韵”之上升华,“形似”与“神似”兼备,若只是得物之形,而遗物之气,则“象之死也”。
要“图真”,须明“六要”。《笔法记》中所提绘景六要素共同构成了“图真”论的丰富内涵:“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1],以“气”“韵”二要为核心,同其余四要辅以绘画到达本真纯然之境。
“气”与“韵”早在六朝谢赫《古画品录》中即有提出,但谢赫之“气韵”是针对人物画而言,荆浩则是针对山水画而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1]。心随笔运实质上是笔随心运,不以心为形役,才能让思想主导用笔,求取“真”物象而不惑;隐没笔墨痕迹确可立不俗“真”形象,风雅自出。“气”与“韵”相合于是才有形神兼备,是“图真”至臻之境界。
“思”则是“删拔大要”,在创作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凝铸思虑要表达的物象。需注意的是,“思”的过程并不是体现在画面上的经营构思,不可与“经营位置”混为一谈,倒是与庄子的“既雕既凿,复归于朴”②不谋而合。
“景”要求妙造自然山川以传其真貌,“搜妙创真”。这就再次强调了画者需将物象之“真”同主观意识之“真”相统一。
最后是“笔”与“墨”。荆浩在《笔法记》中多有对前人笔墨技法的评述,可谓是我国首谈“笔墨并重”者,谢赫六法中只谈“骨法用笔”[3],未涉及两者的联系。“笔”为法则,随物之变而运转变通,不拘形式所限而自如——与“气”暗合;“墨”重渲染,浓淡有致以品自然深浅,而得天之趣——与“韵”暗合。因此,笔墨技法应为“气”“韵”“思”等审美创作意识服务,使画者不囿于笔墨囫囵之中。
夫此“六要”之技,是“图真”理论坚实的实践支撑,“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1]。
二、乔托绘画中的“写实”理念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6~1337年),早期文艺复兴先驱者之一、佛罗伦萨画派鼻祖。他的出现可谓造就了欧洲绘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文艺复兴因他而第一次有了曼妙的“胎动”。其从艺之路颇具戏剧性:早年时乔托在佛罗伦萨或者是穆杰罗的韦斯皮尼亚诺乡野间放牧,传闻中某次放羊时,他刻绘在路边石头上的山羊被途经于此的契马布埃(Cimabue)发觉,契马布埃被乔托的绘画天赋所吸引,于是将其带回自己的工坊做学徒。
如果说契马布埃延续了拜占庭艺术在彻底变革之前的最后辉煌,那么乔托则与过去决裂得更为彻底。他创造了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并由此开创“早期科学化”(early scientific)时代,确立了绘画在其后约7个世纪的主要艺术形式地位,重拾了被中世纪艺术家搁置许久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如此种种,最终推动了以乔托为始的艺术手法重要变革——由此被誉为“西方绘画艺术之父”。
乔托以湿壁画见长,尤其善画宗教题材壁画,受斯科韦尼家族委托于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所绘组画《基督救赎》(共38幅)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这组湿壁画共有38幅,被安排在三层水平饰带上,分别表现了圣母以及她父母约雅敬(Joachim)和安娜(Anna)的生平(顶层)、耶稣的生平和传道(中层),以及耶稣受难和耶稣复活(底层),见证了乔托在透视法上的伟大突破与“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运用暗部与亮部的强烈对比来产生立体感)的萌芽,揭示了乔托巧妙地将生动的叙述、神圣的教义和真实的再现有机融合的过程,为文艺复兴与写实主义的勃兴奠定坚实基础。
无论乔托的艺术风格受到过多么复杂多变的影响,其真正遵从恪守的信条只有“自然”——由可见事物构成的现实世界。重视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观察,认识到视觉世界只有通过观察才能被分析与理解,这就表明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模仿自然的层面,而是通过忠实自然进一步推测其可见规律,从而揭示自然——这是对现实认识的跃升与纵向深入的思考过程,为同时代的艺术家指明了一条艺术表达形式的全新路径:由于乔托,西方画坛毅然将目光逐渐转向了现实世界。
立足于现实的奇点,乔托早期的作品《宝座上的圣母》(Madonna Enthroned)体现了其为再现性艺术作出的贡献——人物开始具有雕塑般的坚实体积感、实体感与空间感——乔托新艺术的目标。他笔下的圣人不再如中世纪宗教画一般程式化、扁平化,而是让人感到立体而生动的再现,这无疑需要对现实的观察足够精微才能做到。圣母的身体不再被漠视或刻意淡化,通过隆起的胸部我们可以体会到画者表达的坚定态度,投射的阴影强化了人物的雕塑感,使其稳稳坐落在属于自己的宝座空间之中。
在这里还不得不提及当时圣方济各修道会起到的作用。罗马教廷一贯宣扬的禁欲主义已逐渐失去民心,反抗之声日益高涨,世俗生活与一定程度上的人性解放开始得到歌颂与宣扬。纵观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可谓也是“神权”“皇权”与“人权”相互博弈的时期,圣方济各修道会的崛起恰好进一步起到了一定助推作用:传统“父权”式的硬性传教方式得到改善,“慈母”式的教诲关怀式传教得以实现,这不失为艺术家们扫清客观上束缚和桎梏的一种方式。乔托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为自我艺术表达争取到了更大的自由,在绘画中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自由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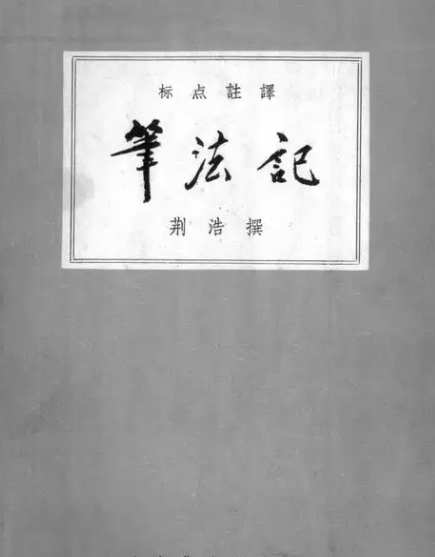
三、荆浩“图真”论与乔托“写实”理念的相似性——以《匡庐图》和《哀悼耶稣》为例
1.对客观现实的忠实再现
对比前文二者理论可得,荆浩的“图真”与乔托的“写实”首先都是之于客观现实而言,无论是荆浩重视的远取势,近取质,躬身自然观察、体验还是乔托重视的现场观摩与写生,都涵盖了通过观察自然而贴近自然,从而再现自然的第一个层面。
先观荆浩所作《匡庐图》,开图千里,纵向布局,将太行山雄奇壮丽的景致全然展现于眼前。由下至上观画,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上段山峰巍峨耸立,山岩轮廓线条疏密有致排布,皴擦点染依山体走势而施;中段以水域相隔,广袤通透,与庞大远景所绘高山相对,人烟迹显于中景,有宅院一座掩映于层林浸染之中,山岩诸峰形态更趋多变,一条山路蜿蜒而出,瀑布泻于两峰之间,颇令人身临其境、心生向往;下段则描绘山脚景致,地势由险转缓、豁然开朗,激流汇入江河,平静悠远。河上一叶扁舟,一船夫蓑衣蓬蒿,似在引领观者走入眼前佳景,画者还细细再现了河畔屋舍俨然、路旁行人悠然的一派恬静景象,足见其对自然观察之精微。
再看乔托所绘《哀悼耶稣》,此为帕多瓦阿雷纳礼拜堂所组画《基督救赎》中最为精彩的一幅,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写实主义氛围尤其浓厚的一幅。画面中,圣约翰俯身向下凝视着已被卸下十字架的耶稣,姿势自然而肃穆,毫无矫饰之感。天使盘旋在上空,似乎无法接受耶稣逝去的事实而乱作一团,圣母马利亚环抱耶稣,用手支撑着他的上半身,一位背对画面的女使托着主的头部——就像现实生活中刚刚发生的一瞬,生动地闯入观者视线,假使去掉圣人们头上的光环,乔托描绘的可以说就是人间最为真实的场景。目之所及不再是神话教义抽象缥缈的遥远图解,而是现实场景的生动再现。
2.物象情绪与精神性的表达
从荆浩强调“度物象而取其真”——追求“气韵之真”与乔托对人物表情与姿态的有意识描绘,二者观念出现了第二层相似之处:“形似”之上而“传神”,物象的内在情绪与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与表达。
《匡庐图》巨壑层叠,山石苍劲,却不乏虚怀若谷的隐士情思。荆浩在描摹主要山景之余,亦增添了隐逸山间的文士生活,天人合一的淡然出世态度透过那笔墨营造的缭绕云雾与隐约峰峦跃然纸上,氤氲出一种宁静旷远的氛围——那高山流水是否也寄托着追求心灵自由、超然于物外的向往?包括画面中留白的部分,加深了山水物象的呼吸感,使空灵与深远的情思更上一层楼。虚实之间,大山大水的气韵与精神性油然而生。
而《哀悼耶稣》之中,表情与姿态成为乔托表达人物情绪的一大支点。天使们“失去”了双腿,张开双臂仿佛欲言又止,一股人性的脆弱与无助被恰到好处地传达出来。细看圣母、天使与门徒脸上的表情,无一不具代入感:马利亚的悲恸、抹大拉的马利亚与圣约翰的动容、右侧两位门徒那一瞬的适从以及前景中两位蒙着头巾的哀悼者低声啜泣…悲与哀仿佛得以穿透画面,直击观者的灵魂。
3.技法服务于思想意境的传递
第三层相似性则是之于掌握“用笔”并使其服务于思想意境的传递。此为荆浩得“形似”、达“气韵”、足“六要”后图“真景”的最高境界,亦为乔托用“高贵的节制”③追求的绘画之热情、生命之自白以及神圣之皈依。
《匡庐图》首次采用了全景式构图,浩浩汤汤可谓一气呵成。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集》中提出山水“三远法”——“高远、平远、深远”,荆浩的取景构图安排正合乎“高远”与“平远”之境界。从用笔上看,除去中锋“点”“擢”,密点刻绘山岩肌理以外,荆浩还采用了独特的解索皴和小斧劈皴。水墨之色天然去雕饰,超越万华而复归自然本原。《匡庐图》全画是“水墨晕章”的绝佳体现,以墨代彩,巧用墨色浓淡干湿对比造景,且看墨色随着清泉泻出而变化,水面又先以淡墨晕染,重墨绘出江舟、横桥,浓淡衬托相宜。心随笔运、搜妙创真,气韵托形而生,真正运笔墨于胸中、合乎于天地之间,备仪不俗,取之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忘笔墨而有真景”[1]。
《哀悼耶稣》的复杂构图安排与人物分组同样别有深意。巨岩成对角线倾斜于画面之上,连同上方“智慧之树”一道将观者视线引向左下角的关注焦点——尽管并不在中心位置,更添几分活力。乔托还大胆采用“背影”人物以强调前景,将他们作为远景人物的视觉位置中介,是对传统正面像描绘形式法则的突破革新,增强了“旁观者”的参与感。光影的灵活运用对空间及人物神韵的刻画起到了极大的支撑,象征光线方向的阴影在画面中央的俯身人物形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衣褶阴影为分割线,二人分别被推向前景与背景,空间层次丰富有序。这不仅是乔托对绘画史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亦是图像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如何将复杂的形式及情感的共鸣结合到一起表达,挖掘宗教神圣题材中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光辉。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荆浩的“图真”论和乔托的写实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进而总结概括出两者在三大层面的相似性。首先,他们都强调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再现,通过对自然万物细致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捕捉物象“形”的真实感。其次,他们都注重物象情绪与精神性的表达,通过对物象内在气质的挖掘阐发,做到细腻的情感传递,使画面具有“神韵”层面的真实感和共情的艺术魅力。最后,在重视笔墨技巧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巧妙的构图和氛围营造,使画面具有层次感和深度,做到笔墨合乎天地自然,达到求意境之“真”的崇高境界。希望在对过去中西方两位画家代表性理念相似性浅析的过程中,进一步思考中西方艺术理论比较研究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运用及启示。
注释:
①《尔雅·释诂》[M].中华书局,2009.p14.
②庄子.《庄子·山木》[M].中华书局,2007.p215.
③Frederick Hartt.《Giotto and the Beginnings of Italian Painting》.Harper&Row,1969.p45.
参考文献
[1]荆浩.笔法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高居瀚(James Cahill).《山水画图》(Hills Beyond: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Academy Styl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3]谢赫.古画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