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与布鲁姆文学批评观的比较—政治批评还是审美批评?论文
2025-03-22 14:13:01 来源: 作者:xujingjing
摘要:文学批评的主题之一是探讨文学作品的本质、内涵和意义。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特里·伊格尔顿与哈罗德·布鲁姆是两位备受瞩目的学者,他们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对西方文学经典进行了探讨。伊格尔顿是一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他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对现代文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在伊格尔顿的著作和论文中曾多次对布鲁姆的观点进行过批评,树立文学批评的“政治批评”原则—“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就像在南非的体育运动中一样,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与之相对,布鲁姆则以其深厚的文学知识和美学素养坚守着关于
文学批评的主题之一是探讨文学作品的本质、内涵和意义。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特里·伊格尔顿与哈罗德·布鲁姆是两位备受瞩目的学者,他们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对西方文学经典进行了探讨。伊格尔顿是一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他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对现代文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在伊格尔顿的著作和论文中曾多次对布鲁姆的观点进行过批评,树立文学批评的“政治批评”原则—“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就像在南非的体育运动中一样,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与之相对,布鲁姆则以其深厚的文学知识和美学素养坚守着关于经典作品的“审美批评”的标准。在他的理论中,审美永远是检验一部作品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对美的理解让我们得以存在,也使我们认知中时间的质量提高了,审美的时刻永远没有尽头”。
这两位学者通过各自的理论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对文学经典的不同解读和观察角度,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对于文学理论的看法。在这个背景下,本文通过深入比较和分析特里·伊格尔顿与哈罗德·布鲁姆在文学经典观方面的不同见解,从而揭示他们各自的理论框架、批评标准以及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
特里·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来源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源于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分析,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信仰体系、价值观或理论框架,它在社会中起着指导和影响人们思想、行为和行动的作用。马克思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便无法脱离其背后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话语问题,不如说是阶级社会本身的客观结构。”
伊格尔顿在吸收了传统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注重社会结构的层面,并将其与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联系起来,“简言之,意识形态不单单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讲出的命题之类),而是一个话语问题,是置身于历史当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流”。因此,对于文学的批评需要从外部的角度考察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形态的塑造,挖掘出文学背后的复杂的权力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的兴起进行分析,发现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突然的兴起是由于当时宗教的衰落,英国文学需要代替宗教承担稳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任务。“英国文学具有三重作用:当然,我认为它仍然要愉悦和教导我们,但是首先它应该拯救我们的灵魂和疗救国家。”通过对于英国文学的分析,伊格尔顿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应当超越狭隘的定义,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话语实践”领域之内。因此,文学自然就与其所产生的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批评也就走上一种“政治批评”。

伊格尔顿所提出的“政治批评”中的“政治”与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政治不同,“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它代表着一种社会上存在的复杂权力关系。因此,政治批评的“特殊之处将会在于它对于种种话语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以及它们之间如何产生这些效果的关心”。在对20世纪的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后,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文学理论的故事却是一个从种种这样的现实逃向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一系列替代的故事”。他认为这些文学理论的共通性在于,它们试图通过文学和哲学的途径来解决现实问题,但却往往没有积极地与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相联系。而政治批评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更具有实践性,通过关注话语的效果和权力关系,政治批评能够将文学作品与社会政治相联系,揭示文学作品中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
布鲁姆的审美批评
布鲁姆因其广泛的西方文学文化领域涉猎,以及对当代西方文论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批评理论。布鲁姆的审美批评来源于他对于西方经典文学的捍卫,在对于经典作品的审美标准进行分析时,他认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渗入进经典”。
在他的审美批评理论中,布鲁姆强调了文学作品审美的自主性和陌生性。在审美自主性上,布鲁姆“接受了康德关于审美活动是非功利性的、审美判断更多的是主观的心理功能以及艺术天才等观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表明,审美判断来源于每个人的“共通感”而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审美来源于人主观心理的判断。可以看出,布鲁姆正是继承了康德的观点。布鲁姆十分强调“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审美体验是个人的、独特的,而不是一种社会共识,因此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应该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而审美的陌生性“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陌生性的作用在于通过让人们重新看待已知的事物,使人们能够超越习惯性的观念和固有的认知模式,从而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布鲁姆的审美批评中也像康德一样提倡天才的创造。他将莎士比亚置于整个西方文学经典体系的核心位置,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整个西方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价值。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心,首先在于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卓越的语言表达,深刻地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体验。此外,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充分借鉴了早期文学作品和人物刻画的经验,并开启了创新的道路。在他的著作《西方正典》中,莎士比亚成为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参照系和对比对象,“他的心灵就是地平线,在地平线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尚无法看到”。
布鲁姆的审美批评通过对于审美自主性、陌生性的强调,对于经典中天才创造的肯定,表现出他在当代多元价值的时代中建立起审美和经典的权威的一种尝试。布鲁姆相信,审美价值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在布鲁姆看来,这种审美和经典的权威不仅可以为文学作品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的美。
对比与比较
伊格尔顿曾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对布鲁姆的文学观点作出过犀利的批评:“布鲁姆的批评理论完完全全地暴露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人本主义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在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后结构主义之后,复归于一个明朗而乐观的人的信念已经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像布鲁姆的人本主义一样已经接受了这些学说的令人痛苦的压力的人本主义都注定要受到它们的致命损伤和污染……于是一个批评阅读的成功与否到头来就不在于其真理价值,而在于批评家自己的修辞力。”伊格尔顿肯定了布鲁姆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式,积极地吸纳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元素,从而为文学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批评了布鲁姆的“修辞式”的批评,认为布鲁姆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采用了晦涩而尼采式的修辞,试图掩盖布鲁姆对真理、价值和人道主义的天真和绝望。与此相对的,布鲁姆也在《西方正典》中明确对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与伊格尔顿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并将20世纪兴起的“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归纳为他所说的“憎恨学派”。
他们文学批评观点的区别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于莎士比亚的看法上。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把“莎士比亚”列为“贵族时代的第一人”,认为莎士比亚后的西方作家无疑不因他而产生“影响的焦虑”,在文中,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赞赏溢于言表:“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与之相对的,伊格尔顿正是对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经典文学做出批评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是伟大文学是因为文学制度将他构成为这样……离开了作品在种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生活和制度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对待方式,就根本无所谓‘真正’伟大的或‘真正’如何的文学。”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来源于文学制度与其背后的权力话语相关,而文学制度又和整个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相联系。因此,伊格尔顿反对这种经典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的说法,“文学批评根据某些制度化了的‘文学’标准来挑选、加工、修正和改写文本,但是这些标准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争辩的,而且始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
这种观点截然对立的背后是他们背后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的不同。首先,布鲁姆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从童年时期他就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浓厚兴趣,到后来他的批评理论中流露出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喜爱和继承。浪漫主义强调个体的主观性和情感抒发,认为作品应该是创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客观的描写。布鲁姆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也强调了个体情感的重要性,他关注作品中的情感体验,并将之视为作品审美价值的一部分。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想象力和创造性的重要性,作家应该具备独特的创作能力,通过想象力创造出独特的世界和人物。布鲁姆也注重作家的创造性,他将作家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看作是作品被视为经典的关键。此外,布鲁姆也受到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布鲁姆在《影响的剖析》中说,“我追随康德,相信审美活动调动了主体的幽微之处,不会被意识形态所染指”。布鲁姆相信审美活动能够调动人类主体内部深层的情感和感知,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德国古典美学中无功利性原则的一种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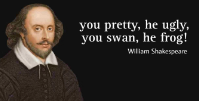
而伊格尔顿则是一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师从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伊格尔顿从他那里学会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英国文学中的重要文本。在后期,他以“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欧美文学批评中的各个流派,主张将文学艺术视作一种有关意识形态的生产。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永远和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复杂权力关系的产物。因此,他在《美学意识形态》序言中明确表达了他对于布鲁姆这种批评家的批评,“我想驳斥这样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任何联系都必定是令人厌恶反感无所适从”。
通过对比伊格尔顿和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的观点,能够反映出文学理论的两种不同的走向。在今天,文学理论有一种突破原有文本的限制、转向文化批评的倾向。尤其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不断涌现,传播途径也多种多样。如以前的电影、电视与流行音乐到今天的短视频、AR游戏、元宇宙等文化形式,文学从文化的中心转移到边缘角落中去,这使得文学理论也面临深刻的变革。就像本雅明在一百年前对于电影艺术的批评一样,艺术的光晕被各种技术驱散,开始走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这种变化,伊格尔顿和布鲁姆都十分细致地分析,但伊格尔顿选择了接受这种变化,开始积极使各种因素—阶级、种族、性别等介入文学,而布鲁姆选择坚守他内心里永久坚信的审美价值。总体来说,政治批评与美学批评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它们都能为解读文学作品、文化现象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