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的阿勒泰》对休闲生活的建构论文
2025-01-23 12:01:05 来源: 作者:dingchenxi
摘要:休闲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空间中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当前内卷化的社会背景下,《我的阿勒泰》试图在主体言说、生活构造和恒常表达三方面建构休闲生活图景。
摘要:休闲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空间中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当前内卷化的社会背景下,《我的阿勒泰》试图在主体言说、生活构造和恒常表达三方面建构休闲生活图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主体通过感官体验和精神世界两方面的经验叙述,生成阿勒泰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场景,带有自然文学的色彩。而日常生活则通过客观冷静的叙述,展现,挖掘出生活中的细节及其背后悲哀与悠闲并存的倾向,表现出自然审美中净化与沉思的特质。恒常的表达是指对阿勒泰生活,习俗和地域等稳定性的塑造,展现出历史的承接性,反映出马克思视域下劳动与休闲内在统一的特性。最终《我的阿勒泰》对休闲生活的建构展现出其价值内蕴及其所衍生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休闲生活;主体性;审美性;恒常特性;价值内蕴
休闲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空间中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近段时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其带有域外风情和松弛感的生活图景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一时间成为网络上讨论的热点。其实,早在2010年前后的文坛上,原作者李娟就是一个极受关注的名字,她关乎阿勒泰的散文得到热捧,也获得了各种奖项,例如天山文艺奖、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上海文学奖等。在李娟作品的相关评述上,研究者则注意到其与自然文学相联系的生态批评上,如郑亮,王聪聪的《阿勒泰意象:李娟散文的生态批评阅读》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下分析了文本内容;[1]齐红的《让自然发言:李娟散文的生态伦理观及其意义》则论证了李娟散文描绘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2]可见,李娟散文存在明显的自然文学元素,值得研究者们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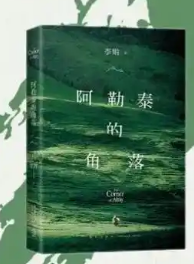
如果仅从作品进行分析,当前的生态视角研究并不能全面解释当前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火热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我的阿勒泰》作为自然文学的一种类型,其中的休闲元素也不可忽视。马*思*义视域下的休闲生活常常是研究者讨论的话题,楼嘉军认为“休闲活动是人们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载体。”[3];谢洪恩,孙林,张世慧则认为休闲文化生态系统与和谐、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4];庞睿的《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逻辑建构》就通过挖掘马克思文本存在的内涵,隐喻,来说明马*思*义也存在着对休闲的论述,具体表现在“时间、异化、自由、和谐与幸福”这几个方面[5]。《我的阿勒泰》中体现着对和谐生活,幸福感的获得和时间本质的理解,同时这一休闲特质已不再是特定阶层的象征,而是把休闲主体重新归之于人民大众身边。因此,本文试图从言说主体、生活构造和恒常表达三方面论述《我的阿勒泰》这一文本是如何建构休闲生活的,发掘出文本其中的内蕴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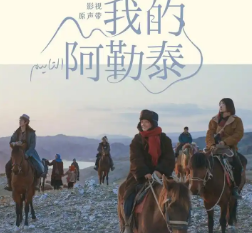
一、主体的言说方式
《我的阿勒泰》对休闲生活的建构,首先聚焦于主体是如何言说的。根据《文化研究关键词》所解释,主体“指的是一种有着主观体验或与其他实体(或客体)有关系的存在”,”这一术语常常被当作‘人’的同义词,或指涉人的意识”[6]。在文本中,主体不仅是讲述者,更是通过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融为一体,以来构建出休闲生活的图景。这一过程中,主体对自然的观照,带有自然文学痕迹,通常来说,“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7]《我的阿勒泰》以真实的感官体验来展现新疆的风土人情,通过各种自然景观和生活场景的描绘,并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感官体验与精神世界相结合的方式多维度描述自己周边生活。这种对自然的观照带有审美意识,内在的精神与美感在细腻的笔触下,自然景物与宁静的韵味是相结合的。
因此,通过经验叙述,主体的形象得以生成。个体经历的细致描写使主体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个人的生活经验与自然环境的交融,使得主体形象愈加得生动。这种经验叙述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的点滴,也涵盖了对自然的感知和内心的情感波动。《我的阿勒泰》把书分为“记忆之中(2007-2009)”和“角落之中(2002-2006)”两部分,承载着作者李娟的个人经历与情感体验,同时展现了她对阿勒泰地区生活的多维观察。前者更多的是作为近期生活经验的记录,是对家庭日常的体验,如家养兔子、摩托车、卫星电话等;后者则侧重于对青春时期的回忆和个人成长的记录,就像“年轻的想法永无止境”“我能感觉到他年少的心灵中某种强大事物正在平静呼吸。”[8]等记述。在这类经验叙述下,《我的阿勒泰》构建出独特的休闲生活元素,阿勒泰的生活细节和土地的自然美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休闲生活状态,读者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在成长中的主体形象。这些鲜明的自然、个性特征,是对人类普遍的情感和经验的共振。在经验叙述下主体有其具体的形象特征,并展现出其向内挖掘的情思,某种程度上深化了文本对休闲生活的探索。
再者,个人经历与情感体验是构造主体形象的双重途径,其所孕育出的情感是真实主体形象的展现。在《我的阿勒泰》中,个人经历与情感体验代表着主体形象的真实与完整。经验叙述方式不仅呈现了阿勒泰地区的图景,也通过个人的真切表达,构造出一幅休闲图景。其涉及的是对生活方式的展示及精神境界的追求,展现的是现代人对平和宁静生活等的共鸣。通过双重途径的叙述,《我的阿勒泰》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带有生命力量和情感温度的休闲生活画卷,指向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
最终,主体形象的叙述及生成也奠定了其叙述风格。具体表现在文本叙述下的语气:清新明快、细致入微,缓慢悠长,同时兼具感伤色彩。这些叙述特征巧妙地体现了休闲生活的元素。首先,以清新明快的语言透露出一种惬意的生活状态,契合了休闲生活的本质——自由和放松,读者能够感知到一种远离都市喧嚣、亲近自然的休闲体验;其次,细致入微的描写为文本增添了丰富的生活细节,使得休闲元素更加具体和生动;再次,缓慢悠长的叙述节奏则加强了文本的休闲感。李娟通过缓慢的叙述节奏是传达情感的重要策略,这一节奏感与阿勒泰的悠闲生活方式相契合,使得文本带有宁静平和的氛围;此外,兼具感伤色彩的叙述风格也为文本中的休闲元素增添了一层深度;最后,这种感伤色彩让读者在感知文本带来的休闲体验空间的同时,也能从其背后感知到生活的复杂韵味。
二、生活的构造策略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过:“生活方式通常有一套价值观为之辩护。”[9]在某种程度上,生活方式是一种受价值观支配的主体活动形式,而主体活动则达成了对生活构造的目的。从《我的阿勒泰》的文本层面进行展开可以看到,其试图通过对人事互动,景物描摹、空间围合及置身于空间中的生活状态来勾勒出休闲世界的画面。
《我的阿勒泰》通过细节呈现日常生活。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在生活的互动上,他人打电话的趣事、习惯吐舌头的外婆、乡村舞会上隐藏的情愫、弹唱会的一些意外及其盛况、和异族朋友“古贝”交流等。另一方面,对自然的观照下,水、云、风、林、戈壁等是文本中常出现的字眼。水分别指代河水,水泉,水波,水晶,水渠等景观;云则衍生出云雾、云块、夜云等相关意象;林则出现了树林、竹林、森林等字眼;戈壁则在九篇短文中反复出现,占据了全书短文的三分之一篇幅。主体在生活琐事的互动下,彰显休闲生活的特征,它表现的是生活的趣味,温情和轻松氛围。通过这些描写,文本构建出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休闲生活方式。区别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下,阿勒泰世界中回归自然、享受生活的方式,成了一种追寻自由,挖掘幸福生活的途径。而这对简单、美好生活的向往,则通向了回归自然、回归内心的幸福观追求。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生活哲学的表达,休闲生活的构建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美的享受,它也使向内转的心灵满足得以阐释。
在第一人称叙述下,特定的地域文化细节围合出文本空间。“围合”作为建筑学的名词,核心点在于创造出具有特定功能和意义的空间。《我的阿勒泰》通过对自然体验和特定人事的呈现,使人们在审美体验下重新进入构建好的休闲空间,体现了休闲生活的最高境界。这里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休闲与审美之间的重新整合与再现,“休闲之为理想在于进入了人类的自在生命领域,审美之为理想在于进入了生命的自由体验状态,两者有着共同的前提与指向,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10]主体在“自由体验”的审美表征下,外部环境的广阔与开放,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追求,都在背后浮现着其对自由、通达和满足的生活状态的“自在生命领域”追求。而在读者的视野下,某种理想生活状态的渴望,超越了当前物质生活,追求精神层面的自由景观被呈现出来。文本通过对地方风貌和人物活动的描述,使读者能够在审美体验中进入带有休闲元素的空间。此空间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让读者在自然与文化的交汇中寻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文本空间也展现出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生活状态。文本中描写的生活空间,如喀吾图、阿克哈拉村、到处可见的矿业等,展现的不仅是阿勒泰的辽阔神秘,也展现人们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常态,人们在这一环境下劳作,生活。尽管这在西方传统休闲理论视域下是充满悖论的,但在马克思劳动休闲观念下,“在消除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劳动与休闲的内在统一有可能成为现实。”[11]文本空间正是作为叙述者和读者审美体验的媒介,生成了非异化劳动的“世界”。主体捕捉到了自然的生机和人们的生活状态,感知到特定文化语境下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读者则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愉悦和心灵满足。文本空间中的休闲生活方式,正是对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诗意表达,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的短暂救赎。
三、恒常的最终表达
在《我的阿勒泰》的空间构造下,阿勒泰的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得以描摹和叙述,而这一空间背后有着特定文化语境下劳动与休闲内在统一的恒常生活特性。通常来说,恒常可以描述习惯、规律或某种持续的状态,具有稳定性;在哲学中,恒常暗示某种永恒的真理或本质,即在时间和变化中仍旧存在的东西。《我的阿勒泰》在生活,习俗,地域等方面都存在持续性与稳定性。短篇《喀吾图的永恒之处》讲述主体在喀吾图生活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是平静的,什么都没法轻易记住,但喀吾图的各种生活画面却记忆犹新:季节更替,人们活动状态的变化——夏天劳作、秋天收成、冬天喝酒——他们从劳作到放松,再到悠闲;习俗上,寡妇再婚,孩子归男方的规定,使得离异母亲“吐滚”因此不愿再婚,一人操持家务,抚养三个孩子;主人公“我”的日子“太过安稳,太过放心了,让人有了依赖,竟懒惰下来了”,也因为“永远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也没法滋生别的什么想法”而喀吾图“只是让你进入它的秩序而已,然后就面对你停止下来”[12]等。可以看到,“恒常”不是抽象的,反而是具体的。打捞、发掘和表现日常生活背后具有的传统意义有着通向恒常的价值意蕴,表现在传统事物在生活现场面前重放光芒,表现出一道恒常的风景线。阿勒泰生活线浸润在一段轮回往复的时间上,一代又一代人年复一年做着相同的事,生活在循环往复、迟缓单一条件下行进。这就与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世界”有着一种微妙的互文性,他们在空间、时间都自足的生活图景上都下了有意或无意的功夫。
由此,恒常生活体现出了一定的文化记忆,并影响着个体和社区的身份认同。记忆作为一种联结生活的手段,在扬·阿斯曼看来,“借助文化记忆,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13],文化记忆所具有的交往性、纽带性和集体性把个体活动及其相应地域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让集体的文化活动超越个体年龄限制成为一种能够延续的“仪式”。主人公在《喀吾图的永恒之处》感知到的喀吾图对当地人们进行同化的特性,他的异族身份尽管能使其能够暂时抽离(他最终离开了喀吾图去其他地方生活),却也留下地域的相关印记,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个事件。可以看到,文化记忆不仅渗透在个体的归属感中,也塑造了特定社区的集体记忆,成为维系其独特文化传统的纽带。记忆也不仅仅是过去的简单回溯,更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历史体验,它影响着个体的生活经历,也在不断塑造着所属社区的文化认同。
而恒常生活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最终则是构建了休闲生活的合法性。从个体到集体,人们对当地文化带有认同感;从劳作到休闲,人们在季节的更替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这一生活方式有着劳动与休闲内在统一的马克思的休闲思想色彩,生活方式的持续性让文化认同得以延续和巩固。这种文化认同感表面上是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体验中获得,实际上则是在无形中接纳、延续了传统生活方式。可以说,认同感是恒常生活的基石,恒常生活的特性反过来加固了人们的认同感。也就是说,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文化认同感提供了恒常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恒常生活的实践经验,又不断深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二者共同塑造出并维系着这一休闲世界。
四、结语
通过对文本的主体言说方式、生活建构策略和恒常生活表达的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看到了一幅带有自然美感和地域特色的休闲生活图景。这一图景以其真诚、宁静和深渊的特征,向读者营呈现出一种休闲生活图景的想象。在当代内卷化及高节奏的城市生活背景下,休闲生活的描绘自然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心灵上的宽慰和启迪。在这样的文本构建下,休闲生活不仅是个体精神世界的寄托,也是承接着对传统生活的认同与发展。休闲生活在历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传承,也在当代马克思文化视域下看到了接驳点,《我的阿勒泰》所传达的价值意蕴已经在文本层面得到体现。而在文本之外,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素朴生活观念的重新兴起也在扩展延伸阿勒泰世界的文本价值,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引发了共鸣与反思,体现出休闲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郑亮,王聪聪.阿勒泰意象:李娟散文的生态批评阅读[J].江汉论坛,2013,(02):130-134.
[2]齐红.让自然发言:李娟散文的生态伦理观及其意义[J].齐鲁学刊,2013,(04):157-160.
[3]楼嘉军.休闲初探[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2):5-9.
[4]谢洪恩,孙林,张世慧.论我国休闲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5,(06):188-193.
[5]庞睿.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逻辑建构[D].山东大学,2015.
[6]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2019,571.
[7]程虹著.宁静无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
[8]李娟.我的阿勒泰[M].花城出版社,2021,141,193.
[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商务印书馆,1989,46.
[10]潘立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6):5-11.
[11]吴育林.论马克思的劳动休闲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 (07):85-89.
[12]李娟.我的阿勒泰[M].花城出版社,2021,123.
[13]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06):1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