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舟《剔灯图》看全形拓入人物画的自我“在场性”论文
2024-12-26 11:23:02 来源: 作者:dingchenxi
摘要:“金石僧”六舟以拓片形式呈现古器物的形象,并与人物绘画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而其中《剔灯图》则是其最为典型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将人物画与青铜器全形拓拓本结合,还展现了六舟作为创作者和画面主人公双重身份的呈现。
摘要:“金石僧”六舟以拓片形式呈现古器物的形象,并与人物绘画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而其中《剔灯图》则是其最为典型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将人物画与青铜器全形拓拓本结合,还展现了六舟作为创作者和画面主人公双重身份的呈现。这种创作形式通过器物与人物尺度的转换,带给观者视觉上的新奇感;另一方面,它也展现了六舟对于自我表现意识的强烈追求。《剔灯图》中的人物绘画由陈庚完成,但六舟的角色不仅仅是拓工这么简单。从最初的画面构思,到人物表现方式,每一个创作过程六舟无不参与其中。观者在欣赏这件作品时,不管是观看拓本还是看画中主角所观看的对象都是六舟,无疑,六舟通过这种方式将他的“在场性”提到了最高。
关键词:六舟;《剔灯图》;主体意识;“在场性”
全形拓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形式,青铜器的全形拓技术出现在清代嘉道年间。相比以往平面化的青铜器传统拓片,全形拓通过传拓青铜器器形,创造出具有立体效果的器物形状。因此,全形拓又被称为“立体拓”。全形拓主要运用墨拓技术,结合绘稿、剪纸等方法,运用透视、墨色浓淡变化,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器物形体。在全形拓补绘画的图像考察研究中,首先,对于补绘图像,需要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以达到提升其艺术价值的目的;其次,当古物图像以独立拓片的形式存在时,它们往往因与补绘图像的结合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在保留古物的历史性的同时,赋予其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丰富对于全形拓补绘画的理解,并为绘画领域的艺术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
被阮元称作“金石僧”的释达受,即六舟,凭借其高超的全形拓技术在晚清享有盛誉。他将“金石墨拓入画”,即以拓片形式呈现古器物的形象,并与绘画相结合,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成古器物拓本补绘的创作形式,对晚清民初乃至后世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六舟的全形拓入画的作品中,有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是将相对写实的人物绘画与拓片相结合表现特定场景,传达纪事信息①[1]。这种创作方式不同于传统清供图中的图式,完全展现了六舟的创新能力,至今为止,没有其他人创作过这类作品。与古砖花供和钟鼎插花不同,这些作品中的器物并没有转化为瓶盎的形象,而是保持了其原有的属性和外貌。自从宋代金石学兴起开始,画作中常常将古代器物和人物共同进行描绘,而在明清时期更是广泛流行。许多卷轴画展现了古代和鉴古场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尚古潮流。六舟的作品与其他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全形拓这个新元素的运用使得画面中的古代器物具有了具体的指向性。更重要的是,在画面中,人物与真实器物的比例被完全颠倒,展现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但又保留了一种来自拓片和绘画共同营造的真实感。
对六舟而言,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三年的这段时间极为重要,期间创作了许多名作。当时,程木庵多次邀请他前往新安述古堂,传拓商周青铜彝器千余件以及宋元明三朝古墨二千多品②[2],可以说他是当时传拓领域的第一名手。其中最著名、也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雁足灯》以雁足造型为基础,灯盘背面刻有铭文,但由于铜锈的覆盖使文字变得模糊不清。六舟后对其进行了剔洗处理,使得铭文重新显露。在述古堂的几年间,他也曾将自己手拓的《雁足灯》拓片赠送给诸多好友,有少数的拓片上还有六舟亲自补绘的《六舟剔灯小像》,将自己剔洗雁足灯的场景绘制在拓片上,使原本普通的《雁足灯》拓片变成了具有创作性的艺术品《六舟剔灯图》。
“剔灯图”是六舟钟爱的一个题材,也是融合了全形拓补绘画与传统人物画的典型创作。目前,根据统计,可以找到三幅其全形拓补绘画作品:浙江省博物馆藏《剔灯图》、上海图书馆藏《剔灯图》(赠沈兆霖本)、2019年北京保利春拍《汉竟宁灯两画全形》③[3]。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剔灯图》长卷纵向尺寸为30.8厘米,横向尺寸为69.5厘米。画面右侧以隶书题“剔灯图”三字,并附六舟题跋;画心内容为两西汉竟宁雁足灯全形拓,绘有一僧人着素袍黄鞋于灯座之上,并用手触摸器物表面;画心左首为沈景修观款。对比画心中央的两个雁足灯全形拓片,可以发现它们都由灯座、灯柱和灯盘组成,但是在细节上由于视角的不同,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异。在右图中,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灯盘呈现内外两层环状相套的形式,雁足以三爪站立在灯座上。而左图则是自下而上的视角,灯座底面内凹且灯盘底部刻有铭文。此外,通过转折和遮挡关系以及透视处理,进一步展现出画面的空间特点。在拓印上,通过墨色的深浅来展现器物表面的高低差异,右图中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墨色浓淡和渐变的运用,通过灯盘的立面从中间到边沿颜色的逐渐加深,中心口沿自上而下渐淡的效果以及灯座雁足处爪尖至灯腿的渐淡效果都凸显了其空间感。绘制画心人物小像的过程首先采用了白描钩勒的技法,然后涂上色彩,整体面部处理颇似波臣派肖像画法④[4]。同时,画面的立体感还来源于拓印和绘画两种不同的传达方式的结合,尽管对人物的绘制相对直接,而器物拓印则采用了相对间接的转写方式,但在视觉呈现上二者却有相反的效果。人像的过分缩小于雁足灯的保留原大尺寸形成鲜明对比,因此雁足灯拓印给人一种更直接更真实的视觉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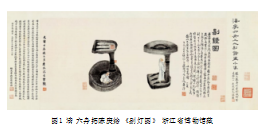
以这样戏剧性的手法进行处理不仅增加了器物的真实性,也对应了题跋中的“所谓芥子纳须弥,化身无量亿,未免孩儿气象矣”。须弥山被视为世界中心最高的山峰,而芥子,即为菜籽,只有芝麻的大小,将须弥山比作芥子那么小,以芝麻一般大小的芥子来容纳世界上最高的山须弥山,超越了大小的界限,阐明了世间万物无大小之区别之分。在《剔灯图》中,六舟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雁足灯中,并将雁足灯比作芥子,六舟则象征须弥山,不再强调现实世界中的大小之别,而是引导观者进入禅理和哲学的思考。
按照目前人物、山水和花鸟画分科,可见到“全形拓与人物画的结合”和“全形拓与花鸟画的结合”这两大类型⑤[5],而在全形拓入人物画这类作品中又以《剔灯图》和《六舟礼佛图卷》最著名。同样是以全形拓入画的纪事作品,《剔灯图》显得更为典型,一方面,相比《礼佛图》中造像形象上看似更接近现实世界比例的画面,《剔灯图》中运用的极度尺寸反转则呈现出一种荒诞戏谑的氛围,另外,在《剔灯图》中六舟更加注重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即六舟作为创作者在作品中的“在场性”。尽管创作者尽可能地还原了原器的尺寸与形制,然而最终呈现的仍是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画面,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后期的人物补绘,通过改变人像的大小将其与器物的比例进行颠倒,从而使得原本真实的全形拓似乎也随之改变了原本的大小。这样与人物绘画相结合,创作者成功地将个人形象和志趣融到对原器的“转译”⑥[3]中,成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中国绘画尤其是写意画强调“意象”,是作为绘画主体的“我”画“我”眼中和写“我”心中的世界⑦[5]。创作者所描绘的物象并不需要完全忠实地还原自然界的事物,他们可以对其进行加工和演绎,赋予其独特的内涵,与自然界的物象产生差异。对于艺术家来说,描绘内心情感要比模拟自然界物象更为重要。此外,对意象的强调还衍生出意造的概念,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作。例如,钟鼎彝器的整体形状原本是忠实于客观物象的描绘,然而当它与人物绘画结合时,却产生了奇妙的意象效果。在绘画中,将画面元素整合得协调美观就足够了,并不必追求细枝末节的准确性。这种强调意象的思维逻辑显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作品中,六舟或坐于雁足灯观摩铭文,或站立其上摩挲灯柱,这样的画面显然有违常理,是创作者自我意识下的构思与呈现。
自道光十五年任命苏州,六舟的视野也从海宁白马庙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随着与外界更多地接触和人际交往的增多,也让他对自我身份的认识有了新的思考。其中,他的全形拓技巧无疑是让他在文人士大夫圈子中脱颖而出、立足生存的法宝,然而六舟并不满足于仅仅在这个圈子中扮演一个“拓工”的角色⑧[1],他希望通过能够通过塑造学者和藏家的形象来正名自己。道光十六年是他意识到自身身份的重要时刻,也是他财务状况能够支持他学术抱负和藏家身份的时候。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如《六舟礼佛图》和《剔灯图》的纪事作品,二这些作品与他对身份建立的自觉性有一定的关系。
在画卷开头的题跋中,六舟记录了他在程木庵遇到雁足灯并进行拓印考释之情形,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窥见他作为一名禅悟之人对“芥子纳须弥”的参悟以及创作初衷。虽然作品是由六舟传拓,陈庚绘画而共同完成的,但六舟承担的角色远不止是拓工。
作为一种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形式,全形拓入人物画囊括了金石传拓和人物绘画创作两个领域。就创作主体而言,拓本博古画大多是金石学家、拓工与画家三者互动合作的产物,例如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吴大澂等人经常要就金石拓片的形制尺寸、画面构图等问题与拓工进行沟通。但是以上三方的配合并非“各司其职”,他们各自的“场域”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状态,因此就存在着主体身份转换的问题⑨[3]。当然,也有难得的既擅画又擅拓的金石学家的出现,能够独立完成博古画的创作。而在其中,拓工的地位较为特殊,他既是传拓活动的完成者,也是拓本博古画的创作者之一。从拓工的角度来看,传拓时一般能够确保器物的清晰完整和准确性即可,但是用于创造博古画的拓片必须依据金石学家的具体要求对画面进行适当调整,要考虑后期为画家或书家的作画与题字留出足够空间。虽然《剔灯图》是由六舟传拓,陈庚绘画而成,但补绘的人物小像显然是根据六舟的主张而得的,因为六舟本人在最初传拓之时就确定了整个画面的要素呈现,因此在创作时,陈庚更像是一个被委托的画工,而非能展现自我创作意识的创作者。而作为这件作品的构思设计者、全程参与者以及最终拥有者,无疑,六舟在作品中发挥了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最强的“在场性”。
注释:
①陈笛.从学术到艺术[D].中央美术学院,2020.
②仲威.六舟和尚与雁足灯[J].中国书法,2015,No.263(05):150-155.
③冯葳.全形拓补绘画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2.
④尉笑.全形拓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2.
⑤冯健.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J].西泠艺丛,2020,No.72(12).
⑥冯葳.全形拓补绘画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2.
⑦冯健.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J].西泠艺丛,2020,No.72(12).
⑧陈笛.从学术到艺术[D].中央美术学院,2020.
⑨冯葳.全形拓补绘画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2.
参考文献:
[1]陈笛.从学术到艺术[D].中央美术学院,2020.
[2]仲威.六舟和尚与雁足灯[J].中国书法,2015,No.263(05):150-155.
[3]冯葳.全形拓补绘画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2.
[4]尉笑.全形拓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2.
[5]冯健.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J].西泠艺丛,2020,No.7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