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的重构——论现代艺术中“光晕”的归置论文
2024-11-28 11:06:18 来源: 作者:dingchenxi
摘要: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可复制性一直是其特有的属性之一。木刻、镌刻、石印等传统复制技术的出现,不断拓宽着艺术创作与艺术传播的新路径。19世纪下半叶,一种全新的复制技术——摄影术横空出世,它与传统复制方式截然不同。
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可复制性一直是其特有的属性之一。木刻、镌刻、石印等传统复制技术的出现,不断拓宽着艺术创作与艺术传播的新路径。19世纪下半叶,一种全新的复制技术——摄影术横空出世,它与传统复制方式截然不同。传统的复制技术都是基于原作来进行复制的,原作与复制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先后顺序和依赖关系,复制品属于原作的一部分。而摄影术中没有所谓的原作一说,即基于摄影术的复制活动如细胞分裂一般,原作与复制品一模一样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在摄影术中,原作与复制品表现出了平等却又对立的关系。

一、技术复制时代:“光晕”的渐熄
原作概念的丢失基于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技术复制时代对艺术的影响是以艺术的宗教膜拜特性的转变为先决条件的。如果说宗教的目的是延伸巫术价值,那么可以说,原始社会中以巫术为起始的艺术自诞生之初便与生俱来地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距离”导致了原始艺术与人的分裂,也间接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距。自艺术诞生之时起,艺术的解释权与创作权就一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也因此使“距离”、分裂以及地位差距三者形成了一个闭环。
回望西方宗教统治时期,宗教艺术作品是以艺术为手段进行宗教传播的一种工具,强调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从艺术作品自身来看,可展览性是艺术作品的特有属性之一,宗教膜拜属性的体现是建立在可展览性之上的,两者的最终目的区别了两者艺术作品的根本价值。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时代因素——技术复制时代,则是膜拜性与可展览性相互转化或走向两极的催化剂。
艺术的可复制性趋势是一个不断追求“近似”的过程,而技术复制时代则改变了追求“近似”过程的性质,转变为对艺术复制的解放。但在复制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艺术品的“原真性”也在逐步丧失。技术复制品对原作的远离,使其不再受原作因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改变的物理结构以及占有关系的限制,最终侵犯了原作的权威。复制过程中所丧失的东西被本雅明用“光晕”这一概念进行概括。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被大量复制品替代,促使观赏方式、观赏角度也发生着巨大改变,这一系列的影响皆归因于技术复制过程中“光晕”的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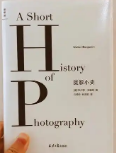
“光晕”一词最早出现于本雅明的《摄影小史》中。文中,他将“光晕”解释为“时间、空间的奇异交织。远方的奇异景象仿佛近在眼前”。后来,本雅明又以自然之物的若即若离来比喻与复制艺术作品相比,原作“光晕”的一定距离的独一无二的显现,肯定了“光晕”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存在。复制品消除了艺术作品与大众间的距离感,使附属于“膜拜价值”的艺术作品被解放出来。着眼于可复制的艺术作品的复制艺术作品,将原作的“原真性”荡涤一空。这使得艺术作品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发生断裂。该断裂一是指艺术创作过程中时间的断层,二是指表演方式与观览角度的割裂,三是指艺术作品历史性的中断。“光晕”所展现出来的“此地此刻性”的特点皆是基于历史的演变过程,是历史不断“赋魅”的结果。复制技术的进步解放了艺术自身的自由,却导致了历史与艺术的断裂。
从历史维度上来看,“光晕”概念的提出是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艺术演变的象征,既能展现出科技发展的蓬勃力量,又表达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对人性丧失的担忧,其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鲜明对比关系的映射。作为社会理性化的牺牲品,艺术作品“光晕”的丧失是一种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复制技术促成的艺术作品“光晕”的丧失是社会“祛魅”的合理工具,是突破传统观念牢笼的有力武器。但另一方面,艺术作品与大众间所产生的“光晕”以及所营造出的精神空间,反而是一个无限接近于人性的“乌托邦”,是快速发展的工业进程中的感性王国。艺术作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既是艺术对人们思想发起冲击的助跑跑道,也是人们精神的缓冲地带,其成为“光晕”在现代艺术中再现的必要条件。
二、现代艺术:“理念”创造的艺术化符号
艺术的演变与发展深受创作手段、展览方式、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将创造理念无限放大的过程。自印象派以来,现代艺术便自带一种“革命”的气质。单论“传统艺术”的角色转换,各个风格、主义、流派都是在矛盾、创新、挑战后登上主流舞台的,后又被冠以“传统艺术”的名号重回历史。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异化过程,既代表着大众个体审美意识的不断觉醒,又是大众艺术自律观念的体现。
现代艺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众多场外因素共同推动而成的。例如摄影技术的诞生改变了以往西方绘画对“近似”的追求,转变了西方绘画“复制”的任务,成为其由具象到抽象演变的推手之一。对现代艺术的文字说明与预先设定加速了其实现自身合法性的论证,现代艺术虽来源于经验社会,却在创作之初便表现出对经验社会的抗拒,正如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言,现代思想与艺术之所以会很难懂、会与尝试截然相悖是因为它真的关心和追求真理;是因为经验已经不允许它再抱守着常识所持的那些清晰简单的观点了——常识之所以所持守这些观点,通常无非是为了求个心安。因而现代艺术形成了一种与之相分离的局面,并用一种复杂且广泛的非艺术的艺术化符号体现出来。
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区别在于创作方式、创作目的和创作理念的不同,而不在于艺术语言的运用。传统艺术不断追求“可视化”,而现代艺术则是经由“理念”创造后的显现。与传统艺术相比,“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一场玩笑的艺术片段,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因为这正是现代灵感的滑稽性质所要表达的东西。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戏剧,它要嘲弄的正是艺术本身”。对艺术本身的嘲弄所反映出的是现代艺术对原有传统艺术的程式化的讽刺(尽管两者的角色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其中也夹杂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艺术家个人思想的映射,由理念形成的艺术化符号正是嘲弄的工具,例如杜尚的“小便池”或劳申伯格的“山羊”。通过将非艺术的符号艺术化,现代艺术与大众、社会甚至与传统艺术之间皆形成了一层显而易见的隔离网,避免了其自身受到大众诠释的腐蚀、社会异化的蚕食以及传统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兼并。
“理念”所创造出的艺术化符号不仅指非艺术的艺术化符号,还指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进行艺术化符号的加工,是运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对传统艺术形式所进行的发现、批评、再利用和创新,这个过程可以被视为传统艺术自身异化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被视为催生出现代艺术的起点之一。从当今语境来看,现代艺术的发展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类似于先前艺术革新与演变的历程,也不再是社会发展进程的附属品。现代艺术之所以体现出一种基于艺术自律的观念,源于其对纯形式化美学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造成现代艺术难以融入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现代艺术表面体现出一种“无序”状态,但实际上,这种“无序”恰恰反映了一种“有序”的发展规律。这是因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复杂的社会状况、历史情况以及艺术内部对形式美学的探索和对于阐释的矛盾态度——既拒绝被简单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迫进行自我阐释。这种多元的影响和内在的张力共同塑造了现代艺术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发展轨迹。
三、场域中的“梦境”:“光晕”的重燃
复制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艺术作品“光晕”的熄灭,原作在复制艺术作品中变得失去了意义。然而,当我们以现代的视角来审视艺术的发展轨迹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可复制的还是不可复制的现代艺术作品,它们对于原作的界定都逐渐变得模糊,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的“光晕”却在“场域”的烘托与“艺术导语”的包装中重燃。
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并且每个小世界皆是具有自身主体逻辑与客观关系的双重特性的空间。因此,场域的构建不仅为合理分解现代艺术价值与意义提供了一种方法,还是重燃现代艺术“光晕”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是场域中的艺术语言构成了艺术作品,尤其是现代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推动现代艺术朝着更注重“理念”表达的方向转化,从而稳固了其艺术地位。二是场域分散了构成艺术品价值和意义的生产主体,将艺术作品从艺术家的创作中解救了出来,使其艺术价值由“所有与艺术关系密切的人,包括为艺术而生存的人,被迫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艺术而生存的人,彼此面对着斗争的人,还有通过这些斗争参与了艺术家价值和艺术价值生产的人”所赋予。三是场域构建本身的相对封闭性赋予了现代艺术自律的特征,即现代艺术的自律是在场域的他律性框架下进行的,因此一些诸如沃霍尔的《布里尔包装盒》或克莱因的单色画这样的作品才获得自己的形式特征和价值。
对于现代艺术来说,场域所构建的是一个脱离经验社会的“梦境”,在这个乌托邦中,即使是在可复制的条件下,现代艺术的“光晕”也依旧会重燃。现代艺术注重创造方式,与复制技术并不冲突,两者的结合是以艺术场域的构建为基础的,离开艺术场域的现代艺术复制品,甚至是现代艺术作品都会丧失其艺术价值。艺术场域的相对封闭会导致大众与现代艺术之间存在天然的“距离”,而现代艺术冲破可复制对“光晕”的影响,则体现在现代艺术要求“复制品”在场域中的“在场”。同时,由于现代艺术对“在场”的要求,其侧重点也由原先艺术作品“一种只看重艺术品的膜拜价值,另一种则只看重其展览价值”转变为对商业价值和政治价值的追捧。
现代艺术“光晕”的重燃还体现在对可复制技术的约束上。对存在于艺术场域的现代艺术来说,技术越易于被复制的艺术作品,反而越难实现完整复制。以现成品艺术作品为例,复制一个相同的小便池或是拼接一只山羊并非难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打造一个恰当的讨论语境,如何构建一个合适的展览环境,以及如何创造出一个能让观众与作品产生最佳互动体验的合适“距离”。现代艺术产生并依赖于艺术场域,这一特性使其复制属性磨灭了原作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复制品的正统地位及其在场域演绎下对原作和“光晕”的继承。从“光晕”的角度来看,这种继承证明了现代艺术与艺术场域正逐步走向自主性,因为继承的发生体现了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两者的身份获得了合法性——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现代的拥趸。然而,这种继承也可能被视为对“光晕”原初概念的偏离。原本,“光晕”是对技术理性与经济理性侵蚀生活意义的担忧,但如今,这种担忧却似乎被现代艺术和艺术场域当作扩展自身影响和互利共赢的工具。因此,继承“光晕”成了它们当前共同的经营特色。
震惊体验是现代人丧失“光晕”后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其瓦解了人们熟知的经验,导致作为传统经验概念的记忆与现代生活中不断产生的刺激或震惊的激增相对立,最终对大众的主体完整性构成威胁。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把震惊经验置于其艺术作品的中心以此来规避震惊”是重回艺术自律的最初尝试。场域所营造出的“梦境”使现代艺术能在复制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中仍然保持自身的“光晕”,就如同使用着波德莱尔似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对艺术作品“膜拜价值”追捧的时代,并借助光怪陆离的艺术之光带领大众重寻被震惊碎裂掉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