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中国画中的重屏画图式论文
2024-09-07 16:09:18 来源: 作者:liziwei
摘要:
屏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室内家具,是古人表达艺术精神、追求功能与装饰和谐统一的重要载体。五代、唐宋时期,屏风便已经开始在传统绘画中活跃起来,由于文人的喜爱,它们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元明清时期,屏风不仅成为画家们的重要构图要素,而且也成了一种多样化的绘画符号,使得图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其中,重屏元素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普通构图模式,并被画家赋予了不一样的艺术风格和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本文主要讨论“重屏”在画面空间结构上的作用、与古代文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对画面意境的烘托这几个方面,并以传统人物画为例从画面出发进行分析讨论,探寻重屏元素在画面中的作用及艺术效果。
在所有关于传统绘画中的屏风元素的研究中,涉及重屏画的部分少之又少。这里选择重屏画进行研究,是因为重屏图示案例特殊且典型,虽然现存的传统重屏画并不多,但其在传统中国画中的特殊性与精彩呈现值得仔细探究。除了屏画本身,本文还联系时代背景、画者风格等,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的文人风采与社会风气。
一、传统重屏画初探
目前对于“重屏”这一概念,并没有准确的定义。更多的研究者对重屏的理解都基于巫鸿先生的《重屏》一书。所谓重屏,笔者将其理解为多层空间中的纵深的屏。下面,本文将以《重屏会棋图》《消夏图》《是一是二图》和《历代画幅集册》(第一幅)这几幅绘有屏风元素的画作为依据,从空间构造、屏画内外联系以及屏风挂像画三个方面逐一讨论传统重屏画,探索其中奥妙所在。重屏之所以与众不同,深受大众关注和喜爱,是因为其画面的空间结构特殊,表达的主题内容更有深意,容易引发观者更深入的思考。
重屏图示的首创者是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他凭借出色的技艺,将南唐时期的李璟与其三个兄弟对弈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了独具匠心的《重屏绘棋图》。这幅作品表面上看记录的是帝王游艺的场景,实则有着更深刻的内涵与目的。这幅画现存的是后人的摹本,其中一幅摹本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另一幅藏于故宫博物院,原作在南宋之后已经失传。
五代南唐时期,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尤爱文艺,在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下,南唐的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其中,周文矩、顾闳中等技艺精湛的宫廷画家尤其善画人物,李璟和李煜还常常召集绘画高手给君臣贵族作画,记录他们的宴饮赋诗等活动,这幅《重屏会棋图》(如图1)描绘的则是帝王与兄弟间的对弈。

画面中重屏的构图形式将画面分成了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就是画面的最前方,即李璟和三个弟弟会棋的场景。棋盘上的棋子呈现出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形状,因此可以推断出第一画面中东南西北的方位。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是东方,而古时又以东方和左边方位最为尊贵,那么画面中李璟所坐的位置就是东面。与李璟并排坐在东边的是太北晋王景遂,棋盘的西南方向和东南方向依次是齐王景达和江王景逿。四人根据东边和左边的坐法,将权力与地位分化也代入了画面中。
第二空间是画家根据白居易所写的一首题为《偶眠》的诗创作出的体现暮年诗人日常起居的生活场景(如图2)。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南唐中主李璟虽然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政策,但他却没能把握住机会,以致南唐最终陷入灭亡的边缘。尽管如此,李璟依然沉迷于文艺活动,忽视了许多本应被重视的事情,使得南唐的衰落变得更加迅速。李璟深知自己沉溺于下棋的嗜好,深深地懊悔,却无力抑制自己的欲望。这幅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可以抚慰李璟的心灵,同时也提醒他要把握好下棋的尺度,切勿因此误事。

此画也有另一种更具政治色彩的解释:在藩镇割据的年代,李璟因争权夺利弑兄的惨剧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的儿子们年纪尚小,但弟弟们的势力却日益强大,为了防止兄弟密谋造反,李璟对外宣称自己死后要将皇位传给弟弟,而不是自己的亲儿子,于是有了《重屏会棋图》中描绘的兄弟四人聚在一起下棋的场景。
二、《消夏图》中的重屏图式研究
同样运用了重屏构图形式的还有元代画家刘贯道所作的《消夏图》,其画面似乎强调的是园林中宁静安逸的退隐生活,主人公身后的屏风上画的则是他在书斋中办理日常公事的场景。有意思的是,《重屏会棋图》中的程式在《消夏图》中被完全倒转:周文矩在屏风上画的室内私人生活在《消夏图》中变成了画中的“现实”;而对士大夫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却变成了屏中画,成为远离观者的暗示性表现。
刘贯道的这幅《消夏图》(如图3)描绘了种有竹子和芭蕉的私家园林。画面中心,一位身着道服却袒胸露乳的士大夫闲适地躺在凉榻上,他背依隐囊,眉头微蹙,若有所思。他左手拿着卷轴,右手持着拂尘,而这两件东西都是文人隐士的传统象征物。隐囊后有一把阮咸,左侧矮桌上物件繁多:一卷竹简、一座古钟,还有各类文玩清供、茶茗器具等。两位女子站在画面的右侧,一位拿着一把山水长扇,另一位则拿着一个包袱,两人似乎正在一边交谈一边朝左走去。主人公的目光被安排在两个女子身后,而他的脸部微微上扬,将观者的注意力引向第二个画面,即榻后的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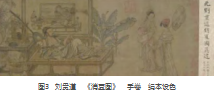
屏风中的主人公又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书斋中的士大夫。他坐在床榻上,一旁的矮桌上摆着为他准备的笔墨纸砚。他身边的小童子奉香而立,而画面左侧的两位小童正在奉茶,前面那位身体前倾,将观者的视线引向第三画面——士大夫身后的一扇山水屏风。屏风上画着一幅山水画,右边近处是高山怪石险峻,树木繁茂,其间一条山路依稀可辨,道路尽头山石掩映处一座古刹隐约可见。
在第一画面中,这些看似超然洒脱的设计却在主人公眉宇间的一丝愁容中显得别有深意。这样的反转究竟有何深意呢?当我们将这幅画放到元代的时代背景下揣摩时,似乎就有了新的答案。元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元朝从建立到灭亡的九十多年间,汉族人始终是被歧视、被统治的,而选择隐逸或者另谋出路成了大部分人的无奈之举。这样看来,画家对主人公表情的描绘是有据可循的。
三、主人公与屏风挂像画
除了上文提到的重屏图示,还有一种特殊的“画中画”构图——挂像画。这种模式使画面中更吸引观者的不再是画面中心坐着的主人公,而是出现在他上方的挂轴肖像画。收录在历代画幅集册中的著名人物画(如图4),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藏印来看,是宋代的杰作。

这幅画整体画面和谐统一,所有的器具包括矮榻、座屏、放着书籍卷轴和古琴的桌子、摆放着酒器和砚台的桌子、圆凳、插花瓷瓶,还有莲花造型的香炉等,都是宋代书斋内经常出现的。画面中心的高士盘腿坐在矮榻上,右手执笔,左手持纸张,双目含笑,看着面前正在倒酒的童子,而童子姿势恭顺,显得他格外和蔼可亲。屏风上画的并不是浩然广阔的山水,而是以花鸟为饰的芦苇沼泽,显得更为清雅。而画面中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高士身后画屏上挂着的肖像画。
不难看出这幅肖像描绘的正是这位高士本人,衣着和头饰均未改变,只是面朝的方向相反。值得琢磨的是,画像中的高士并不像“现实”中的他那样面色温和,而是表情严肃,似乎正自上而下审视着屏风前的自己。这样的设计给观者留出了想象的空间。
作为这张高士图的收藏者,乾隆亦有同样的屏风挂像画,名为《是一是二图》(如图5)。从表面上看,其与历代画幅集册中的人物画极其相似:乾隆皇帝坐在榻上,右手执笔,左手拿纸,身后一架山水屏风,屏风上同样挂着皇帝本人的画像。但不同的是,《是一是二图》中的家具摆设更加精致华美,甚有西式风格,这从侧面体现了乾隆本人的审美趣味,也符合他的身份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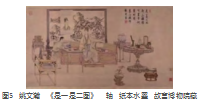
没有了空间的纵深感,这张小小的肖像画也同样给观者以无限的想象。屏风挂像画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屏图示的构图,但这种特殊形式的“画中画”,特别是挂在屏风上的肖像画,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屏。
历代画家利用屏风作为家具的特殊性,把它当作绘画创作的素材,在屏风上绘制山水、人物以及花鸟等,使屏风的艺术价值得到空前增长。在绘画中,画家根据不同时间、人物和心境,创作出含有不同艺术效果的重屏画。画家不仅描绘了屏风的内容,还传达了当时的心境,营造出了不一样的意境。当屏风成为画家描绘的对象并出现在绘画中时,画中屏风存在的意义已经远超过了屏风在生活中所起到的遮蔽、分隔、欣赏等实用性的作用。作为观者,我们必须给予它理性分析,并传递其所对应的文化内涵。
在本文中,笔者进一步分析了《重屏会棋图》、《消夏图》、《历代画幅集册》(第一幅)、《是一是二图》这几幅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及其他以屏风为绘画题材的作品画面的深层内涵。本文对画中屏风的时代背景、画中的屏风与人物的关系、画中屏风的空间构造以及它们要传递的寓意与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说,屏风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古代绘画中借屏风展示的人物内心世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屏风同样也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本文讨论的重屏图示以及画面中的山水屏风与道家物我合一的精神理念不谋而合。屏风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人雅士们展示审美品味的绝佳之选。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绘画中为数不多的重屏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需要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