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岂是蓬蒿人:镜像阶段理论视域下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的主体性建构论文
2024-07-19 10:07:54 来源: 作者:zhouxiaoyi
摘要: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作为精神分析学乃至于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近来被广泛应用于电影文本的评析当中。以镜像阶段理论为抓手,学者可深入挖掘个体在进行自我构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特征。电影的立体化角色谱系塑造需要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转变,镜像阶段理论在电影中的合理运用可以使得剧作方向与人物刻画更有迹可循。文章以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的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与后镜像阶段为框架,通过分析电影《年会不能停》中的主体性建构过程,尝试分析影片主体如何历经自我建构的不同阶段成长为真正独立的社会个体,并总结出主体完善的必由之路。
摘要: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作为精神分析学乃至于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近来被广泛应用于电影文本的评析当中。以镜像阶段理论为抓手,学者可深入挖掘个体在进行自我构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特征。电影的立体化角色谱系塑造需要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转变,镜像阶段理论在电影中的合理运用可以使得剧作方向与人物刻画更有迹可循。文章以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的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与后镜像阶段为框架,通过分析电影《年会不能停》中的主体性建构过程,尝试分析影片主体如何历经自我建构的不同阶段成长为真正独立的社会个体,并总结出主体完善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镜像阶段;《年会不能停》;主体性建构
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的影片《年会不能停》自上映便获得大量观众好评,截至目前获票房12.46亿,实现了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本片以高级钳工胡建林的视角深入现代职场的复杂生态,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展现了当下打工群体的人性挣扎,值得注意的是,由马杰高喊而出的“蓬蒿人”意象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它代表着在职场权力体制架构下被他者认同所钳制的打工人形象。文本中的职场主体可分为远离都市工作环境的“未见蓬蒿人”、身处现代职场人忍气吞声的“甘当蓬蒿人”以及最后掀桌对抗权势的“岂是蓬蒿人”三种,其心理状态恰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的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与后镜像阶段相契合。本文以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为抓手,解读影片角色谱系的主体性建构过程,试图探讨对现代打工人群体主体性构建的心理图示,并为其自我完善拓展新思路。
一、未见蓬蒿人:集体主义与半乌托邦滋养实在本我
拉康认为前镜像阶段是人类主体性构建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体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来自外在的刺激,并且刺激也是片段性质、非连续的,但是主体在其中第一次对世界产生某种感知,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完善自身。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中,90年代末的标准件厂在董事长的保护之下形成一个类乌托邦结构,将现代社会各种规则与潜台词这种大他者隔绝在外,于是胡建林及标准件厂的员工就成为当时万千普通工人的缩影: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以标准件厂为基准,同时对于自己的现状完全认可。整体来看,此时标准件厂中的职场主体正处于一种自我缺失态,其对职场的认知局限于标准件厂的一团和气之中,众和畸形职场环境普遍存在的“蓬蒿人”在这个充满集体主义氛围的半乌托邦之中仍是胚胎状态,身在其中的员工对于都市、职场机器运行规则、复杂人情都是不足、匮乏甚至混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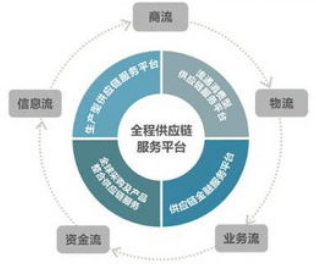
这类“他者”的不在场所促成的自我意识缺失,在文本中有几个突出表征。首先表现为众和标准件厂的员工们以群体利益为先,会自发布置年会场景,出手修理停摆的灯球,朴素的击鼓传花游戏都能赢得满堂喝彩,现代社会规则这个“他者”的缺位让胡建林所处的标准件厂没有众和职场的倾轧人性、利益勾结、内卷横行,众人本着最朴素的价值观在这个巨大的乌托邦中形成了亲如家人的关系,“师徒”的代际传承仍在进行,这种教授方式消解了人与人间的隔膜。其次具体到胡建林的形象,身处天然具有隔离性与朴素性的工作环境中,作为其中的典型员工他所接收到的刺激都是集体主义、团队为先的,因此他与徒弟们的关系是平等而和睦、没有上下级之分,他以兢兢业业并以严谨态度对待生产,在工作中受众人爱戴,因此被调往公司总部也让众人心服口服。
值得一提的是,“他者”的缺位与董事长对标准件厂的保护是分不开的。由于出身标准件厂的董事长对于厂子的支撑与默许,工厂内的职场主体被放置在远离约定俗成职场恶习的桃花源之中。鼓励劳动的时代背景与他者缺席的工作环境塑造了勤恳团结的工人形象,并形成了较强的认同感。这个类乌托邦结构的搭建伴生着较强的群体凝聚力,但同时自发地吸引着“他者”,预示着即将有一个他者的登场,即使这个他者将以冷酷的、如机器运行的态度闯入。
二、甘当蓬蒿人:畸形氛围与偏颇认同异化镜中客我
镜像阶段理论中的第二阶段称为镜像阶段。这一阶段中主体自身感知能力的碎片化仍待解决,然而想象中的控制能力已经超出了主体实际的能力,导致镜中影像最终占据主体地位。应用到自我认知的搭建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他者”的眼光与评价会潜移默化于个体自我的塑造,进而表现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上,成为被“异化”的客我。最初的他者是镜中影像,逐渐演变为原生家庭、社会因素、电影人物等因素。拉康将“他者”概念划分为“小他者”与“大他者”。“小他者”“是自我的某种映射或投射,它同时也是相似者与镜像”[1];对“大他者”来说,“‘大他者’则指代根本的相异性,无法因为认同而被同化,被铭写在象征界的秩序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大他者即象征界”[2]。当胡建林误打误撞进入公司并接连升迁后,物欲至上的公司氛围以及周边同事的殷勤奉承使他看到了成功人士这一理想自我,欣然认同渴望实现阶级跨越走向巅峰人生。其他职场主体已经或早或晚地对社会成功人士达成认同[3],于是在物欲的牵引下屈从于职场潜规则,甘愿成为“蓬蒿人”,而这也是引起当代打工人普遍产生共鸣的困境。
(一)大他者:畸形风气对主体的异化
“大他者”在文本中主要呈现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逼仄社会环境与畸形职场规则,具体显影于众和的等级差距、拜物倾向、糊弄上级指责下级、员工打工领导领赏等乱象。这一“大他者”对主体的异化则是根本性的、高强度、不可逆的——当胡建林首次去集团总部报道时,他昂首迈出旅馆走入高楼林立的城市,低矮混乱的城中村楼房与井然矗立的城市建筑形成鲜明对比。这幅景深画面看似表达着城市对城镇的、现代对过去的侵蚀,实际上暗示着逼仄的生存业态、冷漠的利益纠纷、沉闷的工作氛围对朴素人性的侵蚀与异化。当胡建林抖擞衣衫踏入其中,这种异化就潜移默化地开始了[4]。对于另一重要角色庄正直来说,他是大他者,即象征界投掷在代表着想象界的半乌托邦中的锚点。他较早地受到了大他者的影响,在影片中,身为供销科科长的庄正直将自己厂子生产出的优良品与其他代工厂产出的残次品交换,以此为领导杰弗瑞谋私以求进入总公司,为自己的儿子进入重点高中打基础。在这个隔离性较强的标准件厂,他最先感知到了社会的更迭并受到现代职场运行潜规则这个“大他者”的异化。逐渐与本我疏离的庄正直在这种颠倒错位中逐渐扭曲,成为领导以权谋私的工具。由此可见,庄正直工作调动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故事的错位,他受大他者挟持所造成的异化也是胡建林异化的开端。
影片也详尽刻画了已经被制度化的中层与打工人群像。浅层方面来讲,这种群体异化表现在身份的转变上。“优化”一词在电影中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广进计划大规模裁员行为,也更代表着不容抵抗的、手段剧烈的、来自他者的异化。无论是众和工作数十年薪资优渥的白领还是标准件厂兢兢业业的员工,在一个个完全相同的、逼仄的谈话间转变为歇斯底里的下岗待业工人。众人无可避免地被展露在大他者面前,只能原地承受社会机器与时代辙迹对个体的异化;深层方面来看,这种异化更是心理及行为逻辑的改变。电影中的“被制度化”即“异化”,代表的是人们在进入职场之后对自愿加班、007等不合理工作方式心存不满,却不得不为了保住工作而接受,甚至逐渐为了留在公司不择手段,与先前的行为模式大相径庭了。
(二)小他者:偏颇追捧对主体的异化
影片中的小他者是相似群体的镜像投射,但却有许多实际指代,比如老实耿直的胡建林,叛逆率真的潘怡然,纸醉金迷的皮特等。在接受异化、构建起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他们作为小他者也在不断异化其他主体。
首当其冲受到这种异化的是胡建林——胡建林婚姻失败、工作多年仍在底层,其内心也渴望成就一番未来图景。进入公司之后,他从白领、中层这些小他者身上看到了理想的自我,虚幻的掌握权柄、掌控他人的权利感获取虽然来自他人对其阴差阳错的误解进而造成的追捧与示好[5],但仍是其对当代职场产生充分认同,直接导致了他行为逻辑的官僚化,以及与本我的疏离。
文本中受小他者异化最严重的角色当为马杰。进入职场以来,马哲奉行的工作观念是领导交代我执行,本人干活上级领赏。逼仄的职场环境大他者搭建起严格的尊卑体系,而马杰就在其中扮演着阿谀领导的“狗腿子”角色,虽然仍未接触到公司的核心权力架构,但其作为组长已经拥有一定权力。然而随着小他者胡建林的含糊入场,马杰将其误认为领导的关系户,薪资给予优待,工作全权包揽。这种上级对下级承迎卖笑的做法完全颠覆之前的职场秩序,由职场环境大他者决定的小他者使马杰遭受了程度更深、影响更恶劣的异化。从胡建林和马杰的双向异化中可以看出,裹挟主体的他者无时无刻不在影响镜中成像,虽然其消极与积极并不由本身无实质的镜像决定,对主体构建起主要作用的仍是他者。但在裁员的大背景以及众多小他者的合力作用下,被迫“擦屁股”的马杰成了影片中受异化程度最深的角色。影片中构成镜中我的质素以及入场的大他者,即众和逼仄的职场风气与工作氛围是消极的,因此在文本中的他者异化多给主体带来反面影响。
三、岂是蓬蒿人:朴素良知与认同角力构筑真实自我
在后镜像阶段,随着主体身心机能的日益发育完善,其注意力便会从对于虚假镜像的认同回归到周围环境当中,认知到自己是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存在的。在故事结局段落具体表现为胡建林等人自我朴素良知与正义认同的觉解。为了摆脱镜像的桎梏,不做随波逐流丧失自我的“蓬蒿人”,他们不断为之奔走以求证明清白,最终在年会节目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完成主体意识的搭构。
对于胡建林来说,实在本我中的道德良知推动着他对抗他者,弥补被异化了的客我所犯下的签署关闭工厂的过错。又因为这种被体制化是非自然的、远离人情的,所以对苦难视而不见的他者们所催生的、异化了的客我也产生了一种向心力,鞭策促使着主体进行自我的重构[6]。他在电影中,意识到自己在醉酒状态下签署了关停标准件厂的胡建林面对前来质问的工友们真诚认错,并带领自己的徒弟以及马杰克等前往调查零件高误差率的真相,顺藤摸瓜发现公司副总阴谋,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顺应职场糊弄学、敷衍朋友的自己是被他者所塑造的,因此要主动与此镜像剥离,进行自我重构。至此,他真正实现了与大小他者的分离,完成了对于自我主体意识的搭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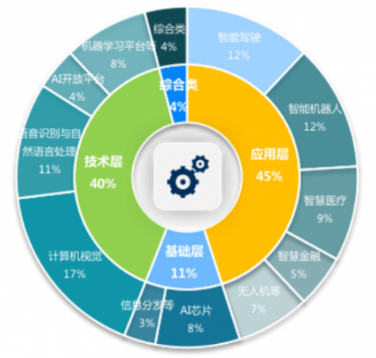
如果说胡建林在片中身处找寻自我意识的过程,那么与之相对的,潘怡然则是始终保有自我意识的显影。她作为众和外包员工展现出的“欠服从性”使其既处于在巨大异化语境中,又是游离者。但是这个游离也并非完全的,她在对抗他者构建自我的过程中仍然因为他者的塑造丢失了部分实在的本我。作为拥有音乐梦想与演唱实力的个体,她放弃了初心,选择进入众和,接受社会职场规则大他者的异化。即便如此,她依旧是全员异化中显著的对抗性符号,是片中始终试图以自我抗衡他者凝视的主体形象。我们可以认为,潘怡然强对抗性、高叛逆度的自我是早于情节矛盾爆发之前,就已经被搭建完成了的。这也促使着她成为胡建林与马杰对抗他者异化,找寻真实自我的助推剂。
马杰在影片中是一个被动且甘心接受社会塑造的小人物形象。如果没有胡建林作为小他者催生其异化,他将难以明确自我与他者的对抗关系。在影片中,马杰一出场便被缔造为懂得察言观色、处事圆滑且深谙职场规则的老打工人形象。对于早已被现代职场大他者异化了的马杰来说,谨小慎微是座右铭,领导心思乃真道理。习惯于在逼仄的职场生态中挣扎的马杰忽然遇到一个横冲直撞、笨拙却鲜活的胡建林,他心中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逐渐开始壮大。“小他者”胡建林让他感到久违的职场中温暖的同事情谊,也逐渐唤起了理想主义的本我。经由了与胡建林、潘怡然共同经历的一系列误会与磨合后,马杰最终爆发了“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声宣言,加入胡建林揭穿副总阴谋的行列中。因此,马杰的自我重构与回归才是本片中最为可喜的一点,也是本片诱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关键之一。因为主角胡建林只是剧作模型愚者成功的特异案例,而马杰才是广大打工人群体的缩影。
四、结语
我们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可以看出,个体的自我是在他者的塑造之下进一步完善,并最终建构起来的,来自他者的异化只是自我完善发展途中必经的站点。“我们可以用笑声对抗恐惧。”[7]这是导演董润年在采访中表达的观念,本文的重心亦是尝试在对抗中寻找和解。此刻的认同幻灭之后,主体又会期待下次理想化的认同,其所参与的想象与现实的角力与辩证就这样不断地在人类的生活里循环,我们的主体性也由此不断形成完善。[8]通过探析影片主体性构建的过程可知,当代打工人群体如果想获得社会秩序的认可,未必需要拜服于不成文的、违反人情道德的社会潜规则。纵观《年会不能停》的角色塑造,我们最终观照到觉醒了劳动者主体意识、重拾本真、自立自强的讨喜形象。这昭示着广大劳动者反抗畸形异化、回归自身本我、构建自我主体性的可能,也鼓舞着大众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迪伦·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M]李新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6,第257页.
[2]迪伦·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M]李新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6,第258页.
[3]龙丹.主体与镜像的辩证关系——镜像认同的三种样态[J].外国文学,2018(01):109-117.
[4]陈林侠.此欲望,非彼欲望——齐泽克的欲望理论及其电影批评反思.文艺研究[J]第8期,2020.
[5]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3-184.
[6]迪伦·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M]李新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6.
[7]黑白文娱.我们可以用笑声对抗恐惧|黑白文娱专访《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EB/OL],2024.
[8]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