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笔下的人物群像论文
2024-06-01 11:57:53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本我”“自我”“超我”角度来看人物背后的精神世界。同时,具有极强“本我”意识的人物存在反英雄特质,这种反英雄特质致使人物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悲剧道路,但闪耀着为数不多的人性浪漫。
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本我”“自我”“超我”角度来看人物背后的精神世界。同时,具有极强“本我”意识的人物存在反英雄特质,这种反英雄特质致使人物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悲剧道路,但闪耀着为数不多的人性浪漫。
双雪涛是一位新生代作家,他的作品题材众多,风格独特,从魔幻到青春伤痛,从悬疑到现实,各种创作风格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从2010年发表《翅鬼》开始,已有多部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双雪涛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极强的“本我”意识,使之抽离日常生活而活出了与传统道德、“理想自我”相悖的人生。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双雪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以此挖掘人物性格背后的精神世界,探究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与物之间的冲突,以及带来的精神困境。
遗世独立:偏执的“疯子”
双雪涛的小说惯用冷峭犀利的笔锋、近乎冷血的纪实性口吻叙述故事,就连他的幽默都是冷冰冰的。也正是这种冷静的客观描述,塑造了一系列不融于社会群体的人物群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分析到,人格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层次构成的,三者处于相互制衡状态时,表现为正常或平凡人;但当三者失衡后,主体便会失去健全的人格。从整体上来看,双雪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在“本我”驱使下,“自我”的存在显得渺小,“超我”中的“良知”就不存在了,社会道德对个人的惩罚与规范的作用显得渺小。但由于现实的束缚与制约,最终人物在“本我”与“超我”的撕扯下,走上悲剧的道路。
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就有这种鲜明的表现,“我”第一次见到“安德烈”的时候,是初一的第一堂课,他穿着像女人套裙似的跨栏背心,拒绝父亲起的“安德舜”名字,而给自己改成“安德烈”,和老师“据理力争”,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成了老师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当老师生气地问“‘听明白了吗?’,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的时候,安德烈也只是摇摇头。从一开始,到后来在历史课上质疑人类的起源,在考试期间为了弄短定理并证明严密性不在乎成绩;用于拒绝潜规则,采用大字报的方式揭发老师的灰色手段;升国旗时演讲的也是带有探索研究性质的话题,这些都是不符合“学生”行为规范的。作者塑造了不谙世事的“安德烈”,自我意识极强,根本不在乎所谓的规则。这不是胡闹,不是叛逆,不是抗拒,而是站在自我的角度进行思考,“本我”占据主体意识,按照自己近乎偏执的信念,本能地展现着自我。同时,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的自我,一方面是人们所说的“良心”,另一方面是“理想自我”,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超我是人格中善良的部分,他讲求道德,而且严厉要求主体按照理想的善之标准行事。这个善之标准是怎么来的?当然是后天教育而来的。例如父母的影响、学校的教育等,但是安德烈公然违抗父母与学校老师,几乎不存在超我,也不存在所谓的良心与理想自我,在超我与本我的制衡中,本我成为“骑手”,控制马儿的方向与行进。在《冷枪》中,老背在网络上的打枪游戏中是英雄,“已经是这个国家里枪法最准的人之一”,他沉迷在网络世界,“大白天别人去上课,他捂着大被睡觉”,这样的沉迷让他变得与人群格格不入,后来更是遵循着他的原则——公平,打“死”了开外挂、放冷枪的“疯狂丘比特”,这一系列事情都表明了“自我”的消失淡化,张扬的“本我”意识成为主人公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对于《大师》中“我”的父亲高棋来说,喜爱下象棋已经到了近乎痴迷的状态,但生活的窘困让父亲压制“本我”,抑制内心的欲望,从纵横棋场的象棋高手沦为十年不下棋的可怜人。

正如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提道:
“自我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表现在它通常控制着一个人的能动性,所以它和本我的关系,就像旨在驯服马匹的骑手,而马匹的力量其实远大于骑手。”双雪涛的笔下,有着一群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本我”长期占据着意识主流,“自我”与“本我”似乎变成了被阉割的不完整的两个人,这种失控状态下,这些人物形成了不健全的人格结构,一步步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现实,只能蜷缩在思想的角落。即使他们天赋异禀、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悟性,照样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发挥,在时代与环境的重重打压下,沦为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可怜人。
平淡无奇:反英雄的“凡人”
如果追溯英雄的发展史,我们从《荷马史诗》等经典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窥见反英雄这一类文学形象,他们作为“英雄”等理想人物的陪衬出现,相悖于人类的共同理想。但进入二十世纪,“反英雄”的概念得到了丰富与扩展,如《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中王岚对“反英雄”这一概念的阐释:“反英雄不是‘反面人物’或‘反面角色已解决的同义词,而是对文学作品中某类人物的统称”,“从表面看,他们可能卑微琐碎,对社会政治和道德往往采取冷漠、愤怒和不在乎的态度,甚至会粗暴残忍,但他们的动机并不邪恶,体现了作者对‘英雄’概念的分解和拆卸”。
双雪涛拒绝塑造拥有波澜壮阔人生经历的高大全式“巨人英雄”,而是将视角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表现出他们对现代社会条框与道德的反叛,以及对社会发展不充分导致的阴暗角落的抗争,对“理想”概念进行拆分与粉碎,消解了人物宏大的心理结构和性格结构,主人公不是大众眼中的“成功人生”,也没有令人羡慕的“传奇经历”,但是他们身上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敢作敢当、诚实善良、执着、生性浪漫自由、相信公平、崇尚科学、坚持探索与寻找。双雪涛在学校、工厂环境、社会环境中创造着自己的“英雄”。《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主人公安德烈是一名普通学生,勇于拒绝学校的潜规则,用大字报的方式替“我”争取去新加坡的名额,在他父母极力撇清关系的同时,他站出来说:“妈,这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干的,你诬赖别人干什么?”就连“我”自己的父母看到我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时,也只是默不作声。他成了“我”学生时代的“英雄”。《跛人》中的刘一朵是自由、敢说敢做的女孩,不抗拒“性”,脱下裙子翻墙,高考后私奔似的奔向北京。这些行为表明她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优秀”女孩,大胆、“不害臊”是她最鲜明的特征,“我”为她的疯狂痴迷。《无赖》中的老马,有点贪财却为人仗义,喜欢喝酒却生性洒脱。《冷枪》中的老背遵循着唯一原则——公平,当他发现有人放冷枪时,选择打“死”了那个人。他没有后悔,冷静地承担后果。“他像个孩子一样,脸朝着墙壁,很快睡着了,而且开始打鼾,他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睡觉了。”
双雪涛小说中的主人公拥有美好的品质,但认为现实是杂乱无序、精神价值边缘化的荒诞世界,沉醉自我世界,因此道德崩溃,良知消解,失去追求现实幸福与终极关怀的勇气。性格失衡使他们成了人群中的另一个、社会中的边缘人。双雪涛笔下的人物群像既表现了对理想的寻找与追求,也借此讽刺着社会的不公,世界的荒诞与冷漠,人生意义的消解,其背后是直白的令人难以直视的呐喊。
优哉游哉:孤独的“诗人”
新时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消解中心、瓦解权威成了作家的普遍共识,他们纷纷开始书写自己故乡的故事。双雪涛也不例外,当他回望家乡时,带着浓浓的眷恋和深厚的感情,以一种温柔甚至宽容的眼光与态度去看待陌生而熟悉的人。同时,双雪涛是有作家意识的难得的年轻作家,呼吸着东北老工业城市沉重的气息,回望着崩塌、衰败的历史环境中的人与物。正如他曾在访谈中说的:“对我来说,东北一部分是我内在的部分;另一方面现在它也是我的另一个他者,我是努力地保持距离看待他。”由此,本着这样的初心和文学使命,他笔下的人物带有浓郁的浪漫气息,闪耀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的人性光芒。
正如《长眠》中开头引用《圣经旧约》第一章第十九节的一句话:“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于你。”有一种不顾一切奔赴于你的即时感,苍凉无助却热血奔涌,而这正是老萧和小米用生命守护着“苹果”的印证。作者在这里又别出心裁地将老萧设为一个会写诗的人,“老萧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同时,小米也是一个会为爱情抛弃传统道德的女人,她背叛了“我”,为爱而走。
他们为爱而活,为爱而死,奔向生命的尽头,却获得了超越生命的浪漫。《冷枪》老背不屑于现实的不公,一心追求游戏中“唯一的真理”;“我”是现实的,会为了顺利毕业而收起锋芒。但当老背在游戏中被背叛时,古老的英雄主义,热血的兄弟情谊,一时间难以压制,最终还是用“武力”守护住了老背矢志不渝的信念。《无赖》中的老马,谈女人,喝宿酒,清醒的日子没有醉酒的日子多。
但就是这样一个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他爱“我”的手,“一双手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念书的胚子”,当他在帮我要回被抢走的台灯时,摘下礼帽,嘴角浮现着骄傲的笑容,将酒瓶砸向自己的脑袋,像是完成了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严肃认真的背后流露着印在骨子里的浪漫热血。作者将人物放在一个日渐衰微的城市环境中,放在一段快速发展变化中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中,但在这种环境中依然存在着熠熠生辉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以生命的代价去追寻与守护,当生命陨落时,换来的是理想的永恒存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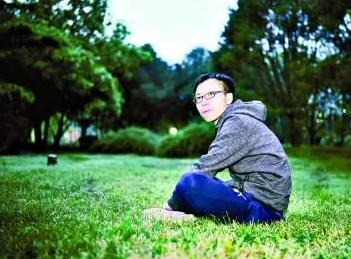
为故事留下一个充满诗意、开放式的结尾是双雪涛惯用的手法,他给了读者多重想象与阐释的空间,也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对未来的期许。《无赖》中老马以壮烈且决绝的方式给予“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而作者并没有讲老马到底有没有死。《冷枪》最后“我走到身后,挥起拐杖把他打倒在地”,像骑士般保护着老背坚守的公平,而作者没有讲“我”最后到底能不能顺利毕业。《长眠》以老萧的一首诗来结尾,“让我们就此长眠,并非异己,只是逆流。让我们就此长眠,成为烛芯,成为地基。让我们就此长眠,醒着,长眠”。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诗歌结束也伴随着生命的消失,但人们对诗歌的无尽探索与阐释也预示着生命的长存,用诗歌传唱着灵魂的崇高、不朽的生命。这样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始终给读者一种待续的感觉,似乎下一幕,人物又能继续上演着传奇的人生经历。就像双雪涛自己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总得有一点在虚构里办的事,有些事情在现实中办不了,那就在小说里办。我们看到电影里一个人可以倒下再起来,起来再倒下,然后再起来,甚至死而复生。但在现实生活中,倒下后是很难爬起来的,所以,我愿意在虚构中让趴下的人能够再站起来。”
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在历史奔腾不息的洪流中,浪漫与坚守理想有时要付出残酷的代价,但正是这种代价让生命变得崇高而有尊严。安德烈、老背、老萧、老马、刘一朵在用生命反抗着绝望与孤独,他们留下的是对时代、对历史的追问,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与追寻。正如《大路》中引用阿贝尔加缪的一句话“人们必须相信,垒山不止就是幸福”,刹那间的极光将是永恒的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