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美学张力与启示意义: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厄舍府之倒塌》论文
2024-06-01 11:52:23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关于存在问题的讨论已持续数千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相较于古典形而上学更新颖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存在与时间》中,他首创性地提出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提出“此在”等概念,将现代哲学观念上的“存在”与古典形而上学中的“存在”加以区分,奠定了现代与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视角,从《厄舍府之倒塌》中的各要素,以及其所展现的存在主义观点入手,揭示小说在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关于存在问题的讨论已持续数千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相较于古典形而上学更新颖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存在与时间》中,他首创性地提出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提出“此在”等概念,将现代哲学观念上的“存在”与古典形而上学中的“存在”加以区分,奠定了现代与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视角,从《厄舍府之倒塌》中的各要素,以及其所展现的存在主义观点入手,揭示小说在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1839年9月,美国著名小说家爱伦·坡发表了短篇小说《厄舍府之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故事讲述了一对兄妹在家族没落后相依为命,住在古老的厄舍府,长年累月经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怀着十分病态的心理维持着生活。
该小说一经发表,便得到了读者与文学界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小说的大量讨论。在心理学方面,有学者借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对其进行了解读,并认为“厄舍对人格中阴影的逃避和恐惧、阿尼玛的错误投射,以及人格面具的僵硬异常都导致了他人格的扭曲,使他丧失理智”。又如,在叙事层面上,有学者认为小说中对厄舍府的描述作为“物”的叙事,推动了整个叙事的发展,并揭示了人物命运发展的必然。以及在社会认知方面,有学者认为厄舍社会关系的破坏引起了其社会认知能力的缺失,而古老的厄舍府这一实在的客体又不断对他施加影响,在恶性循环中,厄舍理性的崩溃成了必然。
显然,以上研究仍未能完全开掘出该小说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内涵。然而,当我们以存在主义视角看待这篇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各要素与关键情节所展现出来的存在主义意义。
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在论述中突出地重提了存在问题,阐述了重提该问题的必要性,并对其进行了讨论。
首先,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与批判中,海德格尔将存在与存在者进行区分。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我们怎样讨论存在者,存在者总已经是在存在已先被领会的基础上才得到领会的。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不应是某一固定的存在者,而是一个变化中的过程,是使存在者“去存在”的过程。
其次,在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要在存在者中把握存在的观点。在现象世界的众多存在者中,海德格尔尤其重视人这一存在者,因为“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并将人命名为“此在”。
此在的本质在于去存在(Zu-sein),从此在的生存观点上来看,筹划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此在对现状是不满的,所以此在将会对自己的生存进行筹划,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同时,此在的存在状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世界中的存在。
最后,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去存在”属性),所以此在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
最后在进一步的论述中,海德格尔提出驱动此在去获得本真状态的必要动力——对死亡的畏惧,即“向死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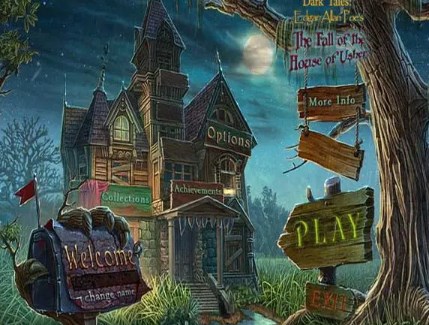
来自古屋的“死亡”邀请:“存在”的前提条件
在《厄舍府之倒塌》中,三位主人公活动的场所即是厄舍府。此外,厄舍府也在向主人公施加着不可忽视的“形而上”影响。因此,厄舍府的形象在小说解读中尤为重要。
归根结底,厄舍府象征着死亡。
首先,从外部来看,厄舍府是腐朽而荒诞的,“那种气息并非生发于天地自然,而是生发于那些枯树残枝、灰墙暗壁,生发于那一汪死气沉沉的湖水。那是一种神秘而致命的雾霭,阴晦,凝滞,朦胧,沉重如铅”。此处,枯树残枝、灰墙暗壁等暗示着毁灭、时间与死亡。
其次,从厄舍府的内部来看,“黑色的帷幔垂悬四壁,室内家具多而古雅,但破旧得令人不适。房间里有不少书籍和乐器,但未能增添一分生气。我觉得呼吸的空气中也充满了忧伤,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凛然、钝重、驱赶不散的阴郁”。黑色的帷幔遮住了阳光,阻拦来自外部世界的生机。古雅的家具本该是庄重与圣洁的象征,却破旧得令人不适,象征光辉家族的没落。呼吸本应是人调节身体机理的必需,却为“我”带来了忧伤。
同时,无论是从厄舍府的内部还是外部上来看,在对颜色的描绘上,作者着重表现的是“灰”“黑”“白”三种颜色。从颜色的象征意义上来看,黑色与灰色无疑将给读者带来关于死亡的联想。
最后,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上来看,主人公赋予厄舍府的感受与联想也皆与死亡相关。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我们能直观体验到故事叙述者“我”的心理活动。日本美学家涩泽龙彦在《恶魔幻影志》中曾对以死亡为主题的恶魔艺术进行过论述,他认为,“人类面对恶魔时感受到的对死亡的恐惧并非对纯粹非存在的恐惧,而是对存在发生的变化感到恐惧”,同样的,在主人公“我”的眼中,厄舍府具有某种非存在的性质,也引起了“我”某种实在的感受。从常规意义上来说,死亡对于人类而言仅仅是作为悬临的可能性,其中也包括主人公,然而,作者通过对厄舍府死亡气息的烘托与描写,把死亡从抽象的可能性变成了可知可感的客观实在。所以厄舍府是死亡的象征。
在死亡中做抉择:此在的本真与非本真存在状态
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观在决定此在的存在状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存在状态需要通过直面死亡来获得,是要“先行到死亡中去”的,而在死亡中做出的抉择,决定了此在的存在状态。
厄舍与此在的非本真存在状态。第一,厄舍对于未知的态度揭示出厄舍的非本真。首先,厄舍对待任何未知事物的态度都处在极端恐惧之中。“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事并非害怕事情本身,而是怕其后果。”这里厄舍明确指出,令他感到恐惧的并非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本身,而是这件事情将要带来的后果。当厄舍意识到“不确定”必将发生时,他选择懦弱地把自己从这个“必将发生”中抽离出来。在面对玛德琳之死时,厄舍同样为其将带来的结果而感到恐惧。显然,这与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主义相违背。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未知虽是无意义的,但正是无意义赋予了人自由创造意义的权力,如萨特所说:“人不是现成的,人是自己造就自己的,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所以,在面对未知时,厄舍因为对存在的模糊与不确定放弃了利用“无意义”来创造意义的权力。他对未知的抗拒,是他“恐惧症”的根源;其对未来的否认揭示出他非本真的存在状态,揭示其走向灭亡的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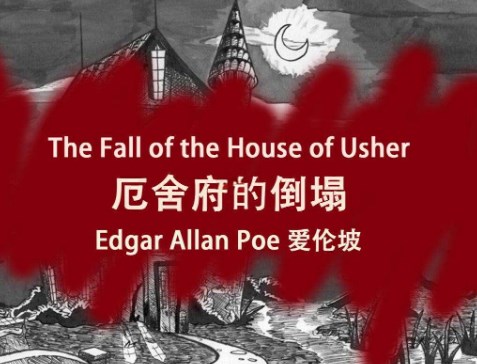
第二,厄舍对于死亡的思考揭示出其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首先,小说对玛德琳所患疾病的描述虽仅寥寥数语,“根深蒂固的冷漠压抑、身体一天天地衰弱消瘦,加上那种虽说转瞬即逝却常常发作的强直性昏厥构成了她疾病的异常症状”。但据推理,“根深蒂固的冷漠”“身体一天天地衰弱消瘦”等症状与厄舍相似,暗示读者马德琳小姐与厄舍所患的是同一种精神疾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德林之死向厄舍展示的是患上这种精神疾病所“注定”的结局。
其次,据海德格尔的论述,人们对于死亡的假设当然不是指真正的死亡,“向死而生”提出的原因也仅是因为只有当人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明白生的真谛,所以“向死存在也就不能是指:停留在终结的可能性中”。然而,厄舍对于玛德琳之死的思考却截然相反:确有可能发生在自身的事被厄舍视作即将发生,甚至已经发生的事——他将自己的思考与生命停留在了终结的可能性中。于是,玛德琳“复活”并夺走厄舍的生命。
一方面,厄舍对于未知意义的抗拒,使他无法在未知的选择中获取本己;另一方面,厄舍确已将对自我的考量放入死亡与未知中,但他懦弱的选择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绝望。
“我”与此在的本真存在状态。第一,“我”对未知的追问体现出“我”的本真。自小说开始,们便可以发现主人公“我”对周遭环境与事件的思考,如“我”对厄舍府的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仔细思忖。是什么使我一见到厄舍府就如此颓丧……”当“我”获得某种接近死亡的感受时,“我”并未麻木地接受或极端抗拒地否定,相反这样的思考证明主人公正试图通过理解周遭现象世界与其中各要素的关联机制来确定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第二,“我”的抉择体现出“我”的本真。首先,主人公试图改变周遭环境。例如,“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千方百计地减轻我朋友的愁苦。我们一起绘画,一起看书,或是我如痴如醉地听他那架六弦琴如泣如诉的即兴演奏”。即便这些努力没能使厄舍敞开心扉,也未能改变所处状况,但“我”已经获得了部分有积极意义的存在。
其次,“我”的逃离是“我”生的选择。厄舍府倒塌前夕,“我”曾险些被死亡的阴影所俘获:“尤其是在把马德琳小姐安放进那个地窖后的第七天或第八天晚上,我在床上充分体验到了那种影响的力量……”在这段叙述中,“我”感受到的那种影响的力量,便是来自死亡。“我”目睹玛德琳小姐之死,并忍受着厄舍极端的疯癫,在这个大风四起的夜晚,“我”似乎也即将坠入深渊。在死亡就快要把“我”俘获之际,“我”做出选择:逃离。这看似是主人公受到惊吓而做出的举动,但就其更深的内涵来看,厄舍与玛德琳之死是向死的臣服,而我的“逃离”即是向死而生。
第三,“我”的“凝视”至关重要。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凝视”具有非凡的含义。许多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对“凝视”进行了深层次剖析。“视线确认了‘我’的存在,也确认了‘他者’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人的意义、世界的意义才由此得以产生和确立。”
在小说结尾,当“我”凝视厄舍府,“我”先前看到的那道裂缝急速变宽。“凝视”一词使读者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厄舍府在“我”的面前崩溃这一事实。作者通过“凝视”一词在读者的脑海中构建起一个“我”与厄舍府相对立的画面,从而使读者体会到“我”的存在,再一次赋予他主体性。
所以在小说的三个主人公中,“我”呈现出的是此在的本真存在状态。
从《厄舍府之倒塌》中我们可以看到,此在的生存,存在,存在状态等是相互关联的系统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核心始终是“人”本身。现象世界的无序或是波流汹涌的海,在这之中最残酷、最根本的便是“死亡”。完整的“人”往往在湍急处入海,将自己放置于对“死亡”的思考中,并通过在死亡中的自由选择,成为本真、本己与本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