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小说《天堂》中“花园”意象的象征意蕴论文
2024-05-31 14:20:22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作为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作品一直都引起后殖民学者的热议。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在东非地区印度洋的桑吉巴尔岛,因地理位置,桑吉巴尔岛和他背靠的坦噶尼喀内陆一直以来都不得不对印度洋敞开着大门,这里聚集着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各种族人群。1886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吉巴尔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和德国各占据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部分,各种族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古尔纳小说《天堂》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主人公优素福是一个斯瓦希里小男孩,12岁的
作为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作品一直都引起后殖民学者的热议。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在东非地区印度洋的桑吉巴尔岛,因地理位置,桑吉巴尔岛和他背靠的坦噶尼喀内陆一直以来都不得不对印度洋敞开着大门,这里聚集着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各种族人群。1886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吉巴尔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和德国各占据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部分,各种族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古尔纳小说《天堂》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主人公优素福是一个斯瓦希里小男孩,12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债台高筑被抵给了他最尊敬的一位富商,优素福称呼他为阿齐兹叔叔。第一次看到阿齐兹叔叔家的花园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到达了天堂。后来优素福开始跟着阿齐兹叔叔的商队到处辗转,一路上随着德国人的殖民,到处都在发生战争、暴乱、镇压和反抗。他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丑陋,目睹了生之苦难和死无尊严,发现自己一直遭受的性剥削和身体剥削历史而自己却对此无能为力后,终于认清了现实,发现无数个如他一般的东非底层人民群众都无法在后殖民背景下摆脱悲惨的命运,自己一直所处的也只是虚假的天堂。
意象由意境和物象融会于一体,作者把“不可言之理以及不可述之事”都寄寓在意象里,赋予意象重现作者当时的情景和感受的功能。意象自身也是各种心理因素的综合,在这里凝聚了创作者最真切的审美情感及最深刻的审美思想。如何塑造和把握文本意象就成了作品美学创作的核心和关键。对《天堂》全书进行审美观照后可得知阿齐兹叔叔家里的花园,应当是全书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贯穿整部小说,一路见证着主人公优素福的自我觉醒,是其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代表符号。在小说开始,优素福来到阿齐兹叔叔家后,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阿齐兹家的花园,在小说结尾,优素福追赶德国军队前,最后听到的声音也来自花园。优素福的命运和其对花园的感情紧紧交织在一起,并且优素福对花园的情感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上层阶级的象征
作为商人和赛义德,阿齐兹叔叔富可敌国。即将成为奴隶的优素福在到达阿齐兹叔叔家后一眼就被花园吸引了,“他瞥见了花园,觉得看到了果树、开花的灌木丛和水的亮光”。“果树”“开花的灌木丛”“泉水”都是当地人民描述天堂时常用的意象,象征着美好与希望。阿齐兹叔叔家的花园就是仿照着传说中描绘的天堂建造的,代表着阿拉伯裔精英阶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花园是统治阶级和上层阶级建造出来的人工天堂。作为身处非洲腹地的普通人,哈米德夫妇深受贫困之苦。在优素福随商队到腹地的山脚村庄驻扎时,对他的房东哈米德夫妇家里的花园竟然荒废着而感到疑惑。从哈米德夫妇的回答中我们就能得出答案,“神赐予了大商人一座天堂般的花园,给我们的就只是满是毒蛇和野兽的灌木丛”。这就是财富和阶级的差距使然。纵使后来哈米德和优素福打算砍倒荆棘灌木来建造花园也以失败告终,这也隐喻着普罗大众不配拥有花园,花园是上层阶级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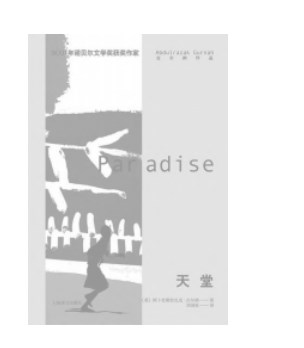
作为奴隶,阿齐兹叔叔家里的花园对优素福来说一直是天堂般的地方。在优素福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花园就是他生活的唯一希望,他为之着迷。在第五章《心心念念的树林》中,优素福在花园里遇到阿米娜,并开始了一段秘密恋情。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学中经常出现以女性为中心的情欲天堂,特别是在描述瓦克瓦克岛时。瓦克瓦克岛一直以来都被称为是男性幻想的终极天堂。首先瓦克瓦克岛是一个黄金天堂,居民们都用黄金给狗做项圈,其次瓦克瓦克岛还是一个情欲天堂,《哈丽达》里面就描述过岛上的各种奇特作物:“女性模样的果实,相同的身体和身材,眼,手,足,毛。拥有乳房的同时也拥有了与女性一样的外阴,散发着芳香,中间还有一条河,它的水比蜜和溶化了的糖要甘甜。”女性模样的果实就象征着侵犯,她们挑逗地裸露着生殖器,发出高潮的叫声来满足男性的性幻想。费德瓦·马尔蒂·道格拉斯认为,瓦克瓦克岛中女性情欲商品化源自《古兰经》天堂中的“性和流动”部分,它为男性的终极性满足建造了花园。阿齐兹的花园又何尝不是他依据自身男性性满足而打造出来的天堂。阿米娜在七岁时便作为债务的抵押物,由父亲卖给了阿齐兹。阿米娜是男性交易的商品,如同瓦克瓦克岛中女性模样的果实,她被送到阿齐兹的天堂花园等待成熟,直到可以被享用。优素福意识到天堂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是当权者用来娱乐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并给他们虚假希望的工具”。优素福也曾设想拒绝被奴役,幻想着他能和阿米娜一起逃离这里,建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花园。然而这个花园梦最后也被阿齐兹的妻子祖莱卡彻底打破。祖莱卡在和优素福的相处过程中进行勾引,并且不顾反对抱住了他。费力挣脱后,优素福倍感羞辱,因为这让他意识到“连最单纯的美德都被他们的阴谋、仇恨和报复性占有欲变成了交换和交易的筹码”。到这一刻,优素福彻底完成了自己的身份构建,追寻花园的梦也就幻灭了。
理想世界的象征
东非的自然环境,在小说里往往以狰狞的面目出现。特别是阿齐兹的商队越是深入东非内陆,环境就越是呈现地狱化的本相:湖上的暴雨让商队难以通过;荆棘丛林不断撕扯着人们的肉体;野外睡觉时会有鬣狗来吃人的脸;连成群的狒狒都可以跑来打劫人类。社会环境也自始至终充满着暴力与迷信。阿齐兹多次带着他的商队深入东非腹地去往天堂之湖,他们带着锄头、刀具以及玻璃器皿等各种开化器材去和当地那些他们认为的野蛮人做买卖,一切看上去似乎挺和谐,但充满了暴力与血腥。商人在商旅时要依靠当地人来指引方向,以及获得充足的食物。然而内战、贩卖奴隶和瘟疫等的大肆流行致使东非内陆人们彼此之间相互猜忌。此时商队的到来就十分容易引发暴力或战争。阿齐兹商队的领队穆罕默德就曾说过,“当其他办法全都行不通时,火药和子弹总能奏效”。这些人也许后来也会因帝国殖民的影响而成为受害者,可是在此之前他们也有过自己的罪恶。他们本身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同时又以同样的种族主义暴力来对待那些所谓的野蛮人。那些野蛮人本身也不是天使,他们经常袭击村落,劫掠妇女,正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贪婪又残暴。
古尔纳在小说中多次使用“四面围墙”和“封闭”等词来形容阿齐兹叔叔家的花园,那么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就代表着保护和安全,在这里优素福可以美美睡上一觉,不用担心现实世界的恶劣环境。花园里透出的“幽静”与“凉意”,更是让人心向往之。花园里流水潺潺,花果飘香,种满了石榴橘子。石榴树是丰饶之树本身,树干和果实就像勃发的生命一样坚实而丰满,这意味着在花园里不用担忧果腹之饥。这样一座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正象征着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与优素福同样被抵给商人阿齐兹为奴隶的哈利勒曾对优素福讲过一个民间故事:杜尔·古尔南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得知在北边住着歌革和玛各,他们是不会说话的野蛮人,总是劫掠邻居的土地,于是杜尔·古尔南修建了一堵歌革和玛各既爬不过也挖不穿的墙,那堵墙就是文明世界边缘的标志。阿齐兹的花园也是杜尔·古尔南帝国的一个缩影,在那里,墙守护着内部的宁静和谐。墙内的花园象征着制度有序的富饶理想文明世界。一墙之外则是充满暴力与迷信的现实野蛮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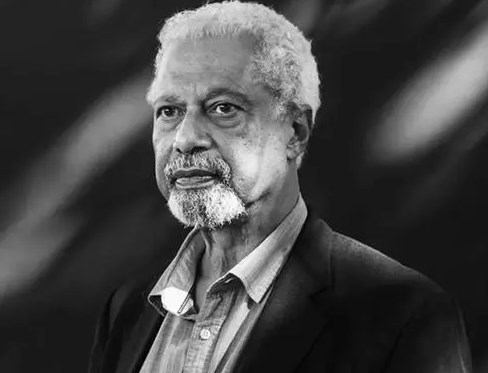
桑吉巴尔岛文化的象征
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向来被称为欧洲大陆文化最多元的地区之一,隶属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桑吉巴尔岛也不例外。这里聚集着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各种族人群形成了属于桑吉巴尔岛独特的文化。花园是当地部落文化的一个典型象征,代表着当地人民对天堂的想象。书中借用优素福的视角,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了阿齐兹家中花园的美丽景色:“花园被分成四个部分,中间有个水池,还有渠道流向四个方向,每个部分都种有花草和灌木”。并且花园的景象常常令他置身其中时仿佛听到了音乐声。河流、绿色及乐声都是描述天堂的经典意象。小说中也曾多次描述过天堂的模样:“天堂有四条河流。它们流往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将花园一分为四。而且到处都有水。凉亭下,果园旁,流过阶地,沿着林边的小道。”由此可以看出花园中的几何设计、潺潺流水与异国果木都是仿照桑吉巴尔岛文化中所想象的天堂而建,体现着桑吉巴尔岛人独特的审美文化。然而不同文化中对天堂的定义和意义都有所不同。此时的花园便是桑吉巴尔岛文化的象征,处处体现着当地的信仰。然而在殖民背景下,西方殖民者不仅对非洲原有的经济、政治产生了冲击,还给非洲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带来西方文化对天堂的“解释权”。殖民时期,从西方而来的传教士深入桑吉巴尔各个村镇和部落,在全国各地都设法开办学校来传授西方文化与思想。正如书中所说:“这些年轻人会失去更多。有朝一日,他们会让这些年轻人唾弃我们所了解的一切,让他们背诵他们的法律及其关于世界的故事,仿佛那是圣言。”
小说结尾德国军官强力打开阿齐兹叔叔家的花园,象征着殖民主义者打开了桑吉巴尔岛文化的大门,强势地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引进该殖民地,花园原本的样子也将由西方文化审美而重新建造。从文化层面讲,殖民者的到来挑战并颠覆了当地的文化根基。也就是说,德国人把当地人从他们所属的天堂驱逐了。优素福追赶德国军队前,“他听到身后的花园里传来像是在闩门的声音”。此时花园闩门就象征着桑吉巴尔岛文化的封锁,也即衰败的开始。不仅如此,文化信仰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识之一,它为个体身份认同提供了唯一、不可替代的价值源泉。花园闩门意味着桑吉巴尔岛群众在殖民统治的背景下逐渐丧失了个体的身份认同。
现代非洲文学是在殖民主义的熔炉中造就而来的。1963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桑吉巴尔爆发革命,阿拉伯裔公民古尔纳在新政权的统治下被迫离开家乡,作为难民来到了英国,直到37岁才有机会重返故乡,他目睹了故乡小镇的衰颓,那些两鬓斑白,牙齿掉光的人依然生活在那里,就像作为时代的物证端坐在历史的深处。古尔纳认为他要写出那个环境中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盘算,他们的喜忧,而不是由外来者和主流的讲述者构建一些被简化了的故事。这些简化和重构历史的胜利者并不真正关注他们,或者只是通过某种与他们的世界观相符的框架观察他们。
意象作为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往往昭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古尔纳通过对花园这一意象的运用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歧视、难民问题等方面。通过对小说中花园意象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殖民统治下非洲底层民众的现实境况。花园象征着上层阶级、理想世界以及桑吉巴尔岛文化。花园梦的幻灭则是指上层阶级的压迫、理想世界的崩塌,以及当地文化的落寞。古尔纳把花园描述得愈美好,非洲人民的生活就愈显得水深火热。对《天堂》这样后殖民作品的分析能够激起读者对难民正在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同情,从而增进人们对第三世界受难者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