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论文
2024-05-27 09:21:31 来源: 作者:heting
摘要:锦,在古代被人们视为是最贵重的织物,以经、纬的交织而展现着丝绸的独特之美。起绒锦在西汉时期,其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开拓与发展,呈现出以织锦为地,绒圈为花的工艺特点。文章从西汉官营机制的应用发展为视角切入,明晰汉代统治者在蚕业、缫丝、官令等原材料,技术手法及中央政策各层面中的关键性铺垫,并以汉代出土的绒圈锦为核心切入点,分析其细腻精湛的工艺结构,绚而不杂的色彩,品味深沉且庄重的色彩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观念。最后阐释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不仅是汉代这一历史阶段中最精美绝伦的部分,更为后来漳绒、妆花绒、天鹅绒等多样
摘要:锦,在古代被人们视为是最贵重的织物,以经、纬的交织而展现着丝绸的独特之美。起绒锦在西汉时期,其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开拓与发展,呈现出以织锦为地,绒圈为花的工艺特点。文章从西汉官营机制的应用发展为视角切入,明晰汉代统治者在蚕业、缫丝、官令等原材料,技术手法及中央政策各层面中的关键性铺垫,并以汉代出土的绒圈锦为核心切入点,分析其细腻精湛的工艺结构,绚而不杂的色彩,品味深沉且庄重的色彩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观念。最后阐释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不仅是汉代这一历史阶段中最精美绝伦的部分,更为后来漳绒、妆花绒、天鹅绒等多样性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汉官营,丝绸,起绒锦
《说文》载有:“锦,襄邑织文。从帛,金声。”[1]锦是以彩色经纬丝交错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物,织造工艺最为复杂,是古代丝织工艺技术的最高代表。早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盅刑骨器上面刻有蚕纹表明其作为丝织物的原料,开启了丝织业发展的新阶段。[2]西周时期,织锦的制作以缠绕、隔织等织造方法,部分镶嵌和刺绣等工艺进行装饰,制作工艺非常精良。后至春秋战国时期,在织造中采用缠绕、隔织、撇捻织、横纱织等织造方法,刺绣、倒钩、镶嵌等工艺,制作难度颇高,工艺极其复杂。随着社会思潮的涌现,服饰审美的变迁促进了织锦技术的进步。至战国时期,人们对织物“增色”的思维式创新促就了西汉官营丝绸起绒锦卓越的纺织技艺水平。以奇突效果为特色的起毛锦是在纹锦基础上的创新式发展,是我国最早发明创造的绒类织物。
一、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
(一)西汉官营机制的应用发展
西汉重视以丝织业为源头的蚕业,统治者设有织室、锦署来分级管理织造织锦,以供宫廷享用。《汉旧仪》载有管理和指导全国蚕业生产的“蚕官令、丞”及“暴室者,掖庭主织作染练之署”,且上林苑设有蚕馆,饲养量达“千薄以上”,[3]通过中央规束的层级分工,使织锦流程秩序严谨化,品种质量高层次化。《韩诗外传》载:“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能成丝。”《春秋繁露》载:“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成丝”足见当时人们已掌握沸水缫丝的技法,[4]且能应用蚕丝中各茧层丝纤维的不同纤度配茧,科学地控制缫出丝物所需的生丝纤度,[5]这为起绒锦经纬丝线的质量提供了基本保障。《天工开物》中的纺车络丝同现代缫丝所用的基本一致,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记有完整的络丝车图形,[6]均表明起绒锦的织造条件在西汉时期已基本形成。孝文帝六年,报单于书中“绣十四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赐锦绣绮殺杂帛八千匹。”河平四年“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又“遣使者持帷帐锦”,[3]3758频繁的对外馈赠与交流,加快了起绒织物多样化的发展进程。汉朝的封建贵族、官僚以及大富豪作为丝织物的核心消费阶级,其对丝绸的大量享用与耗费在《盐铁论•散不足篇》中有所记载:“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紬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7]大量的高级丝织品用以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需要,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促使工艺精美的起绒锦得以发展。《后汉书•舆服志》中:“(后汉)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剪氂蔮……公卿、列候、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缯蔮”[8]其中的“剪氂”一词,被认为是裁剪起绒织物的步骤手法,进一步证明了在西汉时期,起绒织物得到了发展与应用。
(二)工艺结构分析
“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锦的生产工艺极高,织造难度极大,因此古人将锦同黄金等价,被视为古代最贵重的品种。锦是以二色及以上的彩色经、纬丝,用多重组织来交叉织成的丝织品。
起绒锦在织锦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发展,实质上就是以织锦为地,绒圈为花。其亮点在于它的织造结构层面需用到起绒杆作为一根假纬来起绒圈。[9]以或生或熟的桑蚕丝为原料,在双经轴结构的提花机上织造,一般由两组及以上的经线同三组及四组纬线相互交织,经线中分为地、绒二经,纬线由粗、中、细及起绒杆组成。每组线以一定比例排列,一定顺序单独地投纬,将地经与纬线相交,绒经和起绒杆相交,最后抽出起绒杆,形成突出于锦面的绒圈,再以锐利的刻刀割断绒圈,以此产生绒毛,锦面即可形成绚丽丰富、大小交替的绒圈花纹。
西汉史游之作《急就篇》云:“锦绣缦䋃离云爵”,颜师古注:“䋃,谓之刺也。”又《广韵》:“䋃,绢帛毛起如刺也。”形象地描绘了绒的特征。[10]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绒圈锦就是这种有䋃的锦,即起绒锦,是至今历史上发现最早的起绒织物。(图1)该丝织物是以经线提花起绒圈的经四重平纹组织,以地纹经Ⅰ、地纹经Ⅱ、底经、绒圈经为组合,等比排列。大小绒圈用织入起毛杆的方法而构成,每织一梭地纬,就交叉以一根起绒纬。最后抽去假纬,使纹锦地上织出有高度的绒圈花纹,组合花型层次分明,绒圈大小交替,在锦面形成浮雕状的凸起,外观甚为华丽。武威磨嘴子东汉墓亦出土有起绒锦,其结构系三重三枚经线起绒的织法。[11]以绒纬代替纬线织入,分三组:绒圈纹经、地纹经、底纹经,使绒经在起毛部分覆以毛圈,花纹周正,对称排列。相较于西汉时期,起绒锦的工艺水平明显趋于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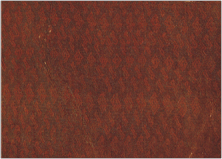
起绒锦中“立体绒圈”的技术将织物平面的纹样肌理建构成立体化,形成了由单调性视觉到多层性触觉的审美通感,深受人们的喜爱且应用于形制多样的各类丝织物之中。如满城汉墓的铁制铠甲边缝处镶以菱纹绒圈锦,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的叠菱纹起毛锦窄条用作丝穗装饰,马王堆一号墓的直裾素纱禅衣、绛紫绢地“长寿绣”面绵袍等以几何纹绒圈锦为缘边,据马王堆汉墓遣策记载,帷、乘云绣枕巾等都是“缋掾(缘)”指的就是“绒圈锦”。[12]29
二、色彩分析
《六书故》曰:“织采为文曰锦”表明锦的特点是先染后织,极富有文采。因此,起绒锦中的经纬线遵循以线染法的顺序先染色,然后在丝织物上装饰织造。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起绒锦花地清晰,色彩绚丽。其中,几何绒圈锦以多色经丝同单色纬丝交叉编织,以此来显现花纹之美。将四根经丝列为一组,纬丝均着单色,每组经丝采用二色或三色,以朱红色、绛色及明度不一的同色系丝线来提花织造,地色大面积地铺列茶褐色和玄色,交相辉映。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的北边箱中有一黄褐绢地“长寿绣”枕头,两端枕顶均用起绒锦。在棕黑显色的底面上,以朱红、深棕色经纬丝线交叉编织。武威磨嘴子62号墓中亦有菱花起毛锦,纹经铺以大面积黄棕,纬线以明纬、夹纬巧妙区分同一棕色的不同明度,正面挑起棕色毛圈,饰以叠菱形花纹。
总之,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色彩中多以深棕、黑色等深色系为底,以朱红色、绛色等明亮色为纹饰凸起。色彩深沉而鲜艳,花地明朗且协调,图纹清晰又雅致,织工精细巧妙,立体感极强。此外,起绒锦的经纬丝线先染后织,色彩的呈现得以牢固地保留。将色彩以起绒的方式呈现,颜色相较于普通织物,有着特殊的柔和感。如在深色底经上凸显竖立浓密的朱红色绒毛,给人一番温暖之意,以及恰到好处的厚实之感。绒圈锦中经线与纬线的交叉编织,着于丝线之上的色彩以自然巧妙的方式呈现出同一色相,不同明度的差异之美。体现和谐、典雅之美。
起绒锦色泽鲜艳光亮,外观绚丽的呈现,根本上是为了体现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红色系的应用蕴含着楚文化中对于暖色、崇日尚红的审美观念倾向。以及儒家《周礼》以五色示尊卑,五正色“青赤黄白黑”为优先顺序的着色,故而起绒锦中多以“五正色”中的“赤”和“五间色”中的“红”来呈现。绒圈锦中邻近色的自然协调,经纬线着棕红、黑色的搭配来体现深沉优雅、古朴雅静,附和了汉代推崇的“休养生息”之策、道家追求物质的“寡欲”和追求思想的“淡泊无为”。
三、起绒锦的深远意义
起绒锦的织造工艺在后代仍被赋予了创新性的延续发展,对多样种类的起绒丝织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出土有叠菱纹起毛锦,它以窄条的样式被应用于丝穗上凸显装饰的效果,其使用的奢侈程度同西汉早期楚地贵族墓葬相当,足可以见“绒圈锦”技术在新莽时期并未销声匿迹。[12]32中唐时期,《红线毯》诗中写有:“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13]这一时期的起绒织物以绒毯的形式而出现。南宋时期,《松漠纪闻》对回鹘的记载中写有“土多产瑟瑟珠玉;帛有兜罗锦、毛氎、绒锦、注丝、熟绫、斜褐”,[14]“绒锦”这一清晰的名词,彰显了沿用之意。《元史•舆服志》中有“怯绵里”的记载,《元宫词》中“剪绒段子御前分”进一步佐证了元代在起绒的基础上,附加以剪绒的技术而发展。[15]后至明代时期,滨海漳州起家的“漳绒”颇有盛名,马王堆汉墓中的绒圈锦,为现代生产的漳绒、漳缎作了铺垫。万历(1573-1620)时《漳州府志》载“天鹅绒,本出外国,今漳人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成割出,机制云蒸,殆夺天巧”,[16]此时期的漳绒在花、素差别之中呈现不同的美,素漳绒表面均为绒圈,和谐统一。花漳绒则是以部分绒圈按花纹割断成绒毛,在凸出的同时亦巧妙地与未割的绒圈相间,配合构成精美花纹。亦有在起绒锦基础上加以金丝线的交叉装饰,创造出了富贵吉祥的金彩绒。或是加入织金技术和挖花法,形成丰富绚丽的妆花绒等。[9]总之,西汉时期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不仅在前代的基础上予以了积极的创新,更为后世起绒织物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其“立体绒圈”技术通过织物表面竖的绒毛使得纹样肌理从视觉的单一层面上升至触觉的多层次化感受。绒毛的产生超出了一般的概念,打破了织物平面二维的局限性,演变发展为立体三维的优异效果。充分体现了古人丝织思想的浪潮式推进。以此为思想起点,后代在此基础上不断打破局限性,如通过置换或加入不同材料探寻绒花在多种类织物上的差异性体现,或加入织金工艺、挖花技术使得锦面绚丽多彩,不断朝着多样性的特点而创新。此外,以毛茸、丰满的锦面来表现独特的花纹元素,厚密的绒毛中体验到柔软、稳重的情感因素。
四、结语
织锦工艺自古以来为世人所慨,起绒锦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创新演变。中央对蚕业的官级化管理推动着丝织业原料的建设性发展,沸水缫丝的工艺技法为起绒技术中的必要环节,即经纬线的编织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官营丝绸中的起绒锦不仅开创了起绒技术的先河,以层次分明的组合花型,大小交替的绒圈,浮雕状凸起的锦面,经纬线交替编织形成颜色的暗与明,巧妙地展现绒圈锦的深沉华丽之美。还以背后蕴含的楚文化、儒家、道家等思想文化内涵,附和着汉代推崇的政教之道。对后代怯绵里、漳绒、天鹅绒等特色性起绒织物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17.
[2]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01):39-94+140-155.
[3](东汉)班固著,许嘉璐、安平秋、张传玺主编.《汉书》[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025-3758.
[4]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96:476.
[5]王树金.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工艺成就赏析[J].文物天地,2015,(09):31-36.
[6]宋伯胤,黎忠义.从汉画象石探索汉代织机构造[J].文物,1962,(03):25-28+44+23-24.
[7]张鹤泉.《盐铁论•散不足篇》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04):70-76.
[8]张惠康主编.《后汉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930-1931.
[9]项婉钰.浅析元明清时代产生和发展的起绒织物[J].艺术品鉴,2015,(07):316+10.
[10]张宏源,魏松卿.关于丝织品[J].文物,1972(09):62-66.
[1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12):9-23+79-80.
[12]夏添.先秦至汉代荆楚服饰考析[D].江南大学,2020.
[13](唐)白居易.红线毯,江洪伟注评.《白居易诗词选》[M].合肥:黄山书社,2008:051.
[14]洪浩著,王云五主编.《松漠纪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3.
[15]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20.
[16]赵承泽.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6-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