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到和解:《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叙述学视角解读论文
2024-05-20 16:36:13 来源: 作者:huangyuying
摘要:[摘 要]《喜福会》是一部典型的人物成长型小说,从人物的视角和声音层面来看,小说讲述 了两代华裔女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共情与和解的故事;从作者的视角和声音层面来看,小 说展现了
[摘 要]《喜福会》是一部典型的人物成长型小说,从人物的视角和声音层面来看,小说讲述 了两代华裔女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共情与和解的故事;从作者的视角和声音层面来看,小 说展现了作者谭恩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华裔女性多元身份构建的独特感知力和洞察力,可 以看作是作家自我情感的投射。
[关键词]《喜福会》; 叙述者;叙事学
谭恩美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华裔女作家之 一,其作品参与构建了美国华裔作家的话语体 系,引起了美国社会对华裔女性生存现状的关 注。《喜福会》作为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 一,聚焦于母女关系,反映了作者的成长故 事,也讲述了第一代华裔女性与第二代华裔女 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共情与和解的故事。

国内已有对小说《喜福会》的文本研究 以及从文化角度对身份构建进行分析的研究, 但鲜有从叙事学视角对文本情节、人物关系来 进行解读的研究。因此,本文结合叙事学理 论,分别从人物和作者的视角与声音来分析两 代华裔女性从冲突到和解的变化过程,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华裔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
1 人物视角与声音
叙事学理论把文本分为故事层和话语层 两个层面。故事层就是通过情节、人物、空间 等呈现出来的故事内容;话语层就是故事内容 的表现方式,即视角与声音。话语层作为故事层的重要表现手段,历来受到叙事学研究的 关注。在话语层分析中,视角研究谁在观察故 事;而声音研究叙述者传达给读者的语言,即 谁在讲述故事。声音是传达,而视角是传达的 依据。叙事学理论明确指出了观察者与叙述者 之间的区别。
首先,叙述者与观察者身份一致,也就 是呈现故事的叙述者与他所呈现故事中的人物 身份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人称“我” 通常被定义为说话的人,也就是叙述者。在 《喜福会》第二单元《二十六道凶门》中,四 个女儿以第一人称视角分别讲述了自己和母亲 之间的故事。在《游戏规则》章节中,故事在 韦弗里 ·江的视角下根据时间顺序向前推进。 小说中对母亲的描述出现在韦弗里的视角中: “我六岁时,母亲教我如何用无形的力量。这 是一种战术……尽管我俩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最 后这一点。”(谭恩美,2017)这段描述包含 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故事中的事件,即 母亲的教育;第二个层面是叙述者,她向我们 描述事件和人物对事件的感受。在这段文本中,韦弗里用第一人称叙述中见证人的旁观视 角推动故事的发展,叙述者在讲述一个他亲自 参与的事件,并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母亲既是观察者在看的人,也是叙述者 在说的人,视角是六岁时的韦弗里的,而声音 则是长大的韦弗里的,这体现了叙述学中聚焦 与叙述的关系。时间差异使叙述者能够对童 年记忆中的母亲作出更为理性的评价,也体现 了叙述者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变化。由于中美 文化差异,幼年韦弗里与母亲之间频繁发生冲 突:母亲认为女儿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女儿的 成就自然能够成为母亲的骄傲;而这对于在美 国长大的,受到个人主义等观念影响的女儿来 说有些难堪,因为她认为自己的成长不应被母 亲过多干涉。
母女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人的品性”与 “环境”之间的冲突。“人具有双重的伦理身 份,一种是与生俱来建立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 的伦理身份,另一种则是后天在社会上不断建 立起来的身份”,韦弗里与母亲的冲突与和解 体现了女儿在伦理身份上的选择和重构(谭恩 美,2017)。在这一章节中,故事是由女儿韦 弗里观察和讲述的,但视角与声音存在时间差 异。这种身份相同、时间不同的叙事手法为现 实读者提供了解读的基础,既为情节发展提供 了动力,也为故事中的多个情节建立了联系。
其次,叙述者与观察者身份不一致。在 叙事学中,根据叙述者介入的程度,叙述者可 以介入叙事,也可以退出叙事,叙述者介入的 程度与叙述声音的强弱成正比。在语法上, 第二人称“你”则指说话的对象,也就是受叙 者;第三人称指话语涉及的人物或事物,是叙 述的客体。在《罗丝 ·许 ·乔丹:一半一半》 章节中,女儿罗丝的婚姻出现了危机,然而, 母亲却要女儿坚守自己的婚姻,努力挽救。在 这段故事中,女儿料想母亲的态度是“那你必 须挽回它”和“不可能”。女儿罗丝对婚姻的 态度是借助母亲来体现的,因此可以推断叙述视角是母亲的,但声音是女儿的。在另一章节 中,丽娜一直觉得母亲被某种恐怖的东西所控 制,“母亲说,那人已在这里住了好几千年, 十分邪恶与贪婪”(谭恩美,2017)。在这段 故事中,母亲的观察是借助女儿的叙述来感知 的,因此可以推断观察视角是母亲的,但声音 是女儿的。叙述者在转述和解释另一人物看到 和想到的东西,叙述和观察呈现分离的状态, 在此基础上,叙述者的叙述具有不同程度的可 信性。在母亲的照片上,丽娜看到了她“惊恐 不安”和“显出几分挫败的谦恭”的神态,这 些描述使读者认为叙述者的叙述具有很高的可 信性。在与母亲相处的日子里,丽娜“很快意 识到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母亲一直以来恐惧 的事不再是警示的语言,而的确成真了”,这 些描述却使读者对这段叙述的可信性产生了怀 疑(谭恩美,2017)。母亲在怀孕期间因被丈 夫抛弃而流产,后来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喜爱 的男人,这段经历导致母亲深受精神折磨,并 且会出现种种恐怖幻觉。然而,女儿丽娜的描 述越笃定,读者就越怀疑她叙述的可信性与判 断的合理性。
在这样一种失衡的母女关系中 ,母女 “彼此失散了……互相间见不到,听不到,互 不了解”(谭恩美, 2017)。由于母亲精神 状态的失常,女儿的情感常常得不到回应,幼 年丽娜不再寻求母亲的理解与支持,母女关系 变得淡漠。母女之间的故事是从幼年丽娜的视 角讲述的,充斥着许多光怪陆离的失真画面。 但成年后,丽娜逐渐改变了对母亲的态度,认 识到了母亲精神问题的根源,也承认了在精神 方面所得到的来自母亲的支持,因而坚信“这 种糟糕的生活终有一日会过去”(谭恩美, 2017 )。
随后,故事的声音是理性的,这说明丽 娜对母亲的感知不再停留于对母亲失常精神的 畏惧,更多的是对母亲痛苦经历的关切和对母 亲原生文化的思考。尽管母亲有其自身的精神问题,但其与女儿的互动也促进了女儿丽娜的 成长,岁月改变了母女关系,读者可以深深感 受到女儿丽娜对母亲从不理解到盲目追从到接 纳的变化过程。
2 作者视角与声音
叙事学理论认为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作 者与主要人物之间是相互区分但又密切联系 的。学者查特曼( 2016 )认为,隐含作者是 “叙事虚构作品本身内部的代理人,它引导着 对于它的任何阅读部分”;真实作者是创作叙 事作品的人,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而叙 述者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人物,是生活在故事虚 构的世界中的人。叙述者一旦被创作出来,就 脱离了作者,成为构成作品的因素(巴尔特, 1989)。因此,真实作者通常不会直接出现在 文本中,他是故事和文本的源头,为读者指引 方向。
作家谭恩美(2020)曾经回忆道:“哪些 时刻你能抹去,记忆并不允许你选择,还恼人 地执意保留最令人痛苦的时刻。记忆极为忠实 地记录了骇人的细节,日后还会借助仅与之依 稀相似的时刻,唤起你对这些细节的记忆。” 在谭恩美的成长过程中,她与母亲存在长期的 对立与冲突,直到了解了母亲的原生文化后, 她才真正理解并接纳了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家 族史使谭恩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华裔女性多 元化的身份构建产生了独特的感知力和洞察 力,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在《喜福会》中,最重要的叙述者是四 对母女,她们叙述了20世纪40年代及之前的故 事,曾在中国生活的母亲虽移民美国但仍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旧保持着中国身份; 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却在中西方双重文化的影 响下陷入身份困境。从现实角度来看,人物及 故事是虚构的,谭恩美借人物来讲述自己的成 长故事和见闻,一方面展现了自己的独特人生经历和所经历的双重文化融合与冲突;另一方 面通过两代华裔女性的自述表达出移民身份的 焦虑,从而引出文化冲突以及生命轮回的宏大 命题。
首先 ,作者视角与声音凌驾于被述世 界,作者是故事外的叙述者,借助文学作品介 入当下社会生活并建立作者观点。在《喜福 会》中,作者谭恩美通过其视角和声音展现了 第一代华裔女性以男权为主导的婚姻观的内涵 和变化。在婚姻中,“她的价值取决于丈夫饭 后打着饱嗝的满意程度”(谭恩美,2017 )。 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女 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着妻子、母亲的角色, 常常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来为家庭做贡献。谭恩 美小说中的母亲具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主导的婚 姻观。在第一代华裔女性许安梅的故事中,她 首先回忆了自己母亲的不幸婚姻,接着指出 “在过去,人们这么做,别无选择……但是现 在,他们可以做点什么了”,可见第一代华裔 女性萌生出了对男权主导婚姻的反抗意识(谭 恩美, 2017)。之后,叙事者讲述了一则中 国新闻——数千年来摧残庄稼的鸟类,终于激 起了农民的反抗,在鸟与人的博弈中,人最终 战胜了鸟,这是一种隐喻,作者谭恩美通过自 己叙述的声音和透过人物进行叙述的声音,始 终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描述第一代华裔女 性的困境与选择。
其次,作者视角与声音从虚构故事内跳 脱到读者生活的真实世界里,在《喜福会》 中,作者谭恩美用第三人称视角和声音讲述了 两代华裔女性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中国人有 中国式的观点,美国人有美国式的观点”,第 一代华裔女性出生、生长于20世纪初的中国, 深受望女成凤观念的影响,以自己心中的期望 来塑造女儿(谭恩美,2017)。第二代华裔女 性出生、生长在美国,华裔的身份使她们不仅 承受着来自传统式中国母亲的压制,还要面对 来自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其身份的认同向来受到华裔美国文学的关注。一方面,受母辈思 维的影响,她们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另一方 面,中国身份又使得她们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 社会。在《罗丝 ·许 ·乔丹:命里缺木》章节 中,女儿罗丝选择丈夫时,看中的是泰德的美 国身份,她希望通过婚姻来弱化自己的中国身 份。在与泰德母亲的见面中,罗丝被当成越南 人,后来又因为她的华裔背景而遭到泰德母亲 的反对。在《江林多:双面人》章节中,母亲 说:“哪怕你穿上他们的衣服,卸掉脸上的 妆,再把你精致的首饰都藏起来……他们只消 打量你走路的姿势,看看你的仪表神态就知道 了。”(谭恩美,2017)在真实的世界里,这 样的身份困境使华裔女性一直处于主流社会的 边缘地位,难以融入中美各自的伦理环境,叙 述与读者的已有经验产生共鸣。
最后,通过文本,作者谭恩美表达了被 述世界的世界观——母亲用中国的方式深爱着 女儿,含蓄有深沉:“很久以来,这个女人都 想把那根天鹅羽毛交给女儿,并告诉她:这根 羽毛看似一文不值,却来自遥远的故土,承载 着我的一片美意。”(谭恩美,2017)在中国 文化中,鹅毛是象征深情厚谊的礼物,隐喻手 法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 解读和建构。作者视角与声音能够帮助读者了 解作品中人物所未表达出来的心路历程,使读 者更加清晰地理解故事的情境和背景,从而增 加文本的可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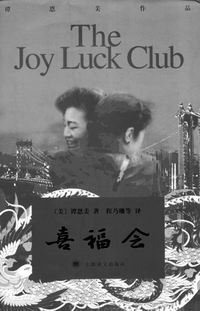
3 结语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代表作之一,也 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人物型作品,通过四对母女 讲述的16段故事,展现了两代华裔女性的困境 和选择。在人物视角与声音中,叙述者是女 儿和母亲,小说巧妙地运用视角与声音的一致 与差异,描述了一个个自我意识萌生与变化的 故事。小说表面是交代母亲移民前的故事和女儿童年以及成年后的故事,实则是对华裔女性 思想的白描——两代华裔女性对创伤的回忆和 对自我身份的探索,这些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基 调。在作者视角与声音中,叙述者作为观察者 处于故事之外,采用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母女之 间的隔阂与融洽,从中美文化的差异和母辈的 原生文化中探究母女隔阂的原因,找寻母女关 系融洽的方式。综上所述,小说中人物、作 者和叙述者相互交织,多层多角度表现了在 “离”与“闹”之间体现母女关系的“和”与 “爱”的审美取向。
参考文献
[1] 巴尔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C]//张寅德. 叙述 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 段雪菲. 浅析《喜福会》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38(3):141-143.
[3]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 卢杨. 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方法与案例[M]. 北 京:华文出版社,2021.
[5] 谭恩美. 喜福会[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17.
[6] 谭恩美. 往昔之始:谭恩美自传[M]. 李军,章力,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7] 查特曼. 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的叙事修辞学[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 邹建军. “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 中的伦理思想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