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早期英译与传播特征探析论文
2024-05-16 09:12:12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中国农学典籍《农政全书》早期外译始于18世纪初,并在19世纪和当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但译本的对比分析研究几乎阙如。本文全面系统评述近代英文期刊、《中华帝国全志》《中国科技术学史》在英语世界中译介《农政全书》的路径和特征,选取《中国杂志》节译《农政全书》的新语料进行分析,阐述农学术语的翻译策略与特色,以期为当代农业著作外译及其研究途径带来些许启发。
[摘要]中国农学典籍《农政全书》早期外译始于18世纪初,并在19世纪和当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但译本的对比分析研究几乎阙如。本文全面系统评述近代英文期刊、《中华帝国全志》《中国科技术学史》在英语世界中译介《农政全书》的路径和特征,选取《中国杂志》节译《农政全书》的新语料进行分析,阐述农学术语的翻译策略与特色,以期为当代农业著作外译及其研究途径带来些许启发。
[关键词]《农政全书》;农学术语;翻译策略
《农政全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农学巨著,对我国的农业耕作、土地开垦、水利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农政全书》的编著者为明朝人徐光启(1562—1633),该书于1636年由陈子龙根据徐光启的遗稿整理而成,全书有60卷,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大类,介绍中外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
根据潘吉星(1984)的研究,17世纪中叶,《农政全书》已传至日本,1696年,东京出版10卷《农政全书》,18世纪《农政全书》传到朝鲜和欧洲。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该书刊载的《蚕桑》在欧洲广为传播,被转译为法文、俄文、英文、德文等语言。目前对《农政全书》译本开展汉英对比分析的研究几乎阙如。
本文旨在归纳《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中译介的概貌,并以《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刊载的《制丝栽桑阐述》为汉英对比分析对象,分析《农政全书》英译及农学术语英译的特色。
1《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
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的法文本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但没有署名译者。其中,《中华帝国全志》英译版的第353—363页的内容以“Of the Silk Manufacture”和“Of the Silk-Worms in China”为题,并说明了这些内容是摘自一部中国古书,用于教会人们养蚕方法,以产出更多上等蚕丝(Extract of old Chinese book,which teaches how to rear and feed silk-worms,so as to have plenty of the best silk.)。该部分对《农政全书》中的蚕桑和制丝内容进行了译介。
《中华帝国全志》这部长达3000页的著作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地理和自上古至清代的历史,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古代典籍、教育、宗教、道德和医药,以及当时中国的周边地区。作者“充满了对中国的景仰之情,把中国描述成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疆域最广袤、风景最美丽的国度之一”,整部著作成为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知识体系的最重要的文献,它推动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高涨(严建强,2002:94—95)。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5月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创办,于1851年12月停刊。该刊最初在广州印刷,1836年搬至澳门印刷,1844年10月在香港印刷,1845年7月再次搬回至广州。《中国丛报》在其发行的20年间,译介的内容涵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商业、对外贸易、自然气候、风土人情、宗教等领域(曾文雄等,2020)。
《中国丛报》在1834年7月第7期和1837年3月第3期分别译介了中国农业(Agriculture in China),论及中国农业的古老特性、农耕规律、发展障碍、土地、气温、灌溉和施肥、畜牧业工具等,以及中国农具的使用说明,包括犁、耙、锄、耙、钩、连枷和水轮等农具;在1849年6月第6期译介了晚清蚕桑古籍《蚕桑合编》。关于《农政全书》的译介,《中国丛报》在1849年9月第9期译介了《农政全书》的“木棉种植”(Direc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
在译介《农政全书》之前,译者做出说明:“这本书是中国人关于农业的最全面的著作之一。该书有六十章,每一章都论述一个特定的主题,并用图画加以说明。作者是明代的徐光启,住在上海。此处所选用的整个章节均引述自书籍。”(Shaw,1849)译文介绍了王祯的《农桑通诀》、玄扈(徐光启的号)的评论、《便民图纂》中有关种植的观点、掌管种植的张五典(Chang Wua-tien)的观点,以及中国中部、山西、陕西、山东、淮南、福建、广东等地的吉贝(即木棉)树种植的情况。译文还提到,广州当时的夷人(外国人)无法得到生丝而被迫用棉制衣,一些番人(外国人)说,制衣所用的棉花其实来自木棉(Shaw,1849)。总体而言,《中国丛报》就《农政全书》中有关木棉种植的内容做了较详细的译介。
近代英文月刊《中日丛报》(Th 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History and Art,Relating to Eastern Asia)由英国汉学家萨默斯(James Summers)创办和主编,在英国伦敦出版。该英文期刊从1863年7月至1865年共出版了29期,共三卷。1864年12月《中日丛报》(第2卷第17期)刊载了题为“Cotton Cultivation in Shanghai”的译文,1865年1月的《中日丛报》(第3卷第18期)也刊载了题为“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 in Shanghai”的译文。
经过对比发现,这两篇译文基本一致,但译文的标题略有改动。另外,与《中国丛报》的译文相比,《中日丛报》刊载的《农政全书》译文的最后一段被删去了。这与《中日丛报》的办刊宗旨有关,换言之,该刊会转引某期刊的重要内容。根据尹文涓(2020)的研究,《中国丛报》与《中日丛报》在创刊宗旨、内容体例等方面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但也存在不同之处。《中日丛报》在“创刊词”中声称《中国丛报》是其前身,其是《中国丛报》的延续(尹文涓,2020)。
《中国杂志》(Chinese Miscellany,1845—1850)由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主编,上海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 Press)出版,旨在介绍中国知识体系,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制造业、贸易、风俗等内容。《中国杂志》共出版了四卷,其中第三卷刊载了《农政全书》的节译,名为《制丝栽桑阐述》(“Dissertation on the Silk-manufac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ulberry”),翻译的内容涉及《杂五行书》《齐民要术》《土农必用》《务本新书》《博闻录》《韩氏直说》《四时类要》《农桑直说》等内容,而且有桑事图谱介绍,并附上16张图,包括火仓、蚕箔、蚕筐、蚕盘、蚕架蚕网、团簇、马头簇、桑网等制作工具的图表。
根据卢嘉锡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译本中的序言,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拟出7卷共34册。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第二册《农业》介绍了《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等著作(Metailie et al.,1986)。Metailie et al.(1986)在书中的第64至70页介绍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描述了该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及历史意义。Metailie et al.(1986)指出,《农政全书》的成书动因是徐光启意识到明代末期中国存在的基本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以图表勾勒了《农政全书》的内容:Nung Pen(农本)、Thien Chih(田制)、Nung Shih(农事)、Shui Li(水利)、Thai Hsi Shui Fa(泰西水法)、Nung Chi Thu Phu(农器图谱)、Shu I(树艺)、Tshan Sang Kuang Lei(蚕桑广类)、Chung Chih(种植)、Mu Yang(牧养)、Chih Tsao(制造)、Huang Cheng(荒政)、Chiu Huang Pen Tshao(救荒本草)。Metailie et al.(1986)说明了《农政全书》这部巨著的核心思想与地位:《农政全书》有70万字,辑录了农业文献229种,并加以评注,着力农业管理,其“创新与优势在于其注重农业发展中管理的作用”。至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中传播的概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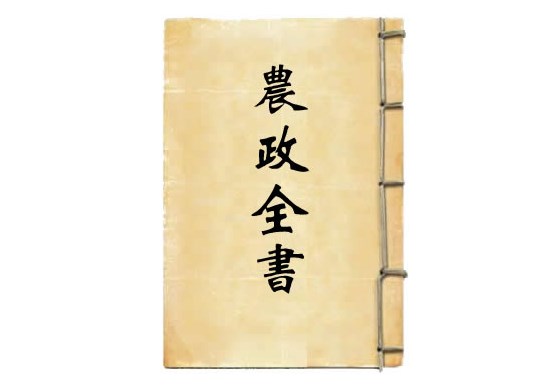
2《农政全书》英译的特色
由上述内容可知,早期《农政全书》的译介与传播主要是通过英文书籍或英文期刊以介绍性、节译等方式推介给欧美等地的读者。下文以刊载在《中国杂志》上的《农政全书》为案例,开展汉英对比分析,探索《农政全书》的翻译特征。
例1:黄省曾曰:蚕之性,喜静而恶喧,故宜静室。喜暖而恶湿,故宜版室。室静,可以辟人声之喧闹;室密,可以辟南风之吹袭;室版,可以辟地气之蒸郁。(徐光启,1930:372)
译文:Hwang-sang-tsang says,“Silk-worms naturally love quietness and abhor noise;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reared in a quiet house:they like to be kept warm and dislike damp,hence they should be reared in a house with a boarded floor.A quite house will of course be free from the noise of men;a close apartment will keep out the blasts of the southern wind;and a boarded floor will prevent the rising of damp exhalations from the ground.”(许海燕,2010:591)
基于观察及汉英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杂志》上刊载的《农政全书》译文基本上忠实于原文。例如,有关“黄省曾”观点的翻译,译文很好地保留了原义。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根据情况调整语序或句式,根据语义进行断句、合句等。不过,译文中也存在增删、误译或术语翻译不统一的问题。例如,在术语翻译方面,“士农必用”这一术语的译名存在不统一现象,有的地方用“音译+脚注”的翻译方式处理:Sze-nung-peih-yung(脚注:important rules for scholars and agriculturists),有的地方用“Agriculturist’s Manual”的意译方式处理(许海燕,2010:594)。
与此类似,“韩氏直说”中的“直说”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翻译,如Plain Account、Plain Directions、Plain Statement等。这种多变的、术语表达不一致的方式,容易使读者混淆。
经过对比分析发现,《农政全书》中有关术语(包括农学术语)的翻译主要采用以下翻译策略:
(1)“零翻译+音译”或“原术语+音译”。这个策略的特征表现为:译者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术语表达,故而在保留原术语的基础上,附上读音,有时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其特征进行一定解释。例如“蒲母草”,其译文为Poo-moo-tsaou(许海燕,2010:646)。
(2)“零翻译+具体化特征”。这个策略的特征表现为:译者保留原术语不译,换言之,对原术语实施零翻译,然后对这个术语的功能进行意译补充。采用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译者很难在译文中找到与原文相对应的表达,进而对这个术语的功能进行解释。例如,针对“插接”“劈接”“搭接”“换接”等术语的翻译,译者在保留这些术语的同时,用graft说明这些术语的功能。例如,“插接”的译文为“插接(grafts in which the cion is inserted)”,译者在翻译时仅对原文的术语功能进行阐述(许海燕,2010:646)。
(3)“零翻译+音译+意译”。这个策略的特征表现为:译者保留原文的术语不译,接着对术语进行音译和意译。例如,“齐民要术”的译文为“齐民要术(Tse-min-yaou-shuh,Important Hin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许海燕,2010:594)。
(4)“零翻译+意译”。这个策略的特征表现为:译者保留原术语不译,即零翻译,并配以英文释义。例如,“秋蚕”的译文为“秋蚕(autumn worm)”(许海燕,2010:628)。
3结语
18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农业科学巨著产生浓厚兴趣,《农政全书》也正是在“中学西传”的浪潮中以不同的载体呈现在西方世界读者的面前。《农政全书》属于科学典籍且内容庞杂,虽然西方汉学家在力量范围之内开展了部分译介,但至今仍未有全译本。本文基于现有的历史语料,剖析《农政全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历程,并用《中国杂志》中新的语料论证农学经典《农政全书》的翻译特征,开拓性地描述农学术语的英译策略,以期给《农政全书》等中国农学典籍的外译及其研究带来些许启发。
参考文献
[1]DU HALDE J B.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l)of those countries[M].London:T.Gardner,1738.
[2]MEDHURST W H.Dissertation on the silk-manufac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ulberry[Z].Shanghai:The Mission Press,1849.
[3]METAILIE G,BRAY F.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I:agriculture[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4]SHAW C.Direc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J].Chinese repository,1849,18(9):449-469.
[5]SUMMERS J.Cotton cultivation in Shanghai[J].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1864,2(17):199-209.
[6]SUMMERS J.The cultivation of cotton in Shanghai[J].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1865,3(18):17-24.
[7]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2):177-188.
[8]徐光启.农政全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9]许海燕.稀见近代英文期刊汇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0]严建强.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11]尹文涓.从《中日丛报》与《中国丛报》之渊源看早期英美汉学与日本学的伴生现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33-45.
[12]曾文雄,刘青.《中国丛报》与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J].现代语文,2020(2):6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