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语言学视角下语言习得研究的一点思考— 以一语及二语习得为例论文
2024-01-30 15:07:22 来源: 作者:hemenglin
摘要:语言习得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各学派尚未达成共识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生物语言学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摘 要:语言习得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各学派尚未达成共识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生物语言学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这一综合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为解决语言习得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 。在此视角下,学者们有望将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相互结合,来解码人类语言习得的终 极奥秘 。文章通过回顾语言习得( 包括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进程,厘清语言习得的最新发展脉 络,结合生物语言学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思考,以期为二语学习者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生物语言学;一语习得;二语习得
Abstract: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 the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 but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Since the 1990s , as the research on biolinguistics has gradually advanced , it has provided new ide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linguis⁃ tics , scholars are expected to combine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biology , linguistics , and psychology with each other to decode the ultimate mystery of huma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 including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ut for⁃ward certain thoughts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in biolinguistics ,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Key words: biolinguistics;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一、引言
1974 年,在首届语言与生物学交叉学科会议 上,来自语言学界和生物学界的专家学者对语言与 大脑的关系进行了研讨,内容涉及人类语言的起源 与变异、语言能力的习得及语言变异等很多方面。 随着生物语言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对语言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 究,目前,生物语言学已成为 一 项 重 要 的 跨 学 科 研究。
在传统的语言学领域,语言习得一直是众多学 者的研究重点,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客观证据,各 学派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分歧 。基于此,文章从当代 生物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出发,重温该领域的经典文 献,旨在厘清语言习得的最新发展脉络,并提出自 己的一点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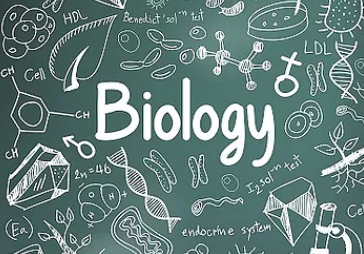
二、传统语言习得观概述
早在 17、18 世纪,语言习得理论就摇摆于洛克 的“ 白板说”和柏拉图(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天赋理念”二者之间,前者认为外在因素是语言习得的 关键( 即“后天派”),而后者则强调语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即“先天派”),二者之争也就是“ 先天”与“后天”之争( Nature -Nurture debate ) , 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莱纳博茨,则提出了“ 大理石 花纹说”( 即“相互作用派”)。 目前,“先天派”在学 术界被普遍认为是主流学派,生物语言学也正是该 派的主要研究方向。
(一)“后天派”理论学说
“ 后天派”认为,加强外部环境对语言学习者的刺激是提高语言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华生提出的“刺激-反应”学说认为,人类语言的习得主要是后天环境刺激之后产生的结果 。但这一理论片面 夸大了环境和教育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忽视 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以及促进心理发展的 内部动因 。布鲁姆菲尔德和斯金纳提出的行为主 义(经验主义理论)认为,儿童通过环境调节和强化 来习得语言,比如其家庭成员、同龄人、教师甚至整 个社会,语言习得是模仿、实践、成功反馈和习惯养 成的结果。
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后天派”认为环境因素 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经历了从机械模仿说到选择 性模拟说,从强化说到中介说的修正与完善 。这对 后来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先天派”理论学说
“ 先天派”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习得装置(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 LAD) 存在于 每个人的大脑中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认 为,人类大脑中存在一种语言习得装置,人类由此 能够轻松习得母语,即一次参数设置的过程 。他提 出的心智主义理论认为,语言主要是由通用语法的 深层和表层结构组成 。之后,莱纳伯格提出了“ 自 然成熟说”,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人体思维机制形成 的产物,在人脑机制的发展到达语言的阶段后,如 果受得相应的环境刺激,便能够使潜在的语言功能 形态转变成真实的话语功能,从而获得语言功能。 后来,莱纳伯格从临床角度基本证实了“关键期假 设”,并提出大脑的单侧化也是在关键期内完成的。
“ 先天派”揭示了人类语言的天赋性,但该学派 中的部分观点是思辨的产物,如人脑中是否存在乔 氏所言的 LAD , 依然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 。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生物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 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先天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乔姆斯基在之后提出了“语言官能”的概念,进 一步推动了该学派在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
(三)“相互作用派”理论学说
以皮亚杰的“认知论”为代表的“相互作用派 ” 认为,语言习得是个体内部构建与外部环境影响相 互作用的结果 。他采用临床研究的方式,揭示了儿 童认知发展的一些规律:顺序性、阶段性、主动性、 内发性等。
皮亚杰认为一切知识系统,从作用机理上讲, 都是同化和顺化的系统;从功能机理上分析,则是 人类主体认知构造的自我内化形成与外化应用的 系统,这些都是构成人类认知结构的基本要素,将 所有因素结合起来造就了人类认识的整合能力。 但是,“相互作用派”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儿童习得母 语的过程,并不完全适用于青少年和成人的二语习 得过程。

三、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习得观
生物语言学为阐释语言习得过程提供了跨学 科的视角 。根据生物语言学的研究,内置的生物系 统触发了语言习得的过程,从而建立了个人的语言 身份 。这个过程并不是静态的,也不仅仅局限于生 物学或语言学,而是随着系统功能的经验或环境输 入的变化而变化 。语言习得过程即是设定参数的 过程,儿童习得母语是第一次设定语言参数,而二 语习得则会进行语言参数的二次设定。
(一)语言官能
[1]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官能存在特定的方位性, 产生于大脑特定区域 。与人类的大多器官( 如心 脏)不同,语言功能不仅具有保持自身再生的能力, 还具有各种功能子系统,包含语法、语义、词法、词 库、音系等。
[2] 乔姆斯基等人强调语言是运算表现系统,并 将语言官能区分为两部分:第 一 是内在的运算系 统,这部分组成了语言知识,其内容是语言生物学 中的核心问题,它是一个单独的认知系统,存储语 言的语音、意义和信息结构,被称为狭义语言官能; 第二是语言应用系统( 但仍然内在于心智/大脑之 中),包括感觉运动系统 SM 和概念意向系统 CI , 该 系统涉及和提取认知系统的信息,语言应用系统与前述运算系统一起又被称为广义语言官能。
(二)生物基础及临床证据
临床证据能够为“语言官能”中的观点做出解 释 。人脑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完善的物质,是上 层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由左右半球组成,每个 半球表面的灰质层称为大脑皮层,大脑皮层配备了 最发达的中枢,负责身体的所有功能活动,语言功 能就是其中之一 。人们普遍认为大脑的言语区主 要位于左半球,也叫优势半球,左半球不仅控制右 躯干,还控制言语中枢,所以 90% 有语言能力的正 常人都是右撇子。
对失语症的临床解剖研究表明,如果脑部某些 部位损害出现疾病,就会引起语言障碍 。利用核磁 共振、脑造影技术可以发现,如果布洛卡三角区受 伤,就可能产生活动失语症,虽然患者能够读懂文 字和听懂与他人对话,但本身并不能说话,也无法 用语字进行口头表述 。处于下颞叶的韦尼克区域 主要承担着言语的感知和对事物的命名等功能,此 区域损害会产生感觉型失语症,患者认知困难较明 显,尽管语音清晰,语调准确,但却没有实质意思, 往往答非所问 。损害额前回后部和中央上回手部 代表区的地方,患者虽能听到他人的交谈,读懂文 章,自己也能说话,但不能写字,但患者手指的其他 活动却不受干扰,这种现象叫做失写症 。优势侧角 回的疾病,患者读不开字音,或不明其含义,像是文 盲,这种现象就叫做失读症 。尽管学术界就不同的 语言中枢管理各自的功能有着不同的认识,但临床 解剖学的证据表明,不同功能区并不是彼此独立, 而是由相应的中枢神经将彼此相互连接起来,构成 一种密切无间的语言官能系统。
此外,生物遗传学 FOXP2 语言基因的发现,进 一步证实了语言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联系 。当语言 基因发生突变时,患者会出现以时态、性别和数量 为特征的语法错误 。对 FXOP2 的进化追溯揭示了 话语的生物学机理对人体进化的意义,研究者曾针 对一对九岁的同卵双生儿进行追踪研究,他们的智 力和性格都很相似,在发音方面都不存在困难,但 是却有阅读障碍,而他们的父母在十年前也出现类 似的语法异常现象 。 由于同卵双生子具有相同的 基因组和遗传过程,他们先天的句法缺陷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双生子的共性遗传问题。
(三)语言习得的参数差异
生物语言学为语言习得参数差异提供了新的 证据 。在生物语言学视角下,语言习得参数差异主 要体现如下。
1 . 一语与二语习得的差异
一语习得过程中的统一性与自发性,与二语习 得过程存在广泛差异 。一语习得中,儿童在准确选 择语言参数之前,其语言可能会显示出和“标准语 ” 不同的特征,如果儿童“ 自创的语法”与其实际接触 的语句出现不同时,就必须重新设置出不同的语句 参数 。参数的重新设置往往是以足够量的“标准 ” 输入或外界干预( 比如家长或老师的刻意纠错)为 基础,只有这样,儿童才能意识到自身的语言错误, 从而调整自己的语言输出。
二语习得必须考虑到普遍语法的“参数重置 ” 和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影响程度 。如果我 们将母语学习与二语习得的初始状态做一个对比, 会发现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母语学习的整 个过程中,儿童的理解能力与口语能力尚处在不完 善的发展阶段,并且母语词汇习得过程还伴随着社 会情感、生理学、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改变,而 成年人的二语习得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大体达成,是 在熟悉母语词汇后才进行的。[3] 儿童大脑中普遍语 法的基本参数处于开放状态,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 通用语法是在母语学习环境的影响下被形式化。 如果说儿童初始习得母语只是通用语言,那么成人 初始学习外语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已有获得 发展的能力、已有的基本基础和普遍语法。
研究发现,在普遍语法内部,母语和二语之间 会相互干扰和影响,所以,在二语交流过程中,许多 成年外语学习者会出现语码转换的特征。
2. 年龄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在二语学习的过程中,年龄因素会影响大脑右 半球的语言处理过程,研究表明,年龄越小,大脑右 半球参与越少,而年龄越大则参与越多。
莱纳伯格认为,幼儿的语言学习在青春期前, 从两岁到青春期前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因为 这段时期是脑部偏侧化发育黄金时期,如果错过了 这一关键期,语言学习的过程也就不太容易了 。所 以,如果二语习得主要发生在这一 时期的末期甚至 之后,那么其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而且,随着年纪增加,二语习得的进程中更容易出现语言“石化”的 现象。
3. 性别差异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4] 生物语言学为性别差异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也提供了新的证据 。语言中枢主要靠左半球,女性 左半球发育较快,有助于语言能力的早期发育 。此 外,在语言发展方面,优势半球的形成与胼胝体有 关 。胼胝体是一条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白质带,男 性和女性的胼胝体形状不同,女性胼胝体的形状多 为球形,男性则多为管状,形状上的差异意味着女 性胼胝体比男性更大更重,且女性的胼胝体发育较 早,加之男性和女性使用大脑的方式不同,女性的 左右半球都参与语言处理,男性大脑分工明确,倾 向于使用右半球来对语言进行加工处理 。因此,在 语言习得方面,女性较男性具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 在语言水平方面的差距会日益缩小,二者最后的状 态会实现基本趋同,这表明男性在语言习得方面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
四、生物语言学视角下对二语者语言习得的建议
综合基因、神经功能、表观遗传学和有利环境 等因素考虑,从生物语言学的视角,对二语习得者 提出如下建议。
二语习得的过程中,普遍语法会被激活 。在这 个过程中,一 方面是在刺激普遍语法二次发挥作 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普遍语法中的参数进行二次设 定 。这些参数的值一旦得到设定,整个语言系统就 可以开始运作 。所以,参数设定的方式显得格外重 要,这也是目标语言输入的过程 。儿童在习得母语 的过程中,通常会以语义输入为先导,形式输入为 辅助,这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语义 激活语法的过程 。因此,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二 语习得者或许可以模仿一语习得的路径,以足够语 义输入为基础,依靠普遍语法进行二次参数设定, 达到习得第二种语言的目标。
文章建议对二语理解能力的培养模式,首先要 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入,包括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声音形式是通过与人交流,使语言能够与大脑建立 思维关系,或者说是让外界环境因素来参数化大 脑,抑或让二语习得者有意识地接触目标语文化, 特别是目标语国家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来 帮助其内在语言装置进行二次参数化;文字形式或 者书面形式的语言材料输入,则是让习得者进行大 量文章阅读,且有意识地记忆语言材料,以此完成 大脑中普遍语法参数的二次设置。
五、结语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 传统的语言习得理论提供了更多的科学依据 。对 语言的生物学特性的讨论,有助于研究者明确语言 习得的规律 。语言基因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证 实了 Chomsky 的语言习得内在机制,也为控制语言 机制的脑科学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和 二语习得中的“僵化”现象,提供了生物学领域的 证据。
生物语言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已经日益得到理 论语言学界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相 信学者们会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前人语言 习得的辩证思想,帮助人们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二语 习得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推动人类语言学向 更高阶段发展。
参考文献:
[ 1 ] Chomsky N.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 De Houser A. Parental language input patterns and children's bilingual use [ J] .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007(28) :411 -424.
[3] Gentner D , Namy L L. Analogical processes in language learning[ J] . C urrent Directions in P sycho⁃logical Science ,2016 , 15(6) :297-301 .
[4] Green M , Piel J.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 men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 2nd ed. ) [ M] . NewYork : Routledge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