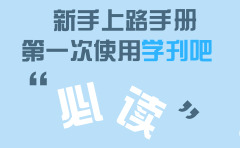《接骨师之女》的沉默书写论文
2024-06-11 11:59:04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接骨师之女》是著名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经典之作。小说中,母亲茹灵对自己的故国经历保持沉默,更囿于移民身份而无法讲述创伤性的记忆。女儿露丝作为第二代美国华裔,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保持缄默,从幼年到中年,她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籍籍无名。她努力维系家庭关系,却从未被美国家庭真正接受。从沉默到发声的转变标志着个体性的回归和情感的连接。沟通成为化解彼此隔阂、增进理解的有效途径。
[摘要]《接骨师之女》是著名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经典之作。小说中,母亲茹灵对自己的故国经历保持沉默,更囿于移民身份而无法讲述创伤性的记忆。女儿露丝作为第二代美国华裔,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保持缄默,从幼年到中年,她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籍籍无名。她努力维系家庭关系,却从未被美国家庭真正接受。从沉默到发声的转变标志着个体性的回归和情感的连接。沟通成为化解彼此隔阂、增进理解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接骨师之女》,谭恩美,沉默叙事,记忆
1研究背景
《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又一部探讨华裔女性的主体构建和成长的作品。跨种族、跨文化对于主体建构的影响是该小说的显著特征。然而,从个体的话语权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曾陷入沉默、无法言说的困境之中。故国创伤带来的苦痛和游离于两种相异文化之外的阈限性身份成为她们沉默的理由。对于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华裔女性而言,她们的沉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2不愿言说:故国的创伤与新居的压抑
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经历,成为埋在茹灵心中的创伤性记忆。她把充满悲伤和绝望的经历藏在了她内心最安全、最安静的角落里。这些记忆以沉默的形式存在,成为她避免揭开伤疤的手段,但这不过是一种欺骗性的自我保护。茹灵其实还记得她的过去,只是刻意地将它们埋藏起来,并试图以这种方式避免再次受到创伤。记忆也是沉默的一种形式,它“不言说、不表达,与声音无关。只有深入理解被沉默所遮蔽的无声无言之物,分析那些尚未被呈现、无法被呈现却又必须呈现的东西,穿越沉默的领地,才能抵达记忆深处”(赵静蓉,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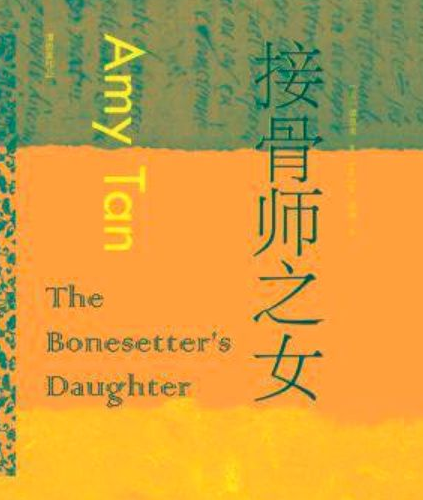
茹灵与母亲宝姨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宝姨与刘家最小的儿子相恋,却在婚礼当天由于张家的搅局同时失去了父亲和丈夫。但是刘家人为了她腹中尚未出生的孩子,便让她以保姆的身份继续留在刘家。为了女儿,宝姨只能以特殊的身份陪伴在她的身边。然而,茹灵在心底只把宝姨当成自己的保姆,一直有意识地反抗她。但是宝姨对她的照顾仍然无微不至,直到那天茹灵决定嫁给张家的儿子,这件事成为茹灵和宝姨之间冲突的高潮,也是茹灵创伤的开始。宝姨原本幸福的家庭生活被张家所毁,因此她心中对张家充满了仇恨。茹灵的那句“就为了摆脱你,我也要嫁过去”成了压垮宝姨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茹灵看到了母亲留给她的文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母亲的死亡让她懊悔不已。茹灵疯狂地寻找母亲的尸体,但始终无法找到,“一部分的她,永远遗失在了穷途末路”,那里正是宝姨的尸骨最后被抛洒的地方(谭恩美,2017:184)。
茹灵很少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即使提到,她也会用那种漠不关心的语气搪塞过去。茹灵对母亲的内疚体现在对宝姨鬼魂的恐惧中,她认为这是一个加在她身上的诅咒,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她。茹灵对于母亲的死抱有深切的愧意,然而她没有正视过这件事,而是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以停顿、遗漏、轻描淡写的形式出现”(Dambska,2016)。宝姨永远也不可能出现了,茹灵只能一遍遍地在梦中呼唤着她的名字。对母亲的愧疚一直留在茹灵心中,成为她不可言说之痛。
为了躲避战争,茹灵通过孤儿院移居美国。但是移民并没有让茹灵在新的环境中摆脱梦魇,反而给她贴上了华裔美国人的标签,遏制了她的自由表达。早期的美国华裔女性“就是第三世界中无权的贫困妇女,并且是一个‘无形无声’的群体”(斯皮瓦克,2007)。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茹灵难以用新的语言进行表达,更承受着美国文化作为主流权力文化对故国文化的完全压制。在美国生活多年,茹灵还是不擅长使用英语,很多时候都需要女儿帮她翻译。因此,她总是陷入沟通困境。在日常生活方面,露丝尚能帮助母亲翻译,而茹灵心中的所思所想又如何跨越语言的壁垒传递出去呢?(林钰婷,2012)此外,露丝的继女儿们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以茹灵为代表的他者文化进行着不对等的想象性认知,她们十分反感露丝和茹灵用中文对话,认为这“像间谍一样,很不礼貌”(谭恩美,2017)。
一直以来,东方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西方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对东方采取俯视的文化态度,而东方被迫成为他者,处于失语的状态。作为华裔美国女性,茹灵的沉默“由于女性和少数民族的双重边缘身份而更加根深蒂固”(蒲若茜等,2016)。于茹灵而言,美国这片土地是一块“没有鬼魂也没有毒咒的大陆”。逃离故国伤痛的第一代移民在远渡重洋、开启新生活的时候,身上仍然背负着无法向别人启齿的秘密。一旦这些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他们就面临着成为社会局外人的风险。
3无法言说:他者的压制与内化的沉默
由于故国的伤痛和秘密,以茹灵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不愿说出自己的故事,而以露丝为代表的第二代移民的沉默则源自社会对其主体性的忽视。一方面,作为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她被贴上了温顺、含蓄的标签;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她的生活和选择受到男性的支配。
露丝的沉默是结构式的,她在美国社会中成长,虽然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她的脑海中博弈,但是她所生活的环境要求她成为符合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模范少数族裔。露丝小时候就非常“讨厌茹灵明知别人不能明白她的私房话,还特意当着别人的面讲中文”(谭恩美,2017)。在学校,为了故意反抗茹灵的要求,露丝赌气沿着滑梯冲下去,摔成了骨折。露丝还在青春期偷偷做了许多母亲禁止的事情。“这样的成长看似完美,潜伏其后的却是他者文化想象在叙事之中的延宕,甚至遮蔽了美国华裔女性灵魂深处的挣扎和内心自省的声音,导致华裔女性的主体性被悬搁。”(黄新辉,2019)尽管露丝在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中长大,但她仍然被看作是社会中的他者,无法被美国社会真正接受。露丝活得小心翼翼,她在融入社会的同时也压抑了自己作为主体的自由,无法将自己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对于像露丝一样拥有双重身份的少数族裔而言,他们既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中国,而是处在两个异质文化的阈限处,无法在任意一方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作为亚裔,露丝在男友亚特家庭中更加不被重视。米莉安是亚特的前妻,亚特的父母“非常钟爱这位前儿媳”,可露丝从没有在亚特的父母身上感受过同样的热情和爱意。亚特的父母没有认真对待亚特和露丝之间的感情,也从未将她视为家庭的一分子,只把露丝当作是亚特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别人介绍露丝。在日常生活中,露丝、亚特和亚特的女儿挤在极小的房子里,连浴室都要写明时间安排,标记每一刻钟轮到谁使用卫生间,而露丝总是“把自己排在了最后一位”。由于每个人都会拖延几分钟,露丝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这种利他性的家庭关系中,露丝渐渐把自己放在最末位。当母亲茹灵的阿尔茨海默症影响了她的生活,将家里搞得一团乱时,露丝向亚特求助,却没有得到回应。她打电话给正在夏威夷的亚特,没有人接,“她能想象出亚特无忧无虑地躺在沙滩上,把所有麻烦问题抛在脑后的样子”(谭恩美,2017)。露丝与亚特的家庭关系并没有增加她作为主体的幸福和快乐,反而让她陷入了自我牺牲的无奈境地,成为家庭生活的附属客体。
4从沉默到发声:主体性回归与情感联结
母亲的病让露丝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回忆起年轻时与母亲的矛盾,露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与莽撞。处于青春期的露丝很容易受到当时美国社会风气的影响,但茹灵没有与露丝进行沟通,而是直接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露丝进行批判。露丝认为自己“有隐私权,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活着不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而茹灵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青春期孩子必经的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引导,她直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不早死掉算了。”最终,结束争吵的是茹灵,她“大喘了几口气,然后离开了露丝的房间。露丝起身使劲把门摔上”(谭恩美,2017)。
母女之间平等的沟通是缺失的,她们对自己内心的想法都保持沉默。在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收拾东西时,露丝发现了一份用毛笔端正写好的手稿。虽然露丝没法看懂全部的汉字,但这一次,露丝不再抗拒成为母亲的翻译,而是想要静下心来了解母亲的所思所想。为了照顾母亲,露丝决定搬去和茹灵同住。亚特也在这次的分居中意识到了自己对露丝的需要,他决定和露丝认真地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亚特提出要和茹灵共同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帮茹灵寻找合适的养老院。当亚特将露丝纳入未来的规划中时,露丝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重戒备”,开始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

一年级时,露丝任性地从滑梯上滑下,摔成了骨折。她发现,自己不说话反而能够吃到母亲一直禁止的汉堡包,于是继续装作无法说话,好让这神奇的魔力继续保持下去。为了与露丝交流,茹灵为她准备了一个沙盘,露丝可以用筷子在沙子上写字。然而,当露丝在沙盘中写下“小狗”时,茹灵则错把露丝想要只小狗的愿望当成了宝姨对她的爱称。茹灵一直认为宝姨的灵魂还飘在空中。而此时的露丝并不明白母亲对宝姨的感情,她使劲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仅是一个长发垂至脚跟的女人的形象。后来,露丝将在沙盘上写字当成跟母亲撒谎耍花样的手段。在得知母亲的身世和在中国的经历之前,生长在美国社会中的露丝无法理解母亲面对宝姨“鬼魂”时的紧张与虔诚。然而,面对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孤立无援的露丝来到了沙滩边,她觉得“沙滩就像一块巨大的写字板,一块干净的石板,仿佛邀请自己填满任何愿望,一切皆有可能实现”,但是此刻,“她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希望和决心。她以后再也不要编造答案了。她会诚心企求”(谭恩美,2017)。当露丝蹲下身,在海滩上写字时,她不再是游离在中国文化之外的他者,而是作为主体,对自己多元、跨种族的身份进行确认。
读完母亲的手稿,露丝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她知道了母亲的故事,也明白了母亲的心意。母亲茹灵只是想回到因为自己的任性而让宝姨伤心自杀的地方。正如茹灵将自己的故事用中文写下,露丝也决定用自己的笔触将这个故事写下来。写出过去的故事不仅是为了“把本该发生的故事、有可能发生的故事都写出来。写下的过去可以改变。过去无非是那些我们选择记住的事情”。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茹灵的故事,她也不必再独自承受愧疚带来的心理压力。
通过揭露伤疤,茹灵超越了被创伤压制的无言的自己,获得了自由。她仍然记得过去的事情,只是她记忆中的内容在悄然改变。她不再总是回忆那些悲伤的片段,而是选择记住那些充满爱的瞬间。揭开记忆的伤疤也许痛苦,但是这代表着不再逃避。感受彼时的痛苦,让沉默的记忆成为重新开始的力量。
5结语
在《接骨师之女》中,谭恩美讲述了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露丝对中国母亲茹灵从误解、发现到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从沉默到发声的转变。茹灵因为战争被迫移民美国,亲生母亲由于自己的任性而自杀、丈夫的离世成为她埋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创伤。异国的新环境并未能缓解她的痛苦,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其无法言说的困境。露丝作为第二代华裔,从童年开始便受到了西方文化对她声音的压制。在社会中,露丝籍籍无名。在与白人男友亚特的家庭关系中,她无足轻重,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然而,母女两人通过揭开伤疤,从回忆中汲取重新前行的力量。沟通不仅是化解彼此隔阂的力量,也是表达真实自我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DAMBSKA I.Silence as an Expression and as a Value[J].Knowledge,language and silence,2016(3):311-319.
[2]黄新辉.美国华裔女作家的成长叙事及主体建构的嬗变——以黄玉雪、汤亭亭、伍慧明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77-87.
[3]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林钰婷.历史的重量:《接骨师之女》的认同建构之途[J].东南学术,2012(4):251-256.
[5]蒲若茜,潘敏芳.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沉默”诗学探析[J].外国文学研究,2016(6):143-151.
[6]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张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7]赵静蓉.让沉默发声——记忆研究中的“沉默”及其表征[J].探索与争鸣,2023(1):135-14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