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人面桃花》的普世性与跨文化性论文
2024-05-15 09:36:43 来源: 作者:heting
摘要: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之下,文学的创作应当具备“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的特点。格非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鲜明的创作手法与思想特色,并结合自身多年来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思考与创作经验,在《人面桃花》的书写中体现了跨越中西方的叙事方式、思想内涵与哲理意义,其创作具有鲜明的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特征。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之下,文学的创作应当具备“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的特点。格非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鲜明的创作手法与思想特色,并结合自身多年来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思考与创作经验,在《人面桃花》的书写中体现了跨越中西方的叙事方式、思想内涵与哲理意义,其创作具有鲜明的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特征。
从世界主义的视角来看,具有成为世界文学潜力的作品应当在更加广阔的文学语境下有着“普世性”的意义和价值。所谓“普世性(universal)”,正如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所概括的,“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不同的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趋同,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普世性寓于差异性之中,正因为有了差异性,普世性才有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文学现象”逐渐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点。“跨文化(Transkulturalität)”概念的主要创始者是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跨文化”这个大概念,有利于化解“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深入考察那些重似叠合和交织的文学作品。
从“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的维度来看,中国文学的发展必然是朝向世界敞开的,中国文学应当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精神且符合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的哲理和原则。《人面桃花》在叙事上达成了中西方叙事传统与技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在内容方面又利用中式传统的写意方式来探究中国式的乌托邦思想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最终形成了跨越文化背景的精神哲理。
叙事方式:整合与重构
一、表层:因果循环描述下的风云传奇
因果关系与情节的环环相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叙事技巧,在《人面桃花》中,女主角秀米的乌托邦革命实践是有因可循的:在秀米儿时,父亲陆侃“桃花源”式的理想图景、修建“风雨长廊”的疯狂举动,这为她日后的革命行动埋下了种子;而在少女时期,家中暂住的“表哥”张季元对秀米关于“平权”“民主”的思想渗透,为她的乌托邦实践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而秀米在“花家舍”所看到的与经历的大同景象及杀戮暴动为秀米最终的革命实践行为提供了动力与行动指南。当秀米在“花家舍”与尼姑韩六闲谈时,韩六明确地猜出秀米心中想的是“这个王观澄这般的无能,这花家舍要是落到我的手里,保管叫它诸事停当,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更加印证了秀米心中隐秘而朦胧的梦想。《人面桃花》没有刻意去渲染与铺张历史的壮阔之感,它从历史生活中一个小人物的不平凡际遇与做出的人生选择,揭示了当时的普通人在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时可能出现的想法与可能付出的行动,以及这种所思所想在付诸实践后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结果。尽管《人面桃花》的整体故事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但在叙事的过程中读者经常可以发现文本中的“传奇”色彩。例如,古人焦先所建造的桃源仙境一直像一个迷梦般笼罩着故事中的所有人;梦境中的声音与景象可以通过“忘忧釜”这一器物被感知,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影响故事主人公的人生选择。
传奇故事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延续了古典小说“传奇”叙事的手法,不仅为作品增加了神秘而浪漫的氛围,也在叙事学理论上彰显了中国古典叙事方式的精致与巧妙。

二、深层: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人性嬗变
在《人面桃花》中,格非通过现代主义的视域,将激烈的情感态度隐含在乌托邦叙述的深层,运用“人物的符号化”与“时空效应”对生命、人性与岁月进行凝视。在小说中,“陆侃”与“王观澄”这两个重要人物并未在文本中真正出现,而是大量地依靠他者的叙述来展现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发展脉络。这种“不在场”的设计使得人物在“被讲述”的过程中逐渐符号化,使人物的命运带动叙述的绵延更具深长的意味。秀米的父亲陆侃被视为“出走的疯子”,而“疯子”这一符号在西方文学中常被看作是具有乌托邦冲动的象征。尽管陆侃在小说开篇便通过出走的方式远离了秀米的成长轨迹,但这种情感的冲动却与秀米如影随形。而花家舍曾经的总揽把王观澄首次出现是在尼姑韩六向秀米介绍花家舍的对话中,之后秀米又在花家舍小岛的一处墓碑上发现了“活死人王观澄撰”的字样。在某种意义上,秀米最终的革命实践与结局也让她成为一个“活死人”——在指路人王观澄的影响下,她兴建普济学堂、进行乌托邦革命的实践,但最终依然抵挡不住个人意识形态对乌托邦王国的反动而走向了失败的结局。格非在叙述中用秀米的人生境遇补充了陆侃与王观澄在读者视域中并不完整的乌托邦经历,以历史的宿命论印证了人性的脆弱性与乌托邦王国的不可抵达性。同时,格非巧妙地利用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秀米在乌托邦理想幻灭与失去儿子的双重打击下,成了一个“哑巴”。这种“人为的自闭”产生了相当大的时空效应,尽管时间在前进,但秀米的心理镜像却在倒退——在小说的结尾,她与侍女喜鹊重返“花家舍”后看到船队经过,心中重现了多年前的自我形象,“她知道,此刻,她所遇见的不是一个过路的船队,而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在这一段的叙述中,时间从当下逐渐流回到秀米纯真的少女时代,格非通过融合现实的“此情此景”与历史记忆中的“久远过去”,在对秀米短暂一生进行了回溯的同时,最终也消解了真实的存在感。
思想内涵:写意与乌托邦
一、外在:写意的方式及其内涵
“写意”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不同于西方讲求事物的真实性与具体性,中式的“写意”借助不同的意象,所要表现的实则是一种超脱于物质本身的形而上价值,因而“写意”也可以被看作最具代表性的中式传统艺术观之一。在《人面桃花》所描绘的普济景象中,“桃花”“瓦釜”与“金蟾”即是最典型的意象。不论是书题中的“人面”与“桃花”,还是丁树则赠送给陆侃的《桃源图》,抑或是故事接近尾声时怒放在破败的普济上的那些桃花,都不难让人联想到命运同时空之间的关系——与“人面”所联系的精神内涵是人的欲望与冲动、寻找与迷失、生存与死亡等,而年年怒放依旧的“桃花”则可以看作是时空、自然、宿命等无法逆转的种种外部存在。故事中的“瓦釜”则是被陆侃、张季元、秀米等人视若珍宝的一个带有“预言”性质的意象,秀米通过发声美妙的“忘忧釜”仿佛看到了“尘世之外还另有一个洁净所在”,而这也象征着超越尘世的纯洁品质以及主人公心中触不可及的最高理想。“金蟾”则是革命党“蜩蛄会”的联络信物,它被不同的人交到秀米的手中,是串联故事发展的脉络线索,也寓意着对于救世理想的守护——关于“革命”的共同理想将被代代延续。这些意象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它们与小说的内在气度更是息息相关。
二、内在:乌托邦幻象及其特色
中国古典气质不仅体现在《人面桃花》的外在形式方面,其文本内容与精神文脉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建构起一个充满着中式特色与韵味的乌托邦理想国,并将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赋予其中。早在中国的魏晋时期,陶渊明笔下便有“桃花源”这一在地缘上与世隔绝的理想国,中国文人志士也常在仕途不顺或是面对社会肮脏现实无能为力时选择退隐山林,以隐逸的隔绝生活实现灵魂的净化与升华、达到个人的至善境界。在古代,文人墨客所有关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中国式乌托邦首先是文人的乌托邦,它变成了文学的素材让人们去体会和感悟,通过文学的加工让它变得更加不可触及。在小说中,秀米在乌托邦实践失败后,回归到了中式传统的“桃源幻梦”之中,即从外在的具体行动转向关注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在与外界断联的情况下修养自己的“本心”。尼姑韩六曾有一番关于“本心”的透彻言论:“人的心就像一个百合,它有多少瓣,心就有多少个分岔,你一瓣一瓣地将它掰开,原来里面还藏着一个芯。人心难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看透生死倒也容易,毕竟生死不由人来作主,可要真正看透名利,抛却欲念,那就难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对于人内心及欲望的教化与约束是治理社会、维系社会安稳的基础条件。这一思想的内在要旨就是以人的高尚内在修养来治理天下。而秀米在一切趋于荒芜后也终于顿悟了关于“乌托邦幻象”的道理:所谓的乌托邦幻象只不过如同天上飘动的云和烟,不知所终;唯有认清自己的本质,才有可能辨别人生的欲望、收获真正的自由。
跨文化性哲思:孤独人生与理想主义
戴姆拉什认为“一旦诸多外国作品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世界文学便尽显无遗。”从跨文化性的视角来看,《人面桃花》就平凡人物跌宕而又充满了虚无之感的人生际遇,自然地引申出了不同国别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生存处境,即,人生的孤独之感与薪火相传、难以磨灭的理想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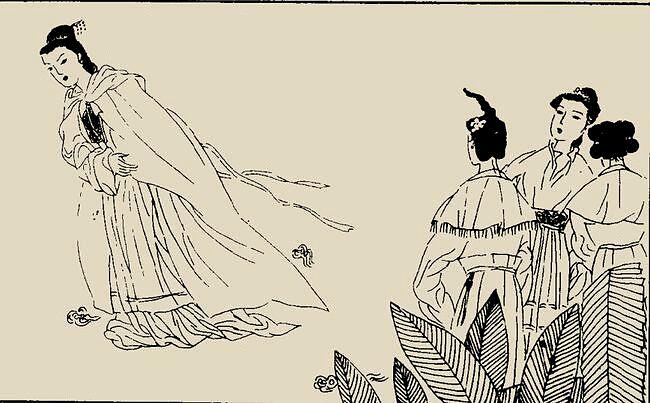
在对《人面桃花》的评价中,许多评论家认为《人面桃花》的创作犹如一场《百年孤独》式的探寻,这不仅表明《人面桃花》具有《百年孤独》一般“梦境与现实”相交错的美学特征,这说明格非赋予了《人面桃花》不容忽视的“伟大的孤独精神”。在格非笔下,秀米与父母之间缺乏沟通,花家舍众首领间彼此猜忌与残杀,普济的改革活动最终也在众参与者的背叛与离去中走向分崩离析的结局……孤独的状态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共性,是中西方文学书写永恒的母题。格非在作品深层所要表达的正是全人类在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孤独精神:每个人的梦都难以被世人理解,个人的行为与思想也具有难以跨越的封闭性。因此,对于人类来讲,真正的解放是不强求他人的、关注于自我的解放。同时,《人面桃花》也将目光聚焦于中西文化共生的“理想主义”之上,从而形成了融汇浪漫与理想主义的一则寓言。也许乌托邦的幻想并不可靠,但人类却又不能抛弃理想。格非借助于乱世众生的种种行为,揭示了“理想主义”之于普罗大众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张季元率领的那些来自社会中上层阶级的革命党人,抑或是那些义无反顾加入革命队伍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能体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人类的本质不过是“孤独地为了理想而奋斗”,这样的精神却经久不衰,从而能够被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坚持与传承。
当今世界,尽管“全球化”面临一系列风险因素的挑战,但其趋势依旧在纵深发展,而“世界文学”无疑是帮助人们了解自我与他者、弥补现实生活中不足之处的重要媒介。格非的《人面桃花》是“江南三部曲”的开篇之作,这一创作打破了格非早期“西方化”的创作风格,在重塑西方叙事技巧的同时巧妙地回顾并融汇了中国古典叙事方式,用传统写意的手法描摹出了一幅中西融合的“乌托邦幻象”,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处境。由此可见,格非的《人面桃花》从历史、人性与命运的多重角度思考了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意蕴,形成了普世性与跨文化性的双重特色,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以崭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