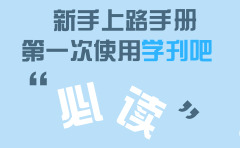方寸灶台间,陶然摹众生 ——读房伟中短篇小说集《小陶然》论文
2025-12-27 13:50:50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房伟创作《小陶然》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对现实与文学边界的持续勘探。“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生活越来越发展,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很多家庭危机和社会危机,由此而来……然而,那些表现方式,是非文学的。
陆文夫曾把作家比喻成厨师:“一个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就像一个厨师,哪有厨师只管自己烧菜,不管食客的口味?否则,你烧得起劲,他难以下咽,新书都睡在书架上,就等于饭菜都倒在泔脚桶里。”这一观点恰与《小陶然》扉页的介绍“每一道私房菜都是一个不俗的故事”形成巧妙呼应。如果说优秀的小说家需要理解读者、摹写我们能够共情的生活,那么房伟便是一个深谙其道的“掌勺人”——一方烟火缭绕的灶台前,他取日常生活为食材,以人生时序为火候,用宽容之心作调味,在现实与虚构的交融中慢慢烹煮众生的喜和忧。
一只酸甜苦辣咸的勺子
房伟创作《小陶然》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对现实与文学边界的持续勘探。“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生活越来越发展,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很多家庭危机和社会危机,由此而来……然而,那些表现方式,是非文学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当社会发展带来了物质丰裕却拉远人心的距离,当家庭与社会危机在日常摩擦中潜滋暗长,这些被新闻报道平面化的困境,该如何通过文学的独特表达获得立体的生命?作者跳出对生活表象的简单摹写,用一支能够品尝人生百味的勺子,舀取不同阶段人群灵魂深处的复杂况味。有青春的炽烈与怅惘,有中年的挣扎与坚守,有老年的通透与眷恋,而这些焦虑与超脱、困惑与顿悟交织的滋味,正是《小陶然》让读者生出共鸣的秘诀所在。
在《小陶然》创作谈中,作者曾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喜欢旷课、写诗、画漫画、乱读书,为了读武侠小说天天翻学校的高墙。”《九三年》里的青春正带着这样的印记,裹挟着20世纪90年代独有的粗粝锋芒,这群少年鲜活坦荡、无拘无束、浑身漾着江湖气,读来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王朔《动物凶猛》里的马小军和他的死党们,他们身上都浸染着未加驯服的生猛,对世俗规训的本能抗拒。书中的刘金花是“公认最漂亮、强悍、有权威的女流氓”,如同《动物凶猛》里的米兰,都是同龄人中的“风云人物”:米兰泳池边的自在成为少年们目光的焦点,刘金花则凭借自身不驯的强悍和骨子里的傲气,活成了少年们心中自由本真的模样。这就是九三年的少年,把“想当流氓”喊成口号,以为拳头能摆平道理、热血能烧穿平庸。岁月却不饶人,又推着他们走出九三年:秦老师不再当“皇帝”,二肥进了看守所成为囚犯,“我”度过青春期,变成了“庸俗迟钝的小学教师”——我们永远留在了九三年。这种今昔境遇的强烈反差,让房伟的青春书写突破了传统成长叙事的浪漫滤镜,以粗粝直白的笔触解构青春符号,并以个体经验勾连起时代记忆,为青春题材文学注入了兼具现实质感与人性深度的独特价值。

如果说青春书写是对“挣脱”的描摹,那么房伟笔下的现实题材便是对“承担”的凝视,同样带着生活的本真,拒绝悬浮的崇高,作者只是把镜头对准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坚守。《果奠》中,消防员殉职牺牲后,失去儿子的母亲没有流露痛彻心扉的哭喊,而是把绵长的思念与隐痛封存在一瓶瓶黄桃罐头里,每一个拧紧的瓶盖都藏着未说尽的牵挂。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那场令人心痛的天津港爆炸案,被火舌无情吞噬的年轻消防员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离去给无数家庭留下了余生难愈的创伤。《一个人的归途》中,疫情突袭、人人自危之际,医生如怡毅然踏上了医院的归途,没有刻意拔高的赞颂,只有普通人担起责任的清醒与牵绊。主人公“如怡”之名自带希望暖意,如今疫情已经过去,回望那段交织恐慌与感动的岁月,这些毅然奔赴的身影都是我们的“平凡英雄”,也让我们看到了责任在普通人身上的分量与光芒。
另一方面,《爱情买卖》与《弟弟的直播》这两篇作品,则共同掀开了数字浪潮对现实生活的冲击与人性的扭曲异化。《爱情买卖》里,失业的中年厨师因沉溺网络陪聊的虚拟温暖一步步偏离人生轨道,为了挽留虚假的情感联结,竟在镜头前做起“淋血炒饭”的荒诞直播。当情感需求被捆绑在虚拟互动的流量规则里,生活的本真也在虚拟的拉扯中逐渐变形。《弟弟的直播》则展现了另一种迷失:超市老板龙傲天不愿以真实身份诉说自己的人生,便虚构出“弟弟”的身份直播,借镜头诉说自己青少年时的遗憾与中老年的家庭焦虑,镜头前的嬉笑怒骂看似热闹,实则是数字时代之中身份焦虑的缩影。当真实的自我找不到倾诉的出口,便只能躲在虚拟身份背后流露心声,人也就在虚拟与现实的模糊边界之间慢慢丢失了对自我的清晰定位与认知。
在青春迷茫、中年焦虑等主题占据文学叙事主流的当下,《小陶然》与《老陶然》这对姊妹篇显得格外难得,它们将目光投向少被关注的老年情感世界,让老年群体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心事与抉择不再隐匿于文学书写的边缘。《小陶然》中,市文联副主席老邱丧偶后,在工会主席的撮合下开始相亲,而银行高管高菁菁也隐去身份,以钟点工的模样接近老邱。她借着收拾屋子的机会留意老邱的生活习惯,在准备家常饭菜时试探他对晚年相伴的期待,看似是虚情,其实都是一片真心,历经半生风雨后,他们更在意的是一份感情能否融入柴米油盐的安稳,能否抵御岁月的平淡。《老陶然》中的闫阿姨面对丈夫出轨的背叛、自己身患绝症的痛苦、女儿争抢财产的冷漠,一度感到绝望无助,却始终没有放弃从伤痛里打捞生活的勇气。从脆弱到坚强的蜕变,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真实书写着老年女性的生命韧性。这样的形象让我很容易地联想到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哈维沙姆小姐,她被情感创伤困住一生,与闫阿姨的坚韧形成鲜明对照。也让我们清晰地看见,老年情感从不是文学叙事中被遗忘的角落,它蕴含着最贴近生命本真的细腻与力量,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不再是沉默的存在,这也为当代文学的情感书写增添了厚重的岁月质感。
酸甜苦辣咸的人生滋味,在《小陶然》里一一呈现。房伟以笔为勺,让我们在品味中看见众生,也看见文学对生活最真诚的回应。
一位虚实间来去自如的“说书人”
房伟的《小陶然》首次出版于2022年9月,彼时收录了八篇中短篇小说,包括《九三年》《果奠》《一个人的归途》《月光下的黄羊》《爱情买卖》《小陶然》《老陶然》《南方》。经过作者的精心修订,2025年最新修订版新增了《弟弟的直播》《幸福的人在微笑》,共计十篇,恰似一席“十全十美”的文学盛宴。当我读罢全书、回看目录时,才恍然发觉这十篇作品的叙事顺序竟然暗合时间脉络,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层层递进。房伟作为一位别出心裁的“说书人”,悄然织就了一部完整的人生序曲。
全书依循着“成长——成熟——衰老”的生命节律,却又不止步于线性叙事的刻板,像是在为读者铺就一条蜿蜒的人生小径,自然地牵引着我们走进作品所营造的情境之中。《九三年》的少年带着生猛的莽撞挥洒汗水,《一个人的归途》里青年医生已在岗位上扛起担当与责任;《月光下的黄羊》见证着都市男女在爱情与现实之间的纠缠与拉扯,《爱情买卖》《南方》《弟弟的直播》写中年人在婚姻琐碎、异乡闯荡与时代浪潮中反复周旋;《小陶然》《老陶然》终落笔于当代老年生活,在人生境遇与情感波折里回望过往,与生活和解。这种叙事节奏的变化,如同呼吸起伏的生命律动,与人生不同阶段的特点相呼应。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小陶然》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独特的叙事时间与节奏,将不同年龄段人物的情感与故事娓娓道来,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完整而生动的人生画卷,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书中人物从少年到暮年的一生。
同时,各个篇目之间又似暗河潜行,于关键处显露出精巧的勾连。如《九三年》中结尾一句“九三年后,不再有强烈的饥饿感”,就这样划下少年与青年的界痕——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情,当物质层面的钝痛消散,精神世界的惶恐便如薄雾弥漫开来,从肉身到灵魂的失重,这就是成长最本真的隐喻。而青年到中年的过渡,在《月光下的黄羊》与《爱情买卖》的对照中愈发清晰:都市男女在草原月色下追问爱情的纯粹,失业的大龄青年在虚拟与现实的情感中寻求寄托。《弟弟的直播》与《小陶然》的细节中也暗合着中年到老年的转捩,一个沉迷于网络直播的“龙傲天”在数字浪潮中左支右绌,深陷自我身份的迷失与焦虑;一名老年丧偶的文艺工作者在相亲骗局中被虚假的温情裹挟,最终又在陶然亭得以自洽。于是,一条贯穿生命的长河就这样缓缓流动起来:少年不知天高地厚的肆意青春,青年怀揣着理想与现实的青涩,中年“被推着走”的挣扎仓皇,老年“停下来看”的通透释然……恰似河水穿过乱石嶙峋的峡谷,闯过湍急的中段,最终淌进波平浪静的大海。
在现当代文学的世界里,茅盾以都市为舞台精准剖析中国的阶级矛盾,老舍以嬉笑怒骂描绘北京底层市民的众生相,巴金以青春烈焰灼烧现实的阴霾与压迫,沈从文在湘西秘境搭建自己的“希腊小庙”……前辈大家皆有其深耕的文学疆域,将特定时空的生命形态书写得入木三分。而房伟的创作却呈现出另一番气象:他更像一位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去自如的说书人,行囊里装满了天南海北的众生故事,既不困于单一题材的深耕,也不囿于固定疆域的营构,而是以敏锐的触角捕捉着社会飞速发展中涌现的各式面孔。《果奠》的叙事实践,恰是这位说书人游走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生动实践。其故事的核心脉络脱胎于作者在山东消防采访时接触到的消防员殉职事件,这些真实素材构成了说书人讲述的“底本”。房伟将这些现实原型作为叙事的根基,让听者能够在具体的人与事中触摸到消防群体的职业重量与情感温度。但说书人的智慧更在于不被“底本”所缚,作者又以虚构为叙事的手段,对真实素材进行艺术化处理:比如让牺牲的孟凯重返人间与母亲对话。这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让母亲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牵挂有处安放,不用只靠眼泪表达。通过战友之口解开母亲多年的困惑,也不是凭空设计,而是把消防员内心的责任宣之于众,帮助母亲明白孩子当初的选择。
这位说书人对现实与虚构的调度,让每个故事都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真实的事件为说书人提供了“说什么”的素材,虚构的笔法则决定了“怎么说”的智慧。这种在现实与虚构之间从容摆渡的讲述能力,正是房伟作为一位说书人的基本功。他的故事既有扎实的根基,又有鲜活的质感,最终能跨越具体时空,在听者心里留下长久的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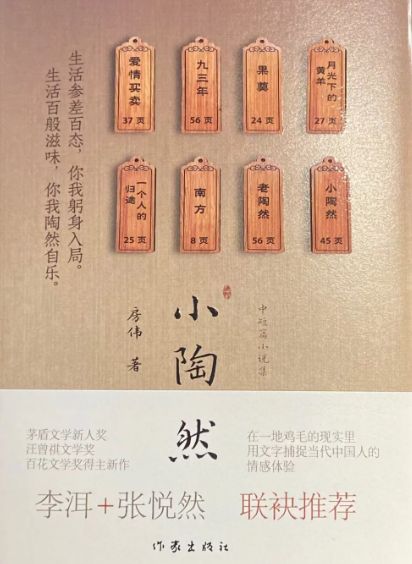
一座“小是小非”构筑的陶然亭
房伟在其理论著作《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中,明确提出了如是观点:“对后发现代中国而言,宏大叙事却未死亡,依然具有表述合法性,并在小说实践中,继续以‘结构性要素’的方式存在”。在他的理论语境里,宏大叙事被锚定为关乎时代底色与价值根基的“大是大非”,如张炜的《九月寓言》胶东乡村的民间故事与集体记忆,承载乡土文明与现代冲击的碰撞;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借一场跨越实战边界的军事演习,书写军队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变革困境与精神坚守。与之不同的是,《小陶然》并没有直接在文本里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命题或非黑即白的终极抉择,而是将目光投向爱情的功利、亲情的疏淡、中年的焦虑、老年的困境……这些日常生活的“小是小非”之中。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选择,背后始终贯穿着他对人性与生活的“陶然”心境。
“陶然”一词,源自白居易笔下“更待菊黄家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原本传达的是远离尘世喧嚣、悠然自得的心境。但在房伟的《小陶然》中,这份“陶然”早已超越了原初的避世悠然,它不再是对尘世纷扰的刻意远离,而是化作一种直面人生百态的体谅与包容。
《月光下的黄羊》中,“我”与安筠相恋多年,曾在诗歌与理想中找到共鸣,可谈婚论嫁之时,安筠对优渥生活的渴望逐渐显露,她想要的不只是安稳,更是能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生活,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要有能力享受奢侈消费……“我”作为一个普通职员,自然无力满足女友的物质欲望。所以最终,安筠选择嫁给能够满足她所追求的优渥生活的万总,曾经以精神契合为核心的爱情,如今却成了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房伟没有指责安筠的选择,也没有渲染“我”的委屈,只是平静地呈现两人从默契到分歧、从相守到分离的过程,让读者看见这份情感结局的背后,是时代物质化浪潮下,个体在欲望与现实间的挣扎,“我”和安筠的故事,不过是无数普通人在爱情与金钱面前不得不面对的纠结与选择。
《老陶然》中的闫阿姨同样面临着独属于自己的艰难处境。与丈夫离异后,原本靠参与歌舞团排解自己内心孤独的她,突然被一场癌症打乱了生活节奏。生病的闫阿姨不仅要面对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还要处理与丈夫出轨对象章怀懿的矛盾,还要承受亲情的淡漠:女儿项莉莉得知病情后,最先考虑的不是母亲的身体,而是如何用母亲的存款和房产解决外孙的学区房问题;儿子项诚虽本性善良,却在妻子的影响下,只纠结于医疗费的分摊方案。过往的平静被彻底打破,闫阿姨的生活又一度陷入绝境。但是,坚韧的她在经历了种种打击后,逐渐摆脱了过去的依赖心态,彻底释放了长久以来的隐忍,最终找到了本真的自我。房伟曾说,创作闫阿姨是为了“表达对中国老年女性的敬意与尊重”,因为她们“伟大而富于忍耐精神”。作者不仅理解她面对癌症时的恐惧,也尊重她摆脱依赖的努力,这种不苛责、不美化的宽容态度,让我们得以看见无数中国老年女性在时代转型中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闫阿姨最终在大雨中沉思的背影,既是她摆脱束缚、找回自我的高光时刻,也是房伟对老年女性生存现状的尊重,“陶然”超越了个人心境,成为一种观照现实、体谅他人的文学温度。
正如有一次,房伟在与读者互动时所言:“相对价值追求和生命体验来说,要作道德判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人性是丰富和复杂的。”他笔下的“陶然亭”从来不是评判“对与错”“好与坏”的审判庭,而是容纳人性真实、直面生存困境的栖息地。我们无需苛求自己处处完美,更该以一颗“陶然”之心去体谅每个普通人在“小是小非”中的挣扎,接纳他们各自的归宿,这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合上书页,《小陶然》中的人间百态仍在眼前流转。它不是一部浅白的情感图鉴,而是作者扎根当代中国、以真诚为底色写就的文学篇章。作者避开了中产小调的浮泛抒情,也摒弃了私密书写的俗艳猎奇,在小说创作“轻”与“重”的辩证关系间找到了精准的平衡点。不管是少年的心事、中年的难处,还是老年的通透;不管是纯粹的爱恋、虚浮的纠葛,还是晚年的温情,皆被妥帖纳入叙事之中。
在新时期文学聚焦现实、探索叙事创新的语境下,“如何创新性地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路径?”始终是我们思考与追问的核心命题。房伟的《小陶然》为我们交出了一份恰切的答卷:既不倚仗宏大历史命题的铺陈,也不依赖猎奇情节的堆砌,而要以观察者的敏锐捕捉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人性细节,以共情者的自觉转化日常经验里的生命体验。正是这样不悬浮、不刻意的书写,让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与灵魂在琐碎日常中寻得了被看见、被安放的空间,也为“中国故事”的讲述增添了贴近大地的质感与直抵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