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哲学视域下的儒家礼乐观念论文
2025-10-01 15:25:30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儒家礼乐观念秉持身心合一理念,二者相互作用以塑造完整人格。此观念不仅关注个体身心和谐,还将其延伸至道德修养、社会秩序构建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层面。
摘要:儒家礼乐观念秉持身心合一理念,二者相互作用以塑造完整人格。此观念不仅关注个体身心和谐,还将其延伸至道德修养、社会秩序构建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层面。文章探究身体在儒家礼乐观念中扮演的角色,剖析礼乐观念对身体的塑造作用,凸显礼乐实践的具身性特征,并思考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启示。
关键词:儒家礼乐;身体哲学;身体观
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中,儒家礼乐观念呈现出鲜明的具身性,体现身体与道德、社会秩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身体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不仅是生命存在的根基,更是儒家礼乐观念得以存在的基石。儒家倡导“礼教”与“乐教”并行,借助“礼”来规范身体行为,进而实现社会和谐;通过“乐”来调节情感、陶冶性情,推动个体心性的提升。在践行礼乐活动的过程中,身体实践引发意识层面(在中国哲学中称之为“心”)的变化,主体通过身体感知与内心体悟实现身心的共同发展。
一、身体哲学与儒家礼乐观念概述
(一)身体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核心观点
在古希腊哲学中,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初步提出身体与灵魂相关联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人的灵魂亦如此,而身体作为灵魂的载体,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随后,柏拉图构建理念世界,身体和灵魂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灵魂追求理念世界的真理,身体却被视作灵魂的束缚,因其产生的食欲、性欲等欲望会干扰灵魂对真理的认知。亚里士多德则持有相对折中的观点,他将灵魂看作身体的形式,身体视为灵魂的质料,强调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奥古斯丁主张人要克制身体的欲望,依靠信仰和神恩净化灵魂,从而获得救赎。在这种观念下,身体被当作灵魂的容器,由于人的原罪,身体常被视为堕落的象征,需要被灵魂克制。
近代哲学中,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成为身体哲学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心灵的本质是思考,身体的本质是广延,心灵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且身体的运作可用机械原理进行解释。斯宾诺莎则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提出心灵和身体是同一实体(神或自然)的两种不同属性,身体状态与心灵状态一一对应,身体活动和心灵观念呈平行关系,为后续身心关系的探讨开辟了新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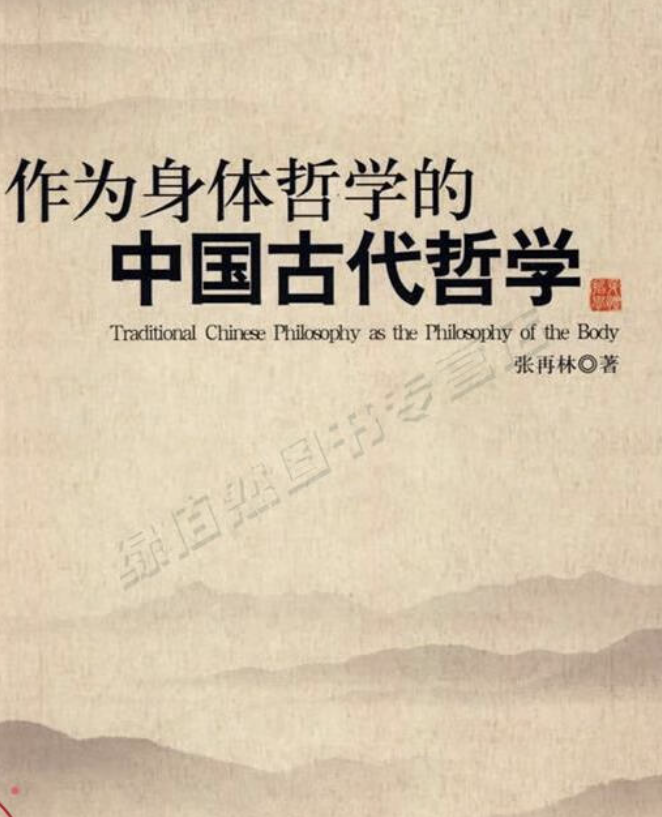
现代哲学中的身体现象学以梅洛-庞蒂为代表,他批判传统哲学对身体的忽视与误解,指出身体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知觉的主体,并在《知觉现象学》中详细阐述身体在空间感知、运动感知等方面的作用。身体并非被动接受外界刺激,而是主动参与到对世界的建构中,产生对世界的认知。这种具身认知的观点对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身体哲学聚焦于身体在认知、存在、伦理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键作用,其核心观点包括:一,具身认知,强调认知过程基于身体的体验和行动;二,身体的存在论意义,身体是个体存在于世界的基础和载体,不仅具有物质性,更是个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媒介;三,身体与伦理道德,身体是道德行为的发生场所和重要载体,身体的行为、姿态和感受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
(二)儒家礼乐观念的内涵
儒家思想强调从个体的修身出发,逐步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和国家和平。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具身认知的过程。通过身体的实践(如礼仪、乐教等),个体在行为上遵循道德规范,在认知上内化规范,从而实现身心的统一和社会的和谐。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身”,大多与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意识层面的活动有关,如“省身、致身、忘身、正身、终身、亲身、洁身、辱身”等词汇,在体现身心一元的同时,也表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个体管理日常行为习惯和情绪以修身,家庭共同劳动、长者身体示范以齐家,领导者身体力行、民众身体参与以治国,此为“修身齐家治国”中的具身性,强调了通过身体的实践和行为来实现道德修养、家庭和谐和国家治理的目标。
在儒家观念里,“礼”是重要的道德准则,可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明确了不同身份角色的道德秩序,要求君主履行职责、臣子尽忠职守、父亲慈爱子女、儿子孝顺长辈;同时,“礼”也是具体行为的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以严格的礼仪要求构建起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此外,“礼”还是人们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丧礼中孝子的哭泣、守灵等行为,就是对逝者哀思之情的外在表达,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千家万户。
儒家思想中的“乐”涵盖音乐、舞蹈、诗等综合性艺术活动。它被视为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以“乐”的形式表达欢乐、悲伤、崇敬等多种复杂情感。同时,“乐”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乐的韵律和节奏与天地自然的规律相呼应,例如古代的乐律与节气、天文等知识存在一定关联,人们通过感受自然节奏,可达到身心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礼”与“乐”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外在形式,更是内在修养的体现。礼乐实践借助“身心一元”的纽带关系,让活动主体通过身体感知,进而获得内心体悟。
二、身体在儒家礼乐观念中的基础地位
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1]。它更为关注存在的本质、存在的基础、存在的根据,身体作为物质的同时也是感知、情感、认知和行动的中心,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活动、行为,恰如强调意识必然要强调观念和思维[2],行为往往作用于虚无形态的意识,反之,一个人的身体行为往往反映主体的内在意识,此为“具身性”的显著体现。
(一)礼——身体的礼仪化
《礼记·大传》载:“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3]”其中,“亲亲、尊尊、长长”意为亲近亲属、尊敬尊长、敬重长辈。前文提到改变历法、服色、徽号、器械等,而后文强调“礼”不可变革,因为“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它规定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规范个体行为实现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而这些行为大多是具有符号意义的身体语言,像祭祀、朝拜、礼仪等活动,都有特定的形态、程序和象征意义,且都需通过身体的具体动作来完成。这些动作不仅是外在形式,更是内在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它们训练身体以使其符合社会规范,而社会也需要经过规范的身体来维持尊卑秩序。
作揖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表问候、尊敬,常见于文人、君臣或朋友之间,如《论语·学而》中“子见老子,作揖,问曰:‘子之可得也,斯人也[4]’”,《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子产见公子,作揖[5]。”由此可见,“作揖”已成为具有固定含义的身体语言,被大众熟知并广泛使用。此外,还有叩首、颔首、拱手、饮酒倾杯等身体行为,上至朝堂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将其内化,在一次次的场合实践中不断深化其影响力,从而形成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这充分体现了“礼”带来的认知具身性。
(二)乐——身体的感知与内化
乐的欣赏是一种综合性的身体感官体验,人们全身心沉浸其中品味乐的审美特质,理解儒家所追求的“尽善尽美”。这种审美体验不仅提升了人们对音乐艺术的鉴赏能力,还增强了对儒家礼乐文化的认同感。下面以祭孔乐舞《八佾舞》为例,从身体感官角度来认识乐。
1.视觉体验
视觉感官首先接触到的是服饰、阵容和仪式场景布置。八佾舞的服饰因朝代不同而有所差异,以北宋制式为例,文舞生头戴漆布制作的黑介帻,身着红绢大袖袍,胸背绘有缠枝方葵花,以红生绢为里衬,外加锦臂鞲,束黑角带,脚穿皂皮四缝靴;武舞者戴漆布制作、上加描金蝉的武弁,服饰、腰带等同文舞生。文武舞者通过冠帽区分,整体服饰偏向暖色,红色代表吉祥、热情,葵花图案寓意美好、繁荣。武舞服饰相对短小,便于做出挥舞斧盾等动作。文舞生右手执翟(龙头髹木插三根雉鸡尾羽),左手执籥(短笛形竹管),翟象征文采斐然,籥代表内心声音,二者结合象征内外兼修、文质彬彬。舞蹈动作干净利落、沉稳大气,敬礼、弯腰、低头等姿势表达对天地、圣贤的尊重,脚下步伐节奏均匀、有顿点,举手投足间尽显庄重。观众看到这样的场景,身体会不自觉地端正,内心也会涌起对先人的敬重之情。
《春秋》中记载八佾舞的规模人数为“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6]。”,其中数字表舞蹈队形的行、列数,“天子用八”即为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同理得诸侯、大夫、士的所用人数,这种严格的人数规定既等级制度的划分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
再言孔庙布局,一般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前到后依次有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十三碑亭等建筑,直至大成殿,仪式多在大成殿前的丹墀及大成殿内举行。在丹墀处搭建木质或石质舞台,用于乐舞表演;在城门上方、道路两旁或建筑周围悬挂印有儒家核心思想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内容的幡旗;在大成殿内正中悬挂大幅孔子画像,四周墙壁镶嵌《孔子圣迹图》等壁画,给人以宏伟肃穆之感。2.听觉体验
音乐是许多礼仪活动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八佾舞》演出时使用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八类乐器,通过不同乐器的组合和演奏,营造出古朴典雅的音乐氛围;演奏成数固定为六章六奏,分别是迎神奏《昭平》之章、初献奏《宣平》之章、亚献奏《秋平》之章、终献奏《叙平》之章、撤馔奏《懿平》之章、送神奏《德平》之章。歌生演唱时要声音洪亮、整齐划一、吐字清晰,节奏平稳和谐,每字八板八眼,体现出中正平和的气质,展现孔子的中庸哲理,传达对孔子的赞颂和敬意。
3.嗅觉体验
在祭孔乐舞《八佾舞》的仪式场景中,嗅觉体验主要来自祭祀香,仪式现场燃烧特制的祭祀香气味浓郁、持久,其成分可能包括檀香、沉香等珍贵香料,淡淡的焚香气味萦绕四周,营造出神圣、肃穆的宗教仪式感,将人们的情感与思绪引导向对先圣孔子的缅怀与尊崇之中。
以上遵循的这些八佾舞礼仪源自河洛的“六代乐舞”,始于周公制礼作乐。《礼记·乐记》云:“乐者,和也;舞者,动也。[7]”其中“和”与“动”体现了身体与心灵的统一,礼乐实践活动承载着儒家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通过外在的身体感官体验与内心的虔诚产生一致,产生精神崇敬,形成身心合一的状态,不管是严格的服饰要求,还是庄严肃穆的乐声,在满足审美需求的同时也体现身份地位和礼仪的庄重性,提醒参与者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自己的身份角色,深刻理解礼乐在传递家族情感、延续文化传承方面的意义。由此可见身体在儒家礼乐观念中的基础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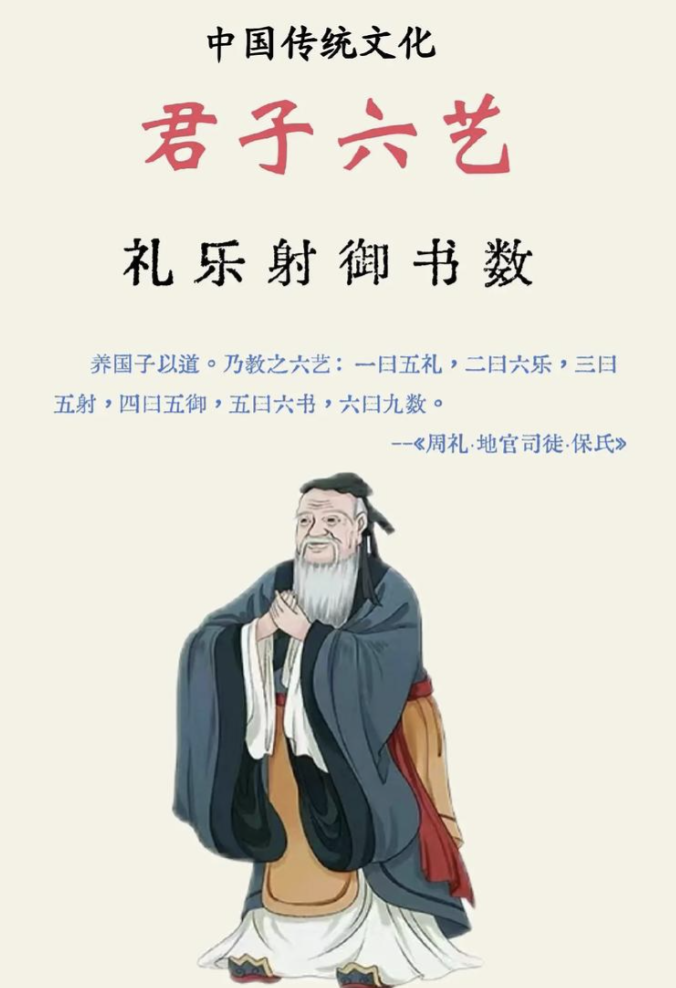
三、儒家礼乐观念对身体塑造的影响
礼仪规范的日常行为对身体有一定约束。行走姿势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和道德风貌,儒家倡导行走时步伐要稳健,目不斜视,分别象征着内心的沉着和坚定和专注和自律的道德品质,与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相呼应。坐姿要求端正庄重,且根据不同场合和身份保持适当的坐姿,如在儒家的讲学场合,学生们正襟危坐,聆听先生教诲,身体的端正坐姿反映出内心对师长的尊敬和对知识的虔诚,体现出儒家倡导的尊师重道的道德观念。
儒家乐教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通过音乐引导人们将情感表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且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儒家乐教中有不同的用途。乐教注重情感的内化过程,人们在学习和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将乐所传达的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情感,《后汉书·律历志上》所言“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8]。”乐的奥秘无法简单地以文本形式流传,需要心灵通达的人通过身体力行去领悟。身体行“乐”之活动,主体的所得更多在于心灵、在于精神,而非浅层的技艺或者谱册此种物质形态的显现,是通过“乐”的具身性达成情感的调节,并且认知上内化了这种和谐,从而提升身体精神境界,塑造平和宁静的心境,激发崇高的道德情感和志向,践行儒家的道德准则,以天下为己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
四、身体哲学视角下儒家礼乐观念的现代价值与启示
(一)对当代身体教育的启示
儒家礼乐观念高度重视身体实践感知,为现代教育融入身体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借鉴。在现代教育中,可以引入礼乐教育,秉持儒家知行合一的理念。“礼”教育规范身体行为,使内心保持专注平和,培养身体的自律性,为精神修养奠定基础;“乐”教育调节身体情感,帮助主体梳理内心困惑,实现精神的舒缓与成长。这种身体与精神的互动,让身体成为精神修养的实践载体,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二)对社会和谐构建的价值
从身体层面来看,“礼”有助于促进人际和谐。礼仪规范下的身体互动能减少人际冲突,增进彼此的尊重与理解。在日常礼仪中,微笑、友好的眼神、握手等身体动作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减少潜在冲突;在社交场合中,以恰当的身体礼仪与人互动,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能有效避推动人际和谐。
“乐”凭借独特的身体共鸣机制凝聚社会共识。音乐、艺术等“乐”的形式超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直接触动人心,强化人们对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同,为凝聚社会共识注入持续动力,成为现代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黏合剂。
五、结语
儒家礼乐观念在身体哲学视域下可见其极强的具身性,强调“体”在礼乐实践中的核心作用。礼乐修身,更是修心养德之道,身与心的相互作用,让行为主将其礼乐活动体之于身、感之于心,从个体出发以至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实现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融统一。
参考文献:
[1]田丰.身体思维与礼乐文明的现代转化[D].苏州大学,2012.
[2]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J].人文杂志,2005.
[3]曾亦,陈文嫣著.国学经典导读礼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01.
[4]盛莉,左曲美,龙婧主编.经典诵读论语古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08.
[5](春秋)左丘明撰;舒胜利,陈霞村译注.左传[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01.
[6](战国)孔子著.春秋[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01.
[7]曾亦,陈文嫣著.国学经典导读礼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01.
[8]庄适选注;王文晖校订.后汉书[M].武汉:崇文书局(原湖北辞书出版社),201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