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悲欢离合”叙事探赜: 边缘个体命运与记忆时代变迁的影像表达论文
2025-09-30 13:50:16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贾樟柯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其电影风格独具特色。他擅用纪实美学风格,以边缘人物叙事为核心,生动展现他们的命运起伏。
摘要:贾樟柯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其电影风格独具特色。他擅用纪实美学风格,以边缘人物叙事为核心,生动展现他们的命运起伏。文章从旨意、文化内涵、呈现方式和人物情节等多方面对贾樟柯电影中蕴含的“悲欢离合”进行解读分析,挖掘其电影在当代电影语境下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与价值,进而全方位展现贾樟柯电影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与强大艺术魅力。
关键词:贾樟柯电影;悲欢离合;个人命运;时代变迁
“悲欢离合”,作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与哲学土壤中的关键母题,在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经典作品中均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一母题下,道家秉持着“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倡导以平静之心顺应自然,坦然面对人生的起伏;儒家则以积极入世之态,坚信苦难与挫折可磨砺人的意志,如孟子所言“曾益其所不能”。
电影,不仅记录着物质的表象,更重要的是挖掘和展现背后的精神内涵;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载体,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贾樟柯,身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翘楚,始终以纪实美学为刃,精准地剖析平凡之人在岁月长河中的命运轨迹。其作品宛如一部部生动的编年史册,细腻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四十余载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以及身处其中小人物们的悲欢离合。在贾樟柯的镜头之下,个体命运的沉浮与时代浪潮的汹涌澎湃紧密交织,他不仅展现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更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之中,将对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融入每一个画面,使电影超脱于单纯的影像记录,升华为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度叩问,彰显出鲜明的民本思想与现实主义审美风格。
因此,深入探究贾樟柯电影中“悲欢离合”主题的叙事策略与表达路径,剖析其如何借由边缘个体的命运展现记忆时代的变迁,对于精准解读贾樟柯电影的艺术灵魂以及洞察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边缘个体命运的群像勾勒
(一)蹉跎岁月里“悲”之情境的深度渲染
贾樟柯以其首部故事长片《小武》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斩获多项大奖,开启了其辉煌的电影生涯。县城小偷小武,有着奇特“职业操守”,行窃只拿钱财,主动退还身份证等物品。他曾与小勇约定,在其婚礼送三斤重的钱。即便小勇结婚未邀他,小武仍坚守承诺。小偷身上的原则与守信,为“手艺人”角色添了一抹戏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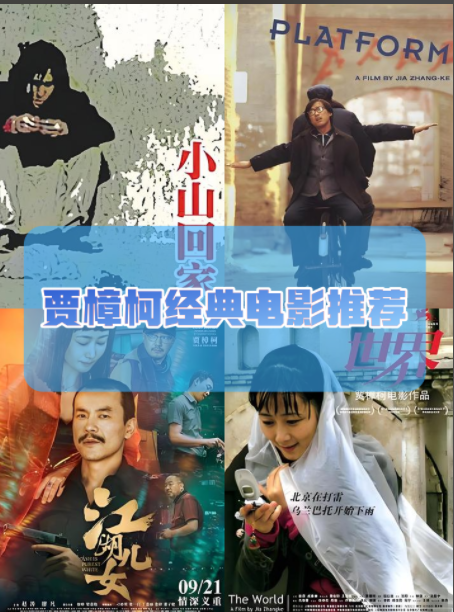
《小武》影片结尾小武被铐在电线杆上围观的那一刻,往日里所有体面都在众人冷漠的注视以及肆意的指指点点之中,如海市蜃楼般消失殆尽。在电影符号学的语境下,那具闪烁着金属光泽、质地坚硬的手铐,作为一种直观的视觉呈现,构成了“能指”。它冰冷的触感、独特的造型,无需过多言语解释,便能被观众一眼识别。而其“所指”则深刻而复杂,既指向了时代变迁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与挣扎,又象征着社会秩序对越轨行为的约束与规训。较于小武的朋友小勇,曾经也是小偷,后来通过贩卖私烟、开歌厅摇身一变成了“民营企业家”。时代的列车裹挟着社会喧嚣,如汹涌奔腾的洪流一般轰隆隆地持续向前疾驰。不愿改变,或难以跟上“时代列车”迅猛的节奏的人们,被无情地甩落到了社会的边缘角落,在落寞与迷茫中挣扎一生。导演运用长镜头拍摄手法,表达出小武此时不安、局促和尴尬的情绪,进而来强化这种“悲”的氛围。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为理解贾樟柯电影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视角。逞英雄之能、行江湖之义的小马哥,因爱情失意、为经济所困的梁子,二人在影片《三峡好人》和《山河故人》中的戏份虽不多,其性格却极具特色,和主角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故事情节、影片结构同样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如小马哥说的:“现在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了!”,最终因值50块钱的“江湖道义”死于一场械斗。身患肺病的煤矿工人梁子拖家带口回到汾阳,在故乡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个年代里有很多像小武、小马哥这种,可以归类于不算张扬的“坏人”,他们都在努力地生活,却始终未能摆脱贫困与疾病的困扰。有很多边缘人物都在蹉跎岁月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是时代的印记,也是一代人的遗憾与悲哀。
(二)转瞬即逝中“欢”之火花的绚烂迸发
中国古代诗词不乏对“欢”的描绘。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尽显及时行乐、豪放洒脱;杜甫“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生动展现战乱平息后的欣喜。诗中“欢”,蕴含诗人价值理念与家国情怀。“电影诗人”贾樟柯作品中的“欢”往往会呈现出,如烟花绽放在天空般绚烂,却又短暂转瞬即逝的欢乐瞬间。
在其精心构建的光影世界中,无论是汾阳街头巷尾处发出的一声欢笑,还是人与人之间碰巧相遇所产生的片刻愉悦心情,都被精准地捕捉到,并且得到了摄影机细致入微的刻画。在电影《小武》《站台》《山河故人》中,小武与梅梅的爱情故事犹如樱花绽放一样美丽而短暂;曾经让人欢聚一堂的文工团,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涛、晋生和梁子三人曾经的友谊,如黄河边冰面上的点燃的烟花,最终要归于平息。
他的电影虽看似粗糙且略显沉闷,但实则不然。在其漫长无尽且略显沉闷压抑的现实主义风格叙事电影作品中,偶然间闪烁而出的点点星光,这份美好又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到几乎在刚刚乍现的那一刻,便又迅速地隐匿于那汹涌澎湃、永不停歇的生活洪流之中,让人还来不及细细品味,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也正因了这份短暂性,它们才愈发显得弥足珍贵,这就是贾樟柯电影特有的审美风韵和艺术魅力所在。
贾樟柯认为:“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含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2]他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对过去时光的眷恋和对传统事物消逝的惆怅,与物哀文化中对世间万物情感的细腻捕捉和对弱者的怜悯有相似之处。多愁善感的他在乎个人的生命感受,思考人在历史中的定位,热衷于为政治上处于边缘,经济上处于贫穷的人们发声。在他的镜头之下,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对于底层人物而言,欢乐时光是如此的奢侈难得。
二、记忆时代变迁的光影铭刻
(一)物是人非间“离”之伤感的幽微袒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生产方式、社会分工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电影中人物在历史的浪潮中不断经历着分离与聚合,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也体现了人性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坚守,而“离”与“合”成为贾樟柯电影一种重要的叙事线索。
小勇再次抚摸那面刻有名字的墙时,与昔日好友小武的感情已生间隙;曾与小武并肩坐着、深情唱歌的梅梅的木床,只剩空床板(《小武》)。崔明亮和尹瑞娟之间有过一段纯真的感情,崔明亮外出闯荡,尹瑞娟则留在了家乡,他们的生活轨迹逐渐分开,曾经的爱情欢乐也只能停留在过去,成为彼此心中一段美好的回忆(《站台》)。时过境迁,同样的地点,人已不是原来的人了。这些电影探讨了友情、爱情、亲情、婚姻等主题,但大多以分别、离开结尾收场,影片情节总是充斥着物是人非的伤感。
“情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有情有义’,我听完之后大受启发。”[3]这是儿时贾樟柯听人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时至今日在他的作品中同样能够看到他对“情”与“义”的解读。《江湖儿女》的故事始终围绕着“情”与“义”展开叙述,电影开篇斌哥让人搬来“关二爷”像,三言两语解决了一起兄弟间的债务纠纷;大哥意外去世,包了厚厚一沓钱给嫂子,正意气风发的斌哥做人仗义,做事讲究情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为斌哥扛罪面临五年牢狱之灾,得到却是对方的躲避,甚至是多年后的不辞而别。
就像电影《山河故人》中的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三段故事都在讲离别,分别是友人离别、家人离别和代际离别。沈涛面对两个男人同时的追求,最终选择了晋生,而梁子则选择离开家乡;婚姻破裂并与丈夫晋生离婚,把到乐送回上海母子分离,沈涛的父亲在车站离世;到乐与父亲的情感完全隔绝二人渐行渐远,与老师米娅开始了忘年恋,最终因世俗、复杂的情感走向破裂。电影画幅历经了从传统电视,到新媒体,再到宽银幕画幅的演变,这一变化过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标志着时间维度下物理层面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山河大地等自然界的事物都会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更何况是具有丰富情感和复杂精神世界的人。这种表达手法不仅深化了电影的艺术感染力,更引发了观众对于时间、生命、情感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历史关系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使电影作品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文化和观念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念、生活态度等都有所不同。
(二)时光悠悠中“合”之篇章的沧桑续写
时光荏苒,故人再次相遇,此情此景别是一般滋味。《三峡好人》英文名叫作《Still Life》,中文翻译为“静物”,就如电影开篇的长镜头记录的一样,劳动者群像犹如静物般定格在某个时刻。电影里的山西煤工韩三明,跋山涉水到奉节寻妻,妻子问韩三明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她,韩三明却沉默不语。再次复合就是十六年,对家庭和传统生活坚守的韩三明决定带妻子女儿回山西,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面前,库区人民默默承受着好人的称誉,带着遗憾和不舍奔波流转艰难迁徙,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连同古老的县城将逐渐被波涛汹涌的江水吞没。
贾樟柯还善用“物”来表达离与合的情感。例如,小武和小勇交谈中,打火机的火苗熄灭,象征着他们的友谊走到了尽头(《小武》);戴墨镜的沈涛和到乐坐在车上,戴墨镜的米亚和到乐坐在车上,这里的墨镜出现两次,并且导演给了两次到乐注视眼前的两个不同的女人,说明墨镜在镜头中有隐喻的作用,墨镜遮住了双眼,留给到乐的是对母亲相貌模糊的记忆,似曾相识的感觉给到乐把对母爱的渴望移情为和老师的虐恋,这是一种想象契合。饺子在影片中多次出现,饺子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情感寓意,沈涛和梁子在愉快地一起吃饺子,此时的晋升饺子没吃上,“醋”倒是喝了不少,自此这也为三人的关系埋下了伏笔。沈涛知道到乐喜欢吃饺子,即使儿子不在身旁也习惯性地包一个特殊形状的饺子,暗示着她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对故人的思念,曾经一起吃饺子的人如今都已离去,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那份温暖与团聚。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Balazs Bella)认为:“时间也像情节、性格刻画或心理描写一样,乃是一部艺术作品的主要东西。”[4]时空的交织与呼应,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带着各自的过去和记忆,在这片土地上寻找着未来的方向,营造出一种时光荏苒、岁月流转的沧桑感,使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时代的印记和人物命运的起伏。

三、当代电影语境下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对边缘性、异质性的关注,打破了传统的中心与权威观念,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主流社会忽视或边缘化的群体和文化现象。贾樟柯电影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他的叙事没有戏剧性的冲突,用纪实美学风格关注平凡的人在蹉跎岁月中的命运变迁史诗。贾樟柯在建构自己电影形式美学的时候,同样特别重视这种现实感、自然感。[5]电影通过展现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表达更深层次的主题和思想,进而引起观众情感共鸣。贾樟柯的电影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深刻的批判与反思,透过《小武》这部影片,导演仿若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发出了灵魂的拷问:那些被时代列车无情甩落的个体,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在社会的浪潮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所并努力适应?《三峡好人》小马哥之死,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底层人物的权益是否有保障?
在一次访谈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尖锐地提问贾樟柯,“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电影是否就是为了在国际上获奖,或者为了博得某种同情。”贾樟柯导演回答则是:“一部电影概括不了一切,它只能概括与表现导演关心的那部分。”[6]精致繁华的上海都市街头并不是中国全部,粗糙朴实的市井生活也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张明信片。我们仰望天空去欣赏如梦如幻月亮的美景时,却忘了构成月球主体的另一面。贾樟柯所塑造的边缘人物就是构成美丽月球背面的每一粒尘埃,他们不是站在阳光下的时代英雄、社会精英,没有超出凡人的意志力或者智慧。他们是坚守家庭传统的煤矿工人韩三明,是坚守自己心中江湖之道的巧巧,这些群像的坚守,更像是贾樟柯对电影艺术坚守的一抹缩影。
相较于国内外其他着眼于小人物命运的电影导演及其作品,贾樟柯的影片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该片关注小人物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挣扎,但没有将人物命运与特定时代的重大变革如此紧密地勾连。韩国导演奉俊昊在其电影作品《寄生虫》中同样关注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对底层生活场景有着具象的描绘,但前者更注重营造视觉上的冲击力和隐喻效果,与贾樟柯的质朴写实风格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
除此之外,他的作品还有着文化传播与记录价值,以及引导影视行业关注现实题材等积极作用。从其作品中也不难看出贾樟柯深深地爱着他的家乡,爱着这片土地:电影里的华语流行歌曲、电影海报、服装发型等,这些流行文化元素成为时代的标志和记忆。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为呈现方式,记录和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等内容,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特色的窗口,同时在文化传播层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也为当代电影承载文化内涵做出了示范。
四、结语
贾樟柯的电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把社会问题照进其中。贾樟柯借“悲欢离合”关注弱势群体、刻画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坚持,传递出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种关怀在当代电影商业化倾向较严重的语境下显得尤为珍贵,引导观众关注身边平凡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引起关注与思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得底层人物在各个领域的权益得到保障,推动法律和观念的进步。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八角笼中》等关注小人物现实题材的优秀国产电影涌现。
参考文献:
[1]贾樟柯.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22.
[2]同[1]:76.
[3]贾樟柯,杨远婴,冯斯亮.拍电影最重要的是“发现”——与贾樟柯导演对话[J].当代电影,2015,(11):38-46.
[4][匈]巴拉兹·贝拉著,何力译.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0):121.
[5]陈波.寻找电影之美贾樟柯十年电影之路[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06):80-84.
[6]贾樟柯,尹鸿.为大时代的小人物写传:对话贾樟柯[J].当代电影,2020,(01):1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