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桑的大海》的牧歌叙事及其北疆文化呈现论文
2025-07-26 16:12:31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孕育于民族交往历史过程中的“北疆文化”,对于我国当下发展仍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小说《巴桑的大海》作为“北疆书写”的生动一例,借由牧歌的音乐特性与艺术技巧在叙事方面开拓出独特的艺术空间,体现为以牧歌性叙事构建成的游牧美学。
摘要:孕育于民族交往历史过程中的“北疆文化”,对于我国当下发展仍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小说《巴桑的大海》作为“北疆书写”的生动一例,借由牧歌的音乐特性与艺术技巧在叙事方面开拓出独特的艺术空间,体现为以牧歌性叙事构建成的游牧美学。海勒根那将自幼聆听的草原上的一切乐音应用于小说叙事中,不仅以显在的蒙古族民歌和自然之音书写游牧世界,还将蒙古族长调中的“复调”“变调”“重复”“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等音乐元素融于作品,实现了小说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将《巴桑的大海》置于北疆文化建设视域下探讨,着力挖掘作品中呈现的北疆文化元素,探究小说在叙事方面对于牧歌等音乐元素的借鉴与突破,发现其民族书写对于“北疆文化”的诠释与传承,既包含了对于民族发展的关注与反思,也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北疆文化;《巴桑的大海》;海勒根那;牧歌叙事
“北疆”是中国北部边疆的简称,指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主兼及周边靠近北部边境的区域。“北疆文化”孕育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过程,是在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建设边疆的历史中凝练而成的地域文化,依据北疆这一地理范围和生活其中的人群展开的文学书写,将为“北疆文化”提供民族认同的鲜活叙事脚本和永恒的记忆标识。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北疆书写”便是生动一例,其笔下的“北疆”,作为书写资源的游牧美学元素也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作家海勒根那鲜明的文化基因,[1]在赋予其独特民族血脉和艺术气质的同时,也为其艺术呈现方式带来灵感。其小说作品《巴桑的大海》荣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其中的北疆文化印记,凸显着他作为蒙古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表达。本文将以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作品《巴桑的大海》为对象,挖掘作品通过牧歌叙事呈现的北疆文化元素,探讨其文学书写中对于民族发展的反思乃至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意义。
音乐叙事,顾名思义是借助音乐性要素为文学叙事延展其诠释领域。聚焦于蒙古族小说,众多有过游牧经历的蒙古族写作者常能自然而然地将其耳濡目染的草原之音引入创作,据此形成独特的叙事样态——牧歌叙事。“牧歌”是源自西方的文学术语,最初指古希腊时期牧羊人们用来描写其纯朴生活、歌咏爱情和哀悼死亡的田园诗歌。经演化,“牧歌”除作为体裁的名称外也被用以泛指田园生活以及与其相关文学创作,同时也作为一种民歌类别,指流行于我国蒙藏等少数民族间的一种即兴所至的歌曲,以音调开阔悠长、节奏自由欢快为主要特点。
我国蒙古族牧歌,是在草原文化影响下生成的民族音乐。蒙古族是我国北疆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性民族,游牧文化已作为文化基因深深嵌入其族群记忆并表现于相应艺术创作,形成了的独特游牧美学。在蒙古族小说中,牧歌除了作为表现地域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内涵的内容元素,还兼具抒情与叙事功能,并由此催生出独特审美内涵。牧歌叙事,并非仅仅是对音乐元素的引入和借鉴,与音乐相关的意象描写也远不只是诗情画意的点缀。因其对情感的触发和结构、主题方面叙事功能的承担,而催生出了蕴含丰富审美价值的游牧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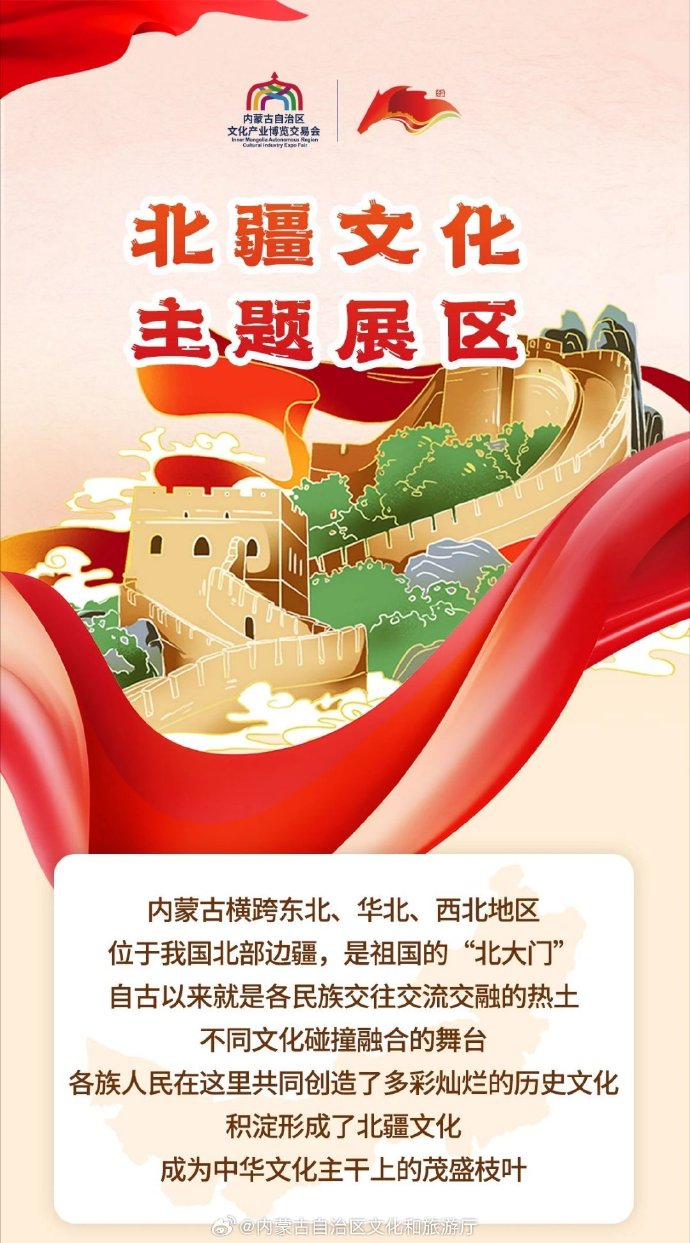
一、作为书写资源:边塞草原的地域色彩与文化空间
草原,作为景观出现本身便构成最直接的审美对象,自然状态下的草原风光借由作家之笔得以舒展,蕴含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巴桑的大海》中多次将日落时分的大漠余晖和夜幕初上的漫天繁星并置,主人公巴桑来找“我”和妹妹阿丽玛的夏日傍晚,“此时的草原宁静极了……太阳徐徐落到天边去,先是把一大片云霞的边缘熨红了,落日可真美!”[3]进而“太阳隐身后,余晖让它身后的晚霞火红了好一阵子。当头顶上泼墨般的流云渐渐消隐于黑暗,最后一条木炭似的晚霞也燃成了灰烬……直到星星在天空登场,一小块月亮原来是在南面的天空悬着的,却一直被忽略,现在终于显露出来,晶莹剔透。”[4]草原在作家笔下从明至暗,其宁静开阔与热烈延绵同时呈现,也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独异的自然场所。
除草原小说的典型景观外,同样辽阔的海洋景观为作品打开了更宽广的审美空间。在巴桑如约与杉蔻见面的那天,“海参崴秋高气爽,港口安谧,大海风平浪静,阳光和暖又柔软,像徐徐落下的金色绸缎,铺洒在蔚蓝的海面。”[5]从草原到大海,两个本自带浪漫属性的场景中,巴桑实现了对人生的跨越。作家的笔下之景也由意境式的抒情描写成为象征式的审美对象,一种能够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乃至呈现美感的艺术空间。
草原,同时也意味着一整套的文化价值、思维习惯和情感结构。“自然以自在的品格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6],草原文化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特定环境中与自然相互作用与选择的结果,因而不仅具有典型的草原生态特征,又孕育并承载了蒙古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结晶,滋养着生活其间的人民。小说借阿丽玛之口讲述的少年猎手海力布的传说,便是作者从科尔沁民间文学中得到的启示。
除了北疆自然景观,小说中还涉及丰富的蒙古族民间风俗、谚语俗语等人文景观,不仅体现着蒙古族的美学理想和情感表达方式,还积淀着蒙古族民间文化的精华,保存着蒙古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伦理观念、民风民俗和民族心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张力。
二、作为呈现方式:蒙古长调中的叙事技巧与艺术氛围
作家的成长环境使他在自然声色中获得音乐感受、情感体验乃至精神净化,并具象化于小说创作中。长调是蒙古族民歌的经典形式之一,长调悠远深沉而韵味无限,宛如蒙古族对上天的呐喊。[7]作家借助显在音乐之声,以游牧世界的古歌织构起牧歌般的美学意境,又在潜在层面借鉴蒙古族长调,将重复、复调等音乐技法引入借鉴于小说叙事,在回环往复的韵律中增强情感的张力,形成了独特的牧歌叙事。
(一)“复调”与“变调”:叙事结构
“复调”起先隶属于音乐范畴,巴赫金将叙事线索和音乐旋律作比,将叙事声音与音乐声部对应,使复调理论进入文学研究及创作的视野。游牧古歌中的长调,其中有一类就是复声长调,又名“潮尔音哆”,“意为具有共鸣的、合音的歌曲。”海勒根那就借鉴了长调的复调性音乐特征,在小说叙事结构与叙事焦点的交错变幻中激活了新的审美价值,其中最突出的是小说“复调”式的叙事框架。
小说的叙事结构以一场特殊的返乡旅途为主线,在运尸人“我”与呼尔德运送其故友巴桑尸体返乡的过程中,以呼尔德的回忆引入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巴桑及其追寻大海的故事。长调般的抒情表达为读者奏响关于巴桑生命的浩歌,描述着草原的雄浑壮阔、牧人的善良果敢和草原额吉的无私隐忍。
此外,本就跌宕的英雄故事还因“变调”手法的运用更加一波三折,在牧歌的欢唱之外,又回响起苍凉的悲音。小说不断进行变奏,主人公巴桑的追寻——被迫返回——再次追寻的故事结构,伴随游牧古歌得以实现,叙事节奏与音乐节奏形成对位,在古歌一唱三叹的曲调中,巴桑克服身体残缺征服蒙古马,又与马为伴,在马背上冲破命运阻碍,其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在主题旋律的重复和回旋中,与读者形成共鸣。
(二)“重复”与叙事节奏
“节奏是生命的基础,但并不为生命独有。”[8]音乐节奏,作为一种流动的时间形式整合音乐的速度、力度以及节拍,创造出音乐旋律与内涵。小说叙事同样需要节奏,海勒根那将重复的方法提炼,将之变形为小说中声音、场景、情节的重复,在小说中和谐分布,形成完整而有特色的牧歌式叙事节奏。
情节的重复是小说中最显而易见的。与老额吉相关的情节描写围绕额吉善良、慈悲的形象展开,其中多次提及、贯穿故事始末的那串佛珠,也在其不断重复出现后作为一种象征物具有了功能性,不仅使小说产生与异域性的神秘氛围,也肯定了这种宗教关怀意识作为信仰给予草原人民的鼓舞与力量。
而小说中关于巴桑骑马与赛马情节的多次描写,则更显示相似情节在重复与变动中创造出的叙事价值。巴桑不断尝试、最终克服身体障碍征服马背的情节本就颇具对人物的塑造功能和对读者的精神鼓舞价值,而与此相关的赛马情节也因对激烈的对抗场面的描述给读者带来刺激与紧张感。在作家对主人公骑马与赛马的数次相关描写中,故事随着巴桑对自我的挑战而不断推进,最终巴桑征服马背、征服敌人也征服自己所带来的精神震撼,则更为深刻。而相关情节节奏紧凑、场面激烈,不免给读者带来紧张感,作家又在其中插入的环境描写,使得作品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如同乐章。抒情中使人物情绪弥漫,重复中控制叙事节奏,更让读者关注到巴桑的主观感受,完成了抒情体验的共享化,也使小说结构趋于完整。
(三)“绵延”与叙事时空
音乐本就是时间性的艺术形式,能体现出时空上的流动变化。蒙古长调也往往音调绵延悠扬,与草原环境相融,形成了悠长的节奏形态,鲜明地体现着草原游牧文化特色和一种辽阔无垠的空间意境。[9]作家在小说叙事时间与空间的表达上借助音乐艺术特有的流动性,与自然的时空秩序形成同构,如一条河流,始于“水滴”的“叮咚声”,终而“海浪”的“咆哮声”,行文流畅如音符般流动不居,在音符的流动组合中,叙事的时空也获得拓展,于和谐状态中散发出流动之美。
在立体的空间维度上,作家借助长调的绵延对叙事予以开拓与延展。小说的表层结构以巴桑的“魂归”为架构,一路从高原行径城市、森林和草原,最终归于大海;在深层结构中,又以巴桑对大海的向往与追寻为核心,由草原观照大海,体现出长调般的广袤意境与胸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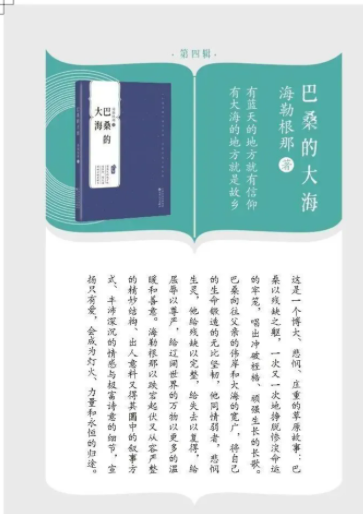
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作品不仅蕴含原始游牧文明,还囊括农耕文明甚至现代的工业文明,同时兼及西方海洋文明。在有限文本中,经由时空的延伸,显示着蒙古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永不设限的宽广恢宏,宛如长调在草原之上回荡。在牧歌般的风调中,寓言着主人公的生命追寻的完满。
(四)“一唱三叹”与情感基调
《巴桑的大海》对长调的另一借鉴处,是同样深邃低回的抒情基调和情感崇尚。与一般歌曲不同,长调有着丰富的层次变化,其“一唱三叹”的特点“主要运用乐汇的贯穿发展方式,乐句的长短不拘一格,又常常插入或长或短的衬词拖腔,因而其结构往往表现为非方整性。”[10]海勒根那在书写中以记忆片段的连缀成文,以求弱化情节而增添抒情性,使得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作品内蕴中又深沉着悲悯与浪漫。而小说中的长调又带有个体性和体验感,直奔人物内心,又通过人物最质朴的话语表达,应和着长调版的一唱三叹,产生极强的情绪感染力和艺术张力。
三、作为精神力量:北疆文化中价值追求与民族品格显现
民族精神发源于其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蒙古族长期生活在广袤无垠的边塞草原,在与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蒙古马般吃苦耐劳又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守望相助”的淳朴人性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与生命意识和“万物有灵”的宗教观与共同体意识等等,在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马背成就了游牧民族狩猎、迁徙、作战的梦想;作为精神支点,马昭示了蒙古族不朽的民族精神与力量。《巴桑的大海》讲述了身体残缺的主人公巴桑从草原到大海的艰难探寻旅程,巴桑克服身体残缺征服蒙古马,又与马为伴,在马背上冲破命运的阻碍。至此,马也作为精神意象见证了巴桑成长历程中自我超越的实现。
无所畏惧的巴桑,无私善良的老额吉,纯洁美丽的阿丽玛,还有一直关心帮助巴桑成长的牧民乡亲等等人物代表着生活在北疆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也显示着草原人民的人性之美与“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作为“守望相助”观念的极致体现与传承载体,小说中的老额吉形象也超越人物本身具有象征意义,慈爱善良、勤劳无私,是养育巴桑成长的老额吉的鲜明品格,也是无数草原“额吉”的共同特质。“额吉”,蒙古语中意为母亲,是草原上最普遍的女性群体,她们身上也恰恰折射着人类崇高的生命境界。在条件恶劣的草原上承受生活的艰辛,又赋予草原万物以无私关怀与爱。草原人民一生与草原紧密相连,在“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下,作家的环境描写在浪漫中又极富现实关怀。外来马戏团的介入象征着现代资本对传统游牧文化的入侵,日本捕鲨船非人道的行径更令原本平静的大海变得触目。作品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大量描写,即是通过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弘扬指斥人类盲目破坏自然的种种丑恶现象,也意在借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智慧,探寻现代观念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使传统生态观念发挥出时代价值。
纵观作品,能清晰看到作家突破民族主义的狭隘限制,表达对民族关系的构想——通过“雪路的相知”实现多民族和谐相处发展的愿景,也借小说传递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敞开自身、面向未来的智性思考。[11]
参考文献:
[1]海勒根那:草籽要到草原落地生根[J].滇池,2017年第8期.
[2]海勒根那:我的荒凉而忧伤的塞外草原[J].江南(江南诗),2020年第6期.
[3]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4]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6页.
[5]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3页.
[6]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7]孙硕.蒙古族长调艺术的美学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第22期.
[8]张洪模.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音乐美学卷[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第312页.
[9]潮鲁.蒙古族长调牧歌研究现状及思考[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0]包·达尔汗,乌云陶丽.蒙古长调[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1]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