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理性与感性——从理性主义到反理性主义思潮论文
2025-01-17 14:32:24 来源: 作者:liziwei
摘要:理性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理性精神赋予了我们思考与逻辑思辨的能力,让我们始终对追求真理保持着热忱。艺术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到工业革命以后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都反映着对理性精神的思考是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蒙德里安对艺术进行定义,认为理性能够创造艺术,而感性能够使艺术被欣赏。也许我们无法界定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理性还是感性所占的比重更为重要,但我们可以在对理性精神在艺术发
摘要:理性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理性精神赋予了我们思考与逻辑思辨的能力,让我们始终对追求真理保持着热忱。艺术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到工业革命以后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都反映着对理性精神的思考是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蒙德里安对艺术进行定义,认为理性能够创造艺术,而感性能够使艺术被欣赏。也许我们无法界定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理性还是感性所占的比重更为重要,但我们可以在对理性精神在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梳理,去窥探理性与艺术的交织与碰撞。
关键词:理性主义;感性主义;理性;感性
一、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理性精神
新古典主义的“新”,是相较于古典主义而言,以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理论为范本,刻意模仿古代艺术的法则,由此形成的艺术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当时的欧洲,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成为17世纪法国主要的思想,他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超越朴素的世界观,艺术应该受到规则的检验和衡量,只有通过理性的推演,才能证明艺术也包括含有纯正的、永恒的和本质的内容,这推动了欧洲社会理性精神的发展。他同时否认了先验性与感性的重要地位,认为对于美的判断只与被观察者本身相关,否定了绝对“美”“丑”的存在。虽然他并未系统对艺术认知进行阐述,但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却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与评判产生着重要影响。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新古典主义的法典,他认为“理性”是唯一值得追寻的东西,也是判断艺术的标准,强调要始终以理性为出发点,用理性来判断并衡量一切,要在艺术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理性的原则,要求诗人“提高你的格调吧,要从工巧求质朴,要崇高而不骄矜,要隽雅而无虚饰”。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绘画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理性,在形式方面反对感性推崇理性;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主义题材。大卫的《马拉之死》以简洁的布局与线条,将马拉的人物形象立体地呈现出来,既表现了马拉生活的朴实无华,又烘托了马拉的伟大,整个画面庄严肃穆。新古典主义认为艺术需要为社会服务,需要通过复古的手段表达理性,在创作中要尊重自然,尊重秩序,以理性表现真实,艺术要体现普遍永恒的人性,要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浪漫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以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在政治上反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的联合统治,在思想上反对古典主义思潮,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强调人的解放,重视人的主观感受,关注人的个性和精神的表达,注重描绘自然风光,歌颂大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中不含理性的表达。画家在绘画主题上主要寻找感性的奇思妙想,但在绘画技巧中则偏重于理性,也就是说在内容方面是感性的,但表现形式却是理性的。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都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的加工,体现着人的自由与解放,但在色彩与线条的运用上都继承了传统的绘画技法,是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理性精神达到了新的高潮。内容的感性与形式的理性相结合,在表现人主观情感的同时,也推动了理性主义的发展。但是在这背后,一场反理性主义运动正在酝酿,一股新的思潮正在悄然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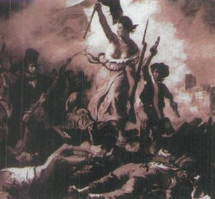
二、反理性主义思潮
理性主义在西方近代达到了全盛的时代,使西方人从中世纪神权和王权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被高高举起,他们开始不断对外在世界进行探索,发展知识科学技术,就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将知识和对象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知识,即符合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从而使哲学的目标从探索外部世界向探索人的内在世界转变。康德“将感性视为将一切纳入直观的能力,有别于知性将一切纳入概念的思维活动。感性完善性即直观的明晰性与真理性,有别于逻辑完善性即概念的明晰性与真理性。”到叔本华,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而理性则是意志的工具,批判了理性主义。尼采也认为人们盲目相信科学的万能性,极致推崇理性主义,这会使人们对人生的判断偏离方向,不能找寻真实的意义。在尼采的观念里,世界变幻无常的,一切都会转瞬即逝,这才是真实的世界。但正因如此,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虚伪、残酷和矛盾,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痛苦不堪的世界。想要从这个世界中脱身,只有依靠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将人从痛苦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家园。
艺术对于尼采来说,是满足生命需要的一种方式,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是生命固有的活动,是意志本体的本源性的创造活动。艺术如同呼吸一样,是人生存所必需的。尼采认为在这一点上,最为值得借鉴的是古希腊人的经验。他们的生活环境充满了阳光,每天生活得十分欢乐。在歌德、席勒看来,这是因为他们达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感性与理性也正好达到了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的和谐”。但尼采却认为古希腊人的快乐并不是由于内心的和谐所导致的,相反,却正是由于内心世界的冲突所导致。他们更加热爱生命,也更加能体会到生命的本质是悲剧。他们为了从这种痛苦中逃离出来,于是对艺术和美的追求更加热烈,从而赋予生活以更深刻的意义,去寻找新的快乐。这便是酒神精神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古希腊神话归结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样一对概念,酒神代表着音乐艺术,而日神则代表着造型艺术,古希腊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就是这两种精神的独立与对立的存在。尼采进一步阐释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并以此为突破口对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深入探究,从而重新审视古希腊文化,最终将其引向强力意志的更为深邃的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社会和人都拥有着健全而强大的人格,他们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有无限的创造激情,这是因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作为悲剧中的两个因素,都对人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现实的生活是充满苦难与不幸的,但由于日神的照耀,人们会产生美丽的幻想,这层美的面纱使人生本来的真实面目被掩盖起来,使人鼓舞起来,重拾信心,人生拥有了希望。通过颂扬现象的永恒,日神能够克服个体的苦难,战胜生活的烦恼,使人对生活又有了向往。同时,酒神能够“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快乐的”,酒神精神能够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得到和解,万物之间和谐,人摆脱了个体性的束缚,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世间万物合为一体,大生命得到显现。但是在悲剧之中,酒神精神也不会导致人的过度纵欲和过度泛滥,因为他总是能够受到日神精神的制约,由此二者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
在酒神精神的基础上,尼采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这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一切价值之重估,这就是我对人类最高自己认识行动的公式,这种行动已成为我的血肉和天才。”尼采对欧洲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地审视,对科学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尼采认为,既然世间万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就不应该存在所谓的最高价值。在理性主义思潮爆发之前,上帝就是最高价值,人们将所有的希望同时也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上帝,成为人活下去甚至死亡的唯一理由。但如今“上帝已死”,被基督教以上帝之手之名创造出来的一套价值体系即将轰然倒塌,人们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精神支柱,彷徨无助,在一个没有价值的虚无之中四处游荡。人们要想重新找到方向,不能再去外物寻找依靠,应该重新审视自我,相信并依赖自己,使自己成为价值的立法者。为了弥补上帝之神带来的空虚,人们应该以勇敢的行动去填补,为自己创立新的价值。尼采能勇敢地向世界宣称:“价值评论的转变——这是我的任务”。
重估一切价值,就是将虚假的科学精神和虚伪的道德精神取而代之,而代替它的正应该是肯定的人生的审美精神。“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在尼采看来,只有酒神精神才能将人生视为审美现象,因为只有它能够使人放纵不羁,使人将人生也视为一场巨大的游戏。尼采从理性的逻辑层面对其进行批判,“他认为,理性依据逻辑而生,它本质上是对逻辑的迷信,是逻辑虚构出来的体系。这种迷信使得理性主义者将逻辑、理性作为人和世界的本质。但是,尼采从逻辑的起源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逻辑来自非逻辑,它产生于人的日常。”尼采将酒神精神作为武器,对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欧洲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打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将美学限制在理性主义范畴内的逻辑思维,将美学从理性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为美学构建更广阔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内容打开了通道。
三、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的关系
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理性的代表,而艺术往往被当作科学的对立面,认为艺术是人感性的产物,似乎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感性与理性在艺术的表达中不可兼容。但其实从艺术的产生之初,感性与理性就是不可分割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在拥有情感的同时可以进行理性思考,这是人类的本能,它迫使人们在感性思维的同时进行理性地思辨,从而对外在事物进行改造,促进艺术的发生。以反思的判断力为特征的艺术理性,是人类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容、规律的主要思维形式,是一种高级的、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活动能力。从古希腊时期理性便渗透到了艺术之中,理性的思维方式成为古希腊哲学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苏格拉底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认为追寻真理是人生的重要目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就是数的和谐,“和谐”是一种审美形式法则,美是建立在和谐比例之下的,艺术的形式美就是建立在数的比例关系之上,美就是和谐的统一。柏拉图更是将世界分为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只有理念世界才是永恒和完善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都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在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中,理性与感性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而感性长期处于理性之下,近代哲学家笛卡尔依然对感性持反对态度,认为感性是不完善的存在,干扰了理性的认知,会对理性产生消极影响。莱布尼茨开始对二者关系进行反思,虽然感性认知是“清楚浑浊的”,并不能像“清楚明晰的”理性认知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满的关于对象的认知,但对象的复杂性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多感性特征,其中也蕴含着丰富且多维的认知。
直到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提出“感性学”,也就是先验感性论,感性才被放到与理性平等的地位被思考。康德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认知,认为知识是外在于我们自身,需要通过努力去向外部寻求;知识是“先验的”,也就是“先天的”,是在经验之前的,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只是需要通过外部对象去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使我们对“自在之物”产生反应,这就是我们“感性认知”的过程。康德对感性认知过程和对象加以阐释,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和价值,推动了人们对于感性的进一步探究。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受到莱布尼茨等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对感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Aesthetica”一词,虽然今天被翻译为美学,但其本意为“感性学”,是感性独立的标志。鲍姆嘉通认为感性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对逻辑的完善性有促进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其弱化了传统理性主义中理性与感性的完全对立状态,将感性从“低级认知”的固有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正视感性在认知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并发展了美学这一学科,将“美”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感性认知中的普遍美。
艺术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更是在黑格尔处得到了判断,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真,就它是真来说,也存在着。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美因此可以下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是“真”,是最高的真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艺术是通过感性事物将绝对理念“显现”出来,成为能被观赏的艺术作品。但这种“显现”是有条件的,需要达到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才能使绝对理念以美的形式呈现出来。至此,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得以明确,艺术中既需要理性因素,又需要感性因素的参与,只有当二者达到契合无间时,才能产生美。艺术的理性精神有了发生的可能,感性的丰富与理性的哲思推动着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四、总结
从理性主义到反理性主义思潮,反映的是人们对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在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不断探讨。从最初柏拉图提出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总是试图通过提升自身的能力去创造出更加接近自然的事物,理性主义在艺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艺术只是机械地描绘外部世界;到后来,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的情况下,人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努力挣脱自然与理性的束缚,借助艺术表达更为真实的自我感受,注重精神世界的表达,由探索外在转为探索自我,感性主义在艺术中逐渐被认知和重视,人更加重视对自身的探究,重视内在体验,重视如何将这种感性体验通过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自身有了更加明晰的认知,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也不断地被创造、被发展,艺术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表达,艺术不再是其他事物的附庸,艺术更能成为艺术本身,艺术的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逐渐达到和谐统一,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
参考文献:
[1][法]布瓦洛著.任典译.诗的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
[2]薛霜雨.鲍姆加登的感性学与康德的感性论——基于认知与审美的考察[J].文艺研究,2023(11).
[3][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84.
[4]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4.
[5][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74-75.
[6]张姚.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理性主义思想比较研究[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2020.
[7][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9: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