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中观女性形象的塑造论文
2024-11-30 15:57:14 来源: 作者:liziwei
摘要:淄川区聊斋俚曲剧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根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编排了许多剧目,深受大众喜爱。女性形象在俚曲中占半壁江山,无论是从文学方面还是音乐方面都值得深入研究。
淄川区聊斋俚曲剧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根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编排了许多剧目,深受大众喜爱。女性形象在俚曲中占半壁江山,无论是从文学方面还是音乐方面都值得深入研究。
一、谈从小说到俚曲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在当代社会,女性群体更受大众关注。文学、戏剧、影视等各个领域的一些新作品中都从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女性人物形象。笔者在研读前人文章后发现在音乐方面关于女性形象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择通过分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俚曲以及现在的聊斋俚曲来探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以《珊瑚》为例,从文学与音乐的视角来探究这个问题。
(一)《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缺失了独立人格,但《聊斋志异》中却描写了一些蒲松龄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形象,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形象,忠于夫君、忠于家庭、甘于奉献的女性形象,有勇有谋的女性形象。
其中,忠于夫君、忠于家庭、甘于奉献的女性形象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当时的社会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女子嫁人之后应遵夫命,即使婆家对其百般刁难仍需选择隐忍,可见当时女性受夫权的压迫,社会地位极低。蒲松龄在书中既赞扬了此类为家庭付出的女性,同时也鼓励受压迫的孝媳妇冲破思想的束缚。例如,在《珊瑚》中,大儿媳珊瑚贤淑孝顺,但婆婆沈氏却对珊瑚百般挑剔,将珊瑚休出家门。沈氏小儿子娶了臧姑,可是臧姑生性凶悍,不久就把婆婆气病了。蒲松龄在这个故事中主要塑造了恶婆婆沈氏、大儿媳珊瑚、二儿媳臧姑这三位女性形象,其中用“悍谬不仁”“触物类而骂之”“恶言诮让”等来形容婆婆沈氏的为人;用“母谓其诲淫,诟责之”“惟其不能贤”来形容婆婆沈氏对大儿媳珊瑚的态度。大儿媳珊瑚对婆婆沈氏的态度书中描写道是“遇之虐,珊瑚无怨色”“当怨者不怨”“当去者不去”。对于二儿媳臧姑的悍妇性格,书中写道“骄悍戾沓”“时有陵虐”,并以“母或怒以色,则臧姑怒以声”“役母若婢”来形容臧姑对待婆婆沈氏的态度。珊瑚这一角色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下大多数女性的现实情况,与臧姑这一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对婆婆的态度不同,前者是逆来顺受,后者是反抗。虽然臧姑在蒲松龄笔下也是反面形象,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少数女性对封建礼教束缚的不满以及她们想要突破桎梏的态度。
(二)蒲松龄的聊斋俚曲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故事鬼神色彩略有减少,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其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上文提到的“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形象”以及“忠于夫君、忠于家庭、甘于奉献的女性形象”。上文提到的《珊瑚》在蒲松龄的聊斋俚曲中被改编成《姑妇曲》,其中对孝贤媳妇珊瑚、恶婆婆于氏(在蒲松龄的聊斋俚曲中《姑妇曲》中婆婆这个角色由沈氏改为于氏)以及悍妇臧姑的描写也更生动形象。曲牌中的唱词将人物塑造得更为立体鲜活。《姑妇曲》在“劈破玉”中描述了珊瑚的孝贤“又孝顺又知礼,一点儿不错。不说她为人好,方且活路多:爬灰扫地,洗碗刷锅……黑夜纺棉织布,白日刺绣绫罗,五更梳头净面,早早伺候婆婆”。在“倒扳桨”中描述恶婆婆“媳妇终日不从容,婆婆闲的皮也疼。不知心里还待咋,终朝吵骂不停声,不停声,好难听,人人说是糊涂虫”。在“倒扳浆”中描述臧姑的泼悍“常见家家要娶媳妇,只当是娶来要做娘;要做娘,气昂昂,婆婆亲来不下床”。
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朝着生活化方向发展,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群众,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依旧是他创作的重心。
(三)当代聊斋俚曲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学界关于音乐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显著发展,主要搜集有关女性的音乐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性别概念形成,并产生了四种观点:强调“性差异”的社会性别观、强调“地位”和“角色”的社会性别观、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别观、强调过程的社会性别观。在人类社会中,女性同男性一样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女性群体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发现社会生活中不同性别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社会性别、社会地位与涉及社会性别的音乐行为之间的关系。
当代聊斋俚曲以慰藉农人、教化百姓为初衷,通过故事的形式向观众传递。笔者主要对《珊瑚曲》进行分析,通过对剧情、唱词以及旋律的分析来探究俚曲中的女性形象的特征。这里提到的《珊瑚曲》实际上是在2009年写成的,其是根据蒲松龄的聊斋俚曲、《聊斋志异》以及蒲松龄写成的传统曲牌中的故事改编的,在服装扮相上要求穿古装戏服。
二、《珊瑚曲》个案分析
(一)从剧情上观女性形象
聊斋俚曲《珊瑚曲》创作于2009年。在人物角色方面,《珊瑚曲》中塑造了四位女性形象,分别是大儿媳珊瑚、二儿媳山菊、恶婆婆臧弥陀、珊瑚的救命恩人何氏。但何氏这个人物在其中起过渡作用,人物性格不太鲜明。
文学作品《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两位悍妇,分别是恶婆婆沈氏和二儿媳臧姑,二儿媳臧姑原本为人嚣张跋扈,在故事中坏事做尽,遭报应之后才改邪归正。但在聊斋俚曲中,二儿媳山菊为人本就正直善良,她气不过婆婆逼走珊瑚,为了替大嫂出气同时也不想自己变成第二个珊瑚才“虐待”婆婆。在《珊瑚曲》中,第一场悍妇虐姑,珊瑚遭虐待被逐出家门;第二场知遇尽孝,珊瑚被逐出家门一心求死但被何氏救下,认何氏当义母;第三场打渔救女,珊瑚和义母打渔的时候偶然救下了落水的山菊;第四场以暴抗暴,山菊在大嫂被逐之后嫁进门,她为了不做第二个珊瑚要整治恶婆婆;第五场施粥行善,恶婆婆被山菊虐待,饿得逃出家门,正巧遇见在施粥行善的珊瑚,珊瑚听闻婆婆受苦则想上门找弟媳理论;第六场解怨结缘,珊瑚找到弟媳理论,山菊认出来这是她往日的救命恩人,也被大嫂的重情重义感动,一改往日作为,妯娌二人共同孝顺婆婆。
(二)从唱词上观女性形象
剧中塑造了三位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从她们的念白与唱词中能够看出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恶婆婆藏弥陀这个角色的名字由来在剧目一开始有了交代,“藏氏吃斋又念佛,人送外号藏弥陀”,但这位弥陀的所作所为却与“吃斋念佛”的形象大相径庭。她认为“摊上个媳妇把命夺”,视大儿媳珊瑚为眼中钉,在生活中处处刁难。
孝媳妇珊瑚身上呈现出孝顺与善良两种性格特点。她对婆婆百依百顺,“甭管婆婆咋横立,我要忍让担待着”。被婆婆百般刁难并逐出家门后,她唱“被逐出门何处去,不如一死了羞耻”,认为被逐是一种羞耻。由此可见当时女性地位的卑微。珊瑚心地善良,体恤生活困难的乡亲,九月九日施粥行善。“咱母女俩同心来舍粥,行善积德肝胆照”的唱词体现了珊瑚善良的性格特点。
对于二儿媳山菊,编剧一改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二儿媳臧姑嚣张跋扈的性格,在《珊瑚曲》中,山菊的所作所为更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在第四场以暴抗暴中,山菊看不惯婆婆的所作所为,唱道:“她捏俺嫂子软柿子,现如今又想把我来拿下,我要做个刺猬叫她拿,和她以牙来还牙。”同时从山菊的自白“我呀,也不是那不讲理的……我就是想治活治活她,为人家珊瑚出出这口气,想叫我做珊瑚第二,没门!”中也可以看到与旧社会大部分女性不同的另一种女性的形象。她面对不公敢于反抗、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可以说,编剧将现代女性的精神融入了山菊这个角色。
(三)从唱腔中观女性角色的塑造
藏氏“俺要那”唱段的调式是F宫调,沿用了传统曲牌“房四娘”的宫调式特点表现人物强势的性格。该唱段出现了大量的纯四度跳进,大多都是下行的,说明人物情绪是负面的。如图1所示的第二句至第四句,句间进行都是sol-mi的级进。第二句起音落音都在sol上,第一小节是级进上行到la,而后有la(低)-re、re-sol的五度、四度跳进。第三句起音mi落音sol,主干音mi-sol-la,以四度跳进为主。第四句起音落音都是mi,主干音do-mi-sol。由此可以看出,句内逻辑以四度迂回跳进为主,句间逻辑以级进为主。音程的跳进再结合唱词所表达的内容,恰好体现出藏氏的刁钻性格。

如图2所示,第八句可以说是这一段的高潮句,连续用了两个la-mi的下行四度跳进,唱词是“快去淘换来”,可见这一句是全曲情绪最激动的一句,前面内容做了大量铺垫,这一句恰好最能体现人物的刁钻性格。
![]()
珊瑚的“珊瑚我”唱段是B羽调的调式风格,奠定了珊瑚无奈、悲伤的情绪基调,珊瑚唱段中借鉴了反“叠断桥”的典型乐句,通过节奏的变化将旋律扩充,但是主旋律形态不发生变化,而且保留了re-sol(低)与sol(低)-si(低)的纯五度与大三度跳进,前奏部分先交代情绪,纵观整段,塑造了珊瑚委屈、忍辱负重的形象。图3中将传统曲牌与珊瑚唱段进行比较。唱词的行腔很长,一个字常常占多个小节,可以看出珊瑚的这个唱段表达了无奈的心情,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软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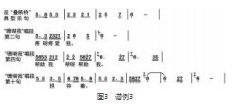
对于山菊恼羞成怒的唱段,该唱段念加唱共10句,落音羽徵羽(低)商角羽(低)角商羽,是D羽调。这个唱段中有许多跳进,且音程跨度比较大,这些跳进是为了配合唱词,该唱段音域较宽且集中在中高音区。由此可以看出,旋律的发展符合人物正义、不甘示弱的性格特征。图4呈现了第三句的旋律。开头就出现了la-mi的四度下行跳进,第二小节是整句的最高音,强调“母夜叉”,而后旋律级进下行,第五小节有小七度的大跳进,再次强调“母夜叉”,可见山菊对婆婆的不满情绪在加强,随后旋律级进下行落在羽(低)音,有巩固调式的作用。
![]()
图5呈现的是第五句的旋律。前四小节都是级进,到第五小节出现上行小六度跳进,第五和第六小节有整句最高音,以强调“软柿子”。以上这几小节音程的大跳进具有肯定、开阔的感受,先铺垫了山菊对恶婆婆之前行为的不满,体现了山菊敢于与不公对抗的性格特征。最后“和她以牙来还牙”重复两遍,更说明了山菊不甘示弱、敢于反抗的性格。

三、俚曲中女性形象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变化
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思想对女性来说是桎梏,但是蒲松龄在他的作品中却塑造了一系列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一)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封建社会中的女性面对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即使面对命运的不公也只能无奈地忍气吞声。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伦理观念有直接联系。
第一,社会环境。封建社会中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几乎都是以男性为主,而女人的职责是在家相夫教子。古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其中包含了男性与女性在物理空间上的内外之分和性别分工上的内外之别。此后,“男外女内”的思想在历代家训和女教书的阐释下,经过唐宋时期的平民化和明清时期的习俗化,逐渐内化为女性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民间习俗规范。这种思想限制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她们没有经济来源,话语权也大大降低。
第二,封建礼教。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决定了她们的悲惨命运,例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指女性一旦出嫁就与娘家没有关系,蒲松龄笔下的珊瑚被婆婆逐出家门后先想到的不是回娘家求助,而是一心求死,认为再回娘家是一种耻辱,可见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荼毒不浅。前文提及从《聊斋志异》到聊斋俚曲中几位女性角色的称谓变化,二儿媳称谓变为“山菊”,说明作者想重新将其塑造成“刀子嘴豆腐心”、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恶婆婆在俚曲中改名为“藏弥陀”,其精髓就在“弥陀”二字,她的嚣张跋扈与吃斋念佛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蒲松龄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只是一种愿望。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现实中男女的不平等,但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文字来抒发心之所愿。他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二)社会发展与女性思想的解放
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深受“三从四德”的荼毒,女子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以嫁人为最终的人生目标,这种封建思想使得女性的一生都难逃被压榨剥削的命运。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女子教育问题看作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并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必然路径。维新派提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口号,xxx也提出了自己的女学强国论,认为要改变女性的地位,则必须使女性接受教育、学习科学知识,在教育上享有平等权。近代以来,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促进了女性解放。蒲松龄在书中对理想女性的畅想照进现实,女性同男性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有从政经商、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有面对不公大胆说不的权利。
聊斋俚曲发展至今同样应该站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创作,像《珊瑚曲》这种通过传统新编的形式对剧情加以改动、对人物形象进行再塑造也表明了新时代思想的注入。
(三)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契合点
通过前文对文学与音乐两大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古今思想的对话。其中传统与现代的思想契合点中,最重要的是对孝道的认同。
从《聊斋志异》中的《珊瑚》到蒲松龄的聊斋俚曲中的《姑妇曲》再到当代聊斋俚曲《珊瑚曲》,其中传达的核心思想就是孝道。“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时至今日,虽然对孝道的解读发生了变化,但核心还是在于要敬老、养老。《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聊斋俚曲中的孝体现在“孝顺”,大儿媳珊瑚一味顺从婆婆,面对婆婆的百般刁难没有一句怨言,被逐出家门还一心求死。笔者认为这种孝是愚孝,孝并不是委曲求全、事事顺从、牺牲自己,正是因为珊瑚的事事顺从才导致婆婆越来越嚣张跋扈,所以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蒲松龄要纠正恶婆婆的错误思想,安排了二儿媳这样的悍妇与之对抗。如今对孝的解读更多在于“敬”,应尊敬长辈而不是一味顺从长辈。因此当代的聊斋俚曲《珊瑚曲》对人物进行再塑造,其中变化最大的二儿媳“山菊”这个角色不甘于忍受恶婆婆的欺凌,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在山菊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的价值趋向是孝敬而不愚昧。
聊斋俚曲剧团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以发扬俚曲。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其不仅新编传统而且大胆创新,创作出多部优秀剧目。在新时代,俚曲创作应契合新思想观念。当下,多部新剧目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歌颂了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无论从剧情还是音乐,对人物性格的描写都细致入微、深入人心。蒲松龄在他的作品中对理想女性的塑造现如今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