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镜中的日耳曼天才——评艾瑞克·莱维《莫扎特与xx》论文
2024-11-01 17:06:19 来源: 作者:liziwei
摘要:本文以艾瑞克·莱维的《莫扎特与xx》一书为评述对象,归纳了书中所述xx执政期间以莫扎特作为“文化武器”来达成政治目标的具体措施、时效状况和后世影响,并分析了xx此举失败的多方面原因。文章认为,xx当局在片面强调莫扎特音乐中的民族性因素时,轻视了对莫扎特音乐的本体解读,误解了莫扎特音乐的实质,以及造就“音乐伟大性”的关键条件。
摘要:本文以艾瑞克·莱维的《莫扎特与xx》一书为评述对象,归纳了书中所述xx执政期间以莫扎特作为“文化武器”来达成政治目标的具体措施、时效状况和后世影响,并分析了xx此举失败的多方面原因。文章认为,xx当局在片面强调莫扎特音乐中的民族性因素时,轻视了对莫扎特音乐的本体解读,误解了莫扎特音乐的实质,以及造就“音乐伟大性”的关键条件。
关键词:莫扎特;xx;文化武器;民族性;伟大性
一、引言:背景与意图
“一战”落败的德国受到战胜国集团的多方压制,债台高筑,更面临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侵袭,政府摇摇欲坠,人民惶惶度日。此时不仅是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共同渴望着能有一股民族的精神力量来支撑眼前的困境——xx团体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怀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野心,他们费尽心思地将精挑细选的日耳曼历史文化名人拉入自己的阵营,并标榜为“德国文化遗产真正的保护者”(详参《莫扎特与xx》第20页,后文页码标注皆为本书页码)。在其趁手的文化“武器”中,不乏重要的德奥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都在这种情况下为其所用。xx政府自然不是欧洲历史中歪曲、挪用艺术家来宣传自我以稳固政权的首例,但就其所作所为的坚决和彻底程度而言,却罕有匹敌——虽然这个过程并非全然顺利。
瓦格纳因留下了言论证据(如其于1850年匿名发表并在1869年瓦格纳重新修改刊印的论文《音乐中的犹太主义》)。而为第三帝国领导者提供了诸多便利,贝多芬也因其斗争意识和革命信念而不幸“被”当成了作曲家中的“原型xx”(第21页),而至于莫扎特,似乎其人其乐都与xx精神无甚瓜葛。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这便是莱维《莫扎特与xx:第三帝国对一个文化偶像的歪曲滥用》一书的核心论题。本书整合利用了xx正式上台直至德国战败这十来年间留下的大量文献资料,除涉及德国境内的政治和音乐活动外,还包含了同时期来自英、美及各国音乐界的不同声音,由此全方位地还原出了第三帝国在将音乐家莫扎特包装为xx拥护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及其对策。
作者艾瑞克·莱维系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客座教授,兼任抑郁音乐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uppressed Music)学术指导,曾在剑桥大学、约克大学、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求学,是20世纪德国音乐——尤其是xx政权时期的德国音乐——的权威研究专家。除本书外,他另著有《第三帝国的音乐》(1994)以及多篇关于20世纪音乐的专论文章。《莫扎特与xx》一书所提供的史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丰富,囊括了当时的著作、报刊、信件、演讲稿乃至音乐节海报、节目单等原始资料,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
言归正传。xx究竟为何对莫扎特如此执着?又是如何利用他的呢?
首先,莫扎特虽是奥地利作曲家,却与德国人同是日耳曼族人。莫扎特的天才名分自然使他成为渲染“种族优越论”的典范例证,被认为能在“一战”后德国的危急情势下凝聚民众,并“号召年轻人为艺术参战”(第205页)。其次,强调莫扎特这位奥地利人的“日耳曼民族”身份,可以美化xx意欲吞并奥地利的战争目的:莫扎特一旦“成为”德意志爱国者,便可为德奥最终合并的“文化同源”进行铺垫,为“吞并”避嫌,使之看起来像是一种“回归”。再次,莫扎特的音乐不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作品在曲调上通俗明快,易于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因而成为“文化武器”的绝佳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xx歪曲莫扎特的同时,海外的音乐家们(尤以英美两国为最)也在与之相抗衡。这场看似具有颠覆性的莫扎特音乐遗产认知与继承之纠纷,实际上为期不长,xx苦心经营的“德意志包装”在其政权垮台后也即刻败露,莫扎特的形象并未因“xx化”而沾上抹不去的污名。

二、措施:“德意志化”与“去犹太化”
莫扎特之于xx,是一个矛盾与可能性共存的“大麻烦”。为了对其进行全面改造,xx采用了多种手段,本书所述其强占莫扎特音乐遗产为己用的主要手段可被归结为两种:“德意志化”与“去犹太化”。
“德意志化”主要应对的是莫扎特是奥地利人而“德国性”在其作品中暧昧不明的问题。第三帝国当局首先蓄意摘取了莫扎特所留文字中对之有利的片段(如书信中出现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荣耀”等字眼,第24页),以佐证这位作曲家的“爱(德)国之心”。而毋庸讳言的是,被抽离语境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的措辞,在意义上是模糊不清的。为攻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节,第三帝国当局不仅禁止德国艺术家参与这一活动,还大幅增加国民越境参加音乐节的课税税款,更不惜采取在音乐节现场恐吓游客、大肆散发xx宣传传单等手段,导致高度依赖旅游业收入的奥地利经济遭受重创(第127页)。然而反讽的是,1938年奥地利终被吞并之后,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节却反而成为第三帝国自我宣传的捷径,用于上演经过xx当局审查与改造的、符合其民族主义主张的作品。
在各种形式的音乐作品中,带有文本的音乐似乎最容易表明“意图”,莫扎特的经典歌剧因而首当其冲成为被xx篡改和利用的对象。xx当局除了将其作品改编为爱国颂歌(第27页)之外,还声称德语才是最符合莫扎特作品文化根本的“母语”,于是积极开展了针对《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等歌剧的德译和改编工作,全然不顾其音乐中的意大利传统和法国因素,并刻意避开风格要素大谈人物性格刻画中展现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的德国性。但这样的片面解读难以在音乐中找到令人信服的依据,因此这些“德意志化”了的莫扎特歌剧版本,在德国及德国占领区之外很快便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如流亡海外的德国指挥家弗里茨·布什(Fritz Busch)与制作人卡尔·艾伯特(Carl Ebert)执掌的第一届“格林德博恩莫扎特音乐节”,在招募演员时就明确提出要求:莫扎特的歌剧必须使用其原初的创作语言来演唱。结果是他们以高质量的演出效果证明了欧洲大陆将莫扎特作品强行“德意志化”的失败——因为它没有开发出新的艺术价值,反而是不合时宜地强化了“地方习气”(第120页)。
相比“德意志化”而言,如何将莫扎特“去犹太化”令xx当局更感棘手。xx主义强调种族优越性,认为占用大量生存空间的一些民族,即没有国家做后盾的犹太民族,应被奴役甚至肃清。若莫扎特与犹太人挂上了钩,必然就站在了xx的对立面。因而对xx而言,莫扎特的“去犹太化”刻不容缓。莫扎特与犹太人的牵连主要源自两件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是与他密切合作的剧作家达·蓬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二是莫扎特所信奉的“共济会”组织也被认为与犹太人大有渊源。
犹太剧作家达·蓬特参与了莫扎特三部重要歌剧的脚本创作,xx所采取的行动与其上台后驱逐境内犹太音乐家时的手段雷同,不外乎诋毁其人格、抹杀其贡献,以彻底将其污名化。xx分子攻击这些作品的剧情设置,并借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对《女人心》的道德观所提出的质疑,来指责达·蓬特的脚本是二流的、庸俗的,再由此反衬莫扎特那天才般的超凡创作能力。“一刀切”式的评价对达·蓬特这位多产的诗人和剧本作家来说并不公正,一部歌剧的成功必然是剧本和音乐共同作用的结果。莫扎特曾在1783年5月7日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台本的挑剔和对达·蓬特的肯定[2]。虽然这并不能体现二人其创作期间的相处细节,但莫扎特最终选用达·蓬特修改的剧本完全是出于本人意愿,因此其剧本质量也应当得到了作曲家的认可,否则莫扎特也不会一再与之合作。xx当局不仅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一事实,为了将莫扎特的反犹主义诠释得更真切,他们还以尊重原作为名对一些作品的剧情做了大幅度修改。时任帝国音乐局长的理查·施特劳斯领衔制作的新版《伊多美纽》即一例,其中因爱生妒的“埃莱克特拉”一角被替换成了为维护种族纯净而阻挠男女主角结合的海神女祭司,其用意不言而喻。
共济会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组织,其源头与古犹太教的传说有所关联。18-19世纪,共济会会员中有不少犹太富商(包括为莫扎特提供资助的共济会兄弟),还被xxx定性为“犹太人的密谋机构”(第40页)。此外,共济会所秉承的平等、反专制、反民族歧视理念也与xx的暴虐行径相去甚远。而为了贬低和淡化莫扎特与这一犹太组织的关系,xx当局利用了莫扎特死因的争议,刻意支持“共济会毒害莫扎特”的阴谋论,谴责共济会对莫扎特实施的种种“迫害”;针对莫扎特笔下与共济会相关的作品,则选择对其中的共济会精神避而不谈。莫扎特笔下最能体现共济会精神的作品是他的歌剧《魔笛》,剧中直接描绘了共济会入会仪式的细节,而且还在三位侍女、三个仙童、三次考验等情节上暗示了具有共济会象征意的数字“三”。剧中萨拉斯特罗这一主宰智慧、象征光明的人物形象,据说源自共济会的精神领袖波恩,光明战胜黑暗的剧情脉络,也体现了共济会的信条。凡此种种,似乎使得xx当局无法简单粗暴地通过“修正”剧情来剔除《魔笛》中的共济会因素,于是他们便尽量淡化共济会符号,着重强调其中的魔幻性、童话性内容。
xx这样做,能取得成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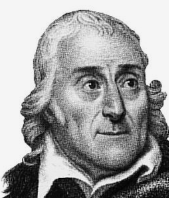
三、时效:外界的质疑与应和
在xx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进入“最终解决阶段”前极力尝试着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一方面是限制和打压犹太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又主动建立起“犹太文化联盟”,以便让失业的犹太人继续从业。这一矛盾行为部分是了应对人才大量流失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清洗”前的缓冲。在此背景下,有能力不受缚于此的犹太人纷纷设法逃离德国,流散异邦的音乐学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离散群体,并与xx保持对立。与此同时,得以从xx监视下“出逃”的犹太富人也转移了属于自己的大量藏品,包括热心的收藏家及“莫扎特迷”——保罗·希尔施(Paul Hirsch)。希尔施在1936年离开德国时,悄悄地带走了其所在图书馆关于莫扎特的全部藏品,其中就有珍贵的莫扎特手稿。这些资料日后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同时也xx于xx)修订克歇尔目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二人还合作编订了莫扎特十首著名弦乐四重奏的曲谱,成功在伦敦出版。而反观此时纳粹操控下的德国莫扎特学者,则陷入了“难为无米炊”的尴尬境地。
当第三帝国兴致勃勃地炫耀德语版《费加罗的婚礼》如何具有“德国性”时,身处xx的捷克xxx保罗·奈特尔(Pual Nettl)在《纽约时报》中一针见血地驳斥了这一荒谬意见。奈特尔注意到:莫扎特是奥地利人,剧本作家是威尼斯犹太人,剧本的来源是戏剧中最具法国性的人物——博马舍,而且其“场景设置在西班牙”——这样一部作品的“德国性”怎能令人信服?质疑声不仅仅源自xx(前文曾提到英国“格林德博恩莫扎特音乐节”要求用意大利原文演唱该剧),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采用了另一种极端的做法:用犹太语译本演唱莫扎特的清唱剧《解放了的伯图里亚》,用希伯来语演唱《后宫诱逃》。虽然这些演出在艺术质量上差强人意,但在当地却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当地的犹太人带来了极大的慰藉,以至于当地人“越来越喜欢莫扎特”。这一现象与所谓的莫扎特“反犹”说构成了尖锐的反讽。小说家安内特·科布尔在审视过莫扎特的时代、立场与音乐性格后总结说:“莫扎特内心始终是个和平主义者。”实际上莫扎特那充满慈悲与真爱的音乐是xx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
在流亡异乡的德国犹太音乐学家中,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的影响力最不容忽视。1933年,爱因斯坦离开德国,在英国、意大利辗转六年后最终移民至xx。在此期间,他对莫扎特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其中就包括编订“克歇尔莫扎特目录”这项不朽的工作。从受托修订到得以出版,历时八年之久。目录出版后,德国对此噤若寒蝉,德国之外则好评如潮。莱维援引了爱因斯坦在《莫扎特其人其乐》中对纳粹行径的质疑:他不仅认为“莫扎特对政治不感兴趣”,还以莫扎特放弃了爱国主义剧本的事实来反驳“德意志爱国主义”论调。他还引述了莫扎特在致父亲的信件中对军国主义的憎恶性言论,以强调莫扎特的民主意识。可见,第三帝国急功近利制造的假象,未能实际操控莫扎特研究的走向。
但xx并不在意来自帝国外的反对声音。战争爆发后,莫扎特的作品一直作为xx的外交工具与德国文化霸权的象征符号出现在前线和后方。不仅莫扎特音乐节随处可见,为了拉近与意大利的盟友关系,xx甚至转而强调莫扎特音乐中意大利风格与德意志精神的巧妙融合,并积极地报道双方的文化合作。而在占领区,除了在东线的波兰——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的仇恨之故——没有产生xx预期的“同化”效果之外,奥地利、捷克及荷兰等国家的文化活动都被第三帝国所渗透,尤其是在巴黎:法国代表团因在参与莫扎特音乐节期间受到礼遇而对德国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可见xx政府利用莫扎特作为文化符号的做法并非全无收效。
既如此,为何xx大费周章为莫扎特量身定做的“德意志偶像”包装会在战后迅速瓦解,也未让莫扎特的名誉受损呢?
四、影响:假象与真相
回顾xx上台后施行的艺术文化独裁政策,可以说涵盖了方方面面:德国的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一切创作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一切以xx的价值观作为标杆,致使xx音乐家们在这十二年间(1933-1945)没有留下民族性突出的佳作。这个曾经诞生过大批知名音乐家的国度,以“低等”血统为由驱逐、迫害了众多优秀音乐家,如作曲家勋伯格、库特·魏尔、汉斯·艾斯勒以及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等,就连非犹太裔的欣德米特等音乐家,也因其音乐被认为体现了“布尔什维主义”这种与xx立场不相容的意识形态而受到了排挤。而至于已故的音乐名家,xx当局更是为所欲为:马勒、门德尔松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全面遭禁,巴赫音乐中的宗教性则被淡化,成为所谓“德意志风格”的代表之一,贝多芬音乐中的斗争性被“升华”为了“条顿英雄主义”,就连移居伦敦成为英国公民的亨德尔也被冠上了“德意志爱国者”之名。
以今人眼光来看,上述音乐家并没有因xx一时的歪曲或诋毁而长期遭受不正确、不公正的评价,反而彼时那些为了事业前途向当局妥协继而位列xx阵营的音乐家(如理查·施特劳斯、卡拉扬等),被永远地烙上了xx的印迹。可见历史真相会在寂静之中默默保留,并等待着被还原的时机。不过有一位音乐家似乎是成了例外,那便是瓦格纳。
战后瓦格纳作为“xx精神导师”的形象非但没有被洗清,反而愈发深入人心,以至于“犹太国”以色列至今仍在“非正式”地禁演瓦格纳的作品。但事实上当最初的“德国工人党”于1920年正式更名为“xx党”时,瓦格纳已辞世37年,他与xx之间本不该存在直接的纠葛,此间想必也存在夸大的解读。但同样是被纳粹利用的日耳曼音乐家,瓦格纳与莫扎特的身后影响却截然不同,何以如此呢?
深究起来,这恐怕并不只是xxx狂热崇拜瓦格纳的“后遗症”,更与瓦格纳本人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脱不了关系。瓦格纳于18世纪50年代明确显现了强烈的反犹态度,不仅写作了声名狼藉的《音乐中的犹太主义》一文,还发表了一系列反犹言论。虽然,这些情绪似可归因于他那激进的革命热情、矛盾的性格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的流亡境遇,而且瓦格纳的理想主义与其辞世50年后再生的法西斯主义也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在公开文论或私密信件中表现的反犹论调必然会成为后人解读的参考;而莫扎特却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抛开作曲家的言论不谈,只就音乐本体而言,瓦格纳的音乐常以复杂、紧张、不协和的音响来制造激烈的情绪,这易于使人联想起疯狂、暴虐的情境,甚或会被认为维系着作者本人的性格倾向。相比而言,莫扎特音乐中则有着相对简单明晰的和声风格与织体结构,就连悲伤愁绪也能搭载着悠扬的旋律,体现出古典作曲家们对于“美”的纯真追求。因此瓦格纳更容易成为xx价值观的有力推手,也更容易被受害者群体所憎恶和抵触。无怪乎xx分子在“征用”莫扎特形象的过程中,更强调其“天才”形象。
不过,莱维此书并未呈现xx当局利用音乐家的全部伎俩,似乎xx眼中只将莫扎特的“民族性”(即德国性)落实在了“用德语演唱”这一点上。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处切题的线索,即提到了瓦尔特··费特(Walther Vetter)的下述观点:“莫扎特的音乐语言在本质上是有组织的,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德国性的”(第36页)。不过这一表述过于模糊,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究竟何为“德国性”呢?它在莫扎特音乐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在18世纪德奥音乐逐渐步入欧洲音乐的中心之前,德国的音乐生活一直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这在歌剧领域最为明显——此时的德语歌唱剧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附于意大利传统。音乐中可被识别的所谓“德意志属性”,是经过了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才逐步形成的,其特性包括:结构形式的严谨性、乐思逻辑的贯通性、织体形态的浓密感和智性化,思想内涵的哲性深度、强烈的宗教化倾向等。然而此时的日耳曼音乐家始终对外来音乐文化表现得高度包容甚至崇拜,上述几位大师无一不是欧洲各国风格和技法成就的集大成者,这样的民族特性似乎是在无意识的自发状态下形成的。直到19世纪中后期的勃拉姆斯时代,“德意志民族精神”才上升为了一种被蓄意维护和标榜的“意识形态”。
此外,从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角度看,莫扎特的创作确实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巴赫父子、亨德尔、格鲁克等多位日耳曼作曲家的影响,似乎它与德国音乐传统的血脉也从未间断过。然而更进一步的事实却是:J.S.巴赫的创作本身广泛体现了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音乐风格,J.C.巴赫的器乐作品中有显著的苏格兰民歌曲调,亨德尔的歌剧“不巧”是意大利式的,深刻影响莫扎特歌剧的亨德尔清唱剧是写给英国人的;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对象是意大利正歌剧,而他实施改革的阵地则是法国的巴黎——可见,莫扎特音乐中的日耳曼“基因”或“民族性”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恰恰是极为多元的。
再者,xx对莫扎特音乐的利用主要集中在他的歌剧领域,这本身是极其片面因而不具有说服力的。使十八世纪日耳曼音乐真正具备“霸主”地位的,恰恰是它在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等器乐领域中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些领域中,学者们再次发现了意大利风格的强烈影响:交响套曲本身就脱胎于意大利正歌剧序曲,而意大利喜歌剧则是对整个维也纳“古典”风格产生了渗透性的影响。
正如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在写给瓦格纳的文字中所说,音乐是“唯一可被理解却不可被转译的悖谬式语言”。因此,想要了解音乐作品中最真切的表达意图,必然要以充分把握音乐本体为前提,继而再考量音乐之外在因素。xx在“改造”莫扎特作品的过程中利用了“转译”过程的困难性,其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化解读,完全脱离了莫扎特的音乐本体。也正因如此,xx对莫扎特形象所做的“德意志偶像”包装才会如此脆弱,一旦其政治威慑力荡然无存,这种包装便随之破裂。
五、反思:民族性作为“优势”抑或“局限”
xx选择利用莫扎特,是因为莫扎特音乐的伟大性早已经成为共识,xx想要进一步把他变成伟大的“日耳曼民族音乐家”。但事实上,莫扎特某些作品也曾遭受冷遇,在其身后才逐渐焕发光芒。而且,在莫扎特的伟大性逐渐得到公认的过程中,却从未有人如xx那般着意强调其“民族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莫扎特音乐中无论是否具有突出的民族特性,都并不影响其传播和接受。
意大利性也好,德国性也罢,这些民族性因素在莫扎特的创作中都是以不自觉的方式融入的,各种因素都是莫扎特音乐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莫扎特游历各国的人生经验的音乐化体现,是他对各国音乐文化经过吸收、消化、解构、重组之后形成的整合化形态。如纳粹当局那样单独强调其“德国性”是荒谬无稽的,这与莫扎特音乐中强大的文化包容性构成了巨大的冲突。纳粹也未能正确把握民族性在莫扎特音乐中的实际价值。即便他们有充分证据证明莫扎特的作品从创作构思到表现内涵都纯然体现了“德国性”,这也并不会增加莫扎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反之,虽然后世学者津津乐道于莫扎特音乐中的“普世性”,却也并未抹杀其鲜明个性。毋宁说,莫扎特音乐的魅力不在于体现了任何民族色彩,而在于其完美地融合了超凡的情感深度、自如的歌唱风格、内在的戏剧性、复杂的结构以及丰富的表现力。
诚然,民族特性(尽管与伟大性无关)也能赋予音乐作品以特殊的意蕴和光泽:对内,它能在本民族受众中引发强烈的文化共鸣和民族认同感;对外,它能对“他者”文化中的受众产生一种奇异新鲜的吸引力。但这种意蕴和光泽并不会在本质上影响作品的价值。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音乐中的伟大性》中论及“民族性”时曾说:“无论是民族外衣,还是所谓的世界性或超民族性的风格,都与音乐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毫无关系。”[5]即便对于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作曲家(如穆索尔斯基),在其作品被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民族色彩也“只起了一个很次要的作用”(第18页),它应当被视为音乐语言的风格特征,却不会成为传播和评价中的障碍或优势。与民族性相仿,作曲家的“个人性”也是如此,保罗·亨利·朗在论及贝多芬时也提到:
一位艺术家哪怕具有高度的个性也可以获得普遍的承认,这位具有普遍价值的个体(每个人心中的英雄)所具有的强大的力量和交流的渴望是任何其他音乐家都不能比拟的。
即便贝多芬音乐中的德意志属性广被论及,其价值也更多在于作品自身的艺术性构思以及能引发普遍共鸣的斗争意识。反观独尊“德意志民族性”的xx政权,似乎并未造就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究其原因,并非那些蓄意凸显民族性的作品,造成了有碍于国际性传播的壁垒,而在于这种狭隘的民族性使作品沦为了xx民族主义精神的陈列品,削弱了普遍价值。
总之,作品“伟大”与否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蕴藏着能对全世界、全人类产生广泛吸引力的普遍价值。作为个性特质的“民族性”,虽与世界性或普遍价值并不冲突,却远不及后者重要。xx对莫扎特的歪曲和滥用,除了可作为对把握民族性价值的反面例证之外,在本质上也是对音乐作品做政治性解读的极端例证——虽然极端,却并非个例。xx对莫扎特形象的征用既未对作曲家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也未使他的作品增添新的光彩。xx的失败印证了基于某种政治立场“反推”音乐价值的解读方式存在漏洞。政治因素会影响作曲家创作时的精神与意志,继而对作品产生某些间接影响,但这些因素本身是外在于音乐的,不应作为衡量音乐自身价值的主要依据。
结语:缺憾与意义
本书作者艾瑞克·莱维在编织、呈现各种文献资料时并未完全遵照时间顺序。在第四章“把莫扎特雅利安化”之后,作者插入了第三帝国可控范围之外的流亡音乐家们为抵制恶意歪曲莫扎特的现象所做的斗争。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了某种混乱,尤其是频频被提到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相关叙述在时间点上较为跳跃,减弱了叙述的连续性,也使部分内容相互交叠。在谈及此事的音乐学家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以xx阵营的音乐学家埃里希·申克为例,他在1931年的“萨尔茨堡国际莫扎特大会”上曾试图抹去犹太音乐学家的研究成果,还组建了“莫扎特中央研究院”,以便干预莫扎特研究的方向。但这位反犹态度极为强烈的音乐家,在第一章之后就几乎不再被提及,而只在最后说到了他的战后处境。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之外的其他莫扎特学者,则大多只被零散提及,相关字句散落于书中各处,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即便是这位学者,其关于莫扎特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被充分交代,尽管第六章有相对集中的记述。尤为缺憾的是,作者没有将他在xx期间的研究与他离开德国前的研究活动(第一章)合理串联起来,而只是反复地叙述了其犹太身份引发的不公正待遇,读来颇觉赘余。
此外,书中所列史实集中指向了xx对莫扎特形象的歪曲,但并未从正面论及莫扎特的“真正面目”究竟为何,故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对照。作者对此关键问题的立场略显笼统,除了意识到“民族性”(这是作者想要明确否定的)与“世界性”或“包容性”存在联系之外,很难找到更多关于莫扎特音乐本质的内容。这使对莫扎特音乐缺乏基础性了解的读者难以对xx歪曲在何处、滥用到何种地步、产生了何种影响等问题产生明确认知。
好在作者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相当详尽,能让读者从多方阵营的具体言论中清晰回顾关于“xx与莫扎特”这一话题的事实情形,这为莫扎特音乐的接受史研究和第三帝国的音乐文化方针等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让我们对符号化了的音乐家所留给世界的财富有了新思考。
参考文献:
[1]艾瑞克·莱维.莫扎特与xx:第三帝国对一个文化偶像的歪曲滥用[M].杨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1).
[2]莫扎特.莫扎特书信集[M].钱仁康,编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3]伍维曦.“风格叙事与历史语境:作为‘音乐史事件’的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J].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13,1.
[4]Claude LéⅥ-Strauss,The Raw and the Cooked:Mytholog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5]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音乐中的伟大性[M].张雪梁,译.杨燕迪,孙红杰,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01).
[6]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保罗·亨利·朗文集[M].马艳艳,译.孙国忠,孙红杰,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