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后人类:赛博格艺术中身体的表现形式论文
2024-06-14 09:43:43 来源: 作者:caixiaona
摘要: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赛博格”在人与科技联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被提出。技术和人自身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高度融合,引出技术化的身体、媒介化的身体、和虚拟身体的媒介化等身体的多种形式,也伴随着机器哲学、“超人类”“后人类”等概念被提出。文章从后人类身体的理念出发,探寻赛博格艺术中技术、媒介与身体的紧密关系和产生的演变。
摘要: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赛博格”在人与科技联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被提出。技术和人自身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高度融合,引出技术化的身体、媒介化的身体、和虚拟身体的媒介化等身体的多种形式,也伴随着机器哲学、“超人类”“后人类”等概念被提出。文章从后人类身体的理念出发,探寻赛博格艺术中技术、媒介与身体的紧密关系和产生的演变。
关键词:赛博格;新媒体艺术;身体;后人类
媒介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环境接触的中介,一切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或拓展,不同媒介延伸了人的不同部分,也延伸了不同的感觉器官。[1]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媒介,媒介又是人体感官和神经系统的延伸。伴随着科技发展、新媒介诞生、参与并影响着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与发展,它的表现方法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形式。新技术催生出新媒介,新媒介的媒介特性将身体延伸多种虚拟形式,新技术的嵌入则导致了赛博格身体的出现,揭示出身体受技术、媒介的影响所形成的后人类变化。
一、赛博格与后人类身体
人的身份是否局限于实际的物体当中,对此的思考在千年前便已开始,古希腊时期忒修斯从克里特岛凯旋所乘的船被留下当作纪念碑。随着时间推移,船身腐朽后逐渐替换为新的木材直至整个船身。哲学家们由此发出了疑问: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吗?若是,可它已经没有原本的一根木头了;若不是,又该从何时开始算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人们通过科技手段对身体实验与改造层出不穷,各种手术嫁接、移植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现实当中。当身体的主体性在受到挑战时,赛博格(Cyborg)的概念被提出,它是由控制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这个词语拆分重组而成:指代那些借由人工科技来增加或强化生物体局限的人类身体。人机混合的赛博格形象最初是在科幻小说、影视当中,如爱伦•坡在1839年的短篇小说《消耗殆尽的男人》中描述了一个大部分身体都由假肢组成的人物形象;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明确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与虚构的创造物”

哈拉维表示:我们已经成了半机械人,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旧边界正在消失。[2]从这个角度来看,肉体不再是固定的实体,也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体,而是随着其特定的环境和所嵌入的话语的不断改变存在的。传统意义上的生物与环境的界限是已经无法满足,“后人类”的提出象征着人类正迈进一个新的进化阶段。目前,受遗传工程、生物技术、虚拟技术、人工智能及伦理道德的制约影响,后人类进化主要包括三种方式:
第一是生物技术对身体基因再造重组(如克隆技术的使用)。[3]艺术实验室SymbioticA的《猪翅膀》(pigwings)项目,“猪的骨髓干细胞和三维生物可吸收聚合物被用来制作猪骨组织翅膀,使之成为人形脊椎动物可飞行的三种解决方案的形状”[4](天使、恶魔、飞龙),用于创造人与动物的物理杂交设想。
第二是对身体进行技术或人工进行种植(如义肢等医疗手术的使用)。[5]赛博格艺术家尼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和穆恩•里巴斯(Moon Ribas)都为自己安装了额外的“肢体”用于延伸和增强身体的感知内容。澳大利亚艺术家史蒂拉克(Stelarc)他的系列的“身体添加”实验如《第三手》(The Third Hand)和《第三耳》(Third Ear)都扩展了身体能力,强调“人体已过时”的概念。
第三是利用虚拟技术制造虚拟形象并改造现实身体,将虚拟和现实合并,包括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的共生。[6]艺术家乔恩•拉夫曼(Jon Rafman)的作品《库尔•艾德曼》(Kool-Aid Man,1974)就是这样虚拟与现实边界模糊的作品。艺术家基于第二人生的游戏平台,以一个虚拟的形象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游览为主视角,遍历了这个由现实用户创建的数字景观。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扮演模拟现实的身份,二者相互影响。
哈拉维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界定:动物与人类、自然/人工制造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的领域。[7]她的“半渗透自我”(Semipermeable self)概念,取代了旧的同质身份的概念,暗示了有机体和技术以及生物和机械之间的相互渗透,由此可见后人类在科学、技术中的发展都促进身体媒介的多样化。
二、后人类身体的表现形式
西方知名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他通过现象学的理论去探讨分析人工制品、人类、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其著作《技术中的身体》中对于“身体”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三个身体(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理论[8]:以梅洛•庞蒂思想为基础的物质身体,是具有生物性,是原始的身体本身的肉体拥有基本的触觉、行动和表达情感的能力;第二是基于福柯的镜像理论代表着“他者”对自我的建构过程,主要针对身份、文化知识等意义下的文化身体;最后是被科技改造形成的技术身体,它融合了物质与文化,并通过技术建立起的科技意义上的身体。随着技术进步,物质身体被机械逐渐替代,技术身体完善的同时也注定身体的媒介化虚拟化,文化身体被潜移默化的改变,最终形成后人类景观。“新媒体艺术将身体视作媒介与感知的中介产物”,要实现身体的价值,将其作为媒介传播中重要节点。[9]身体主体呈现出“媒介”化,即身体与其环境之间处在混乱交错之中。身体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它同时是行动和服从的实体,给予和感知意义,触摸与被触摸,身体给予行动和反应。艺术家将身体与技术结合,为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1.肢体的延伸
关于假肢的两种思想结合:一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假肢延伸,使肢体超越自身;第二个是海耶斯在后人类观点认为身体是我们都已学会操纵的“原始假肢”。但在媒介信息化的后人类时代,身体与机械计算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个的角度看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理论,身体不再把假肢作为媒介延伸,相反,身体就是媒介本身。
日本艺术家Takehito Etani的作品《第三只眼的计划》(The Third Eye Project,2002)呈现了一种自我疏远的体验[10]。装置剥夺了本体的视觉,只允许单眼观看眼前的显示器,以抵消外部视觉感受,使其专注于屏幕,观者通过单目屏幕体观看的则是自身第三人称视角的实时反馈。“第三只眼计划”将肉身“虚拟化”通过技术身体的视角去观看物质身体。作品把惯常的视角转移到第三人称视角,通过模仿*频游戏的视角自上而下的观看,视觉被延伸,模拟的虚拟视觉引导着肉身在物质空间中探索。陌生怪异的感知削弱了使用者的安全感,穿戴者会担心绊倒而小心翼翼地移动,感官系统必须通过学习新的行动语言来重新掌控身体。《第三只眼的计划》展现了身体、虚拟空间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结合了技术与身体的交互的条件,将视觉感受抬升到身体之外,强调了存在于身体自我感知中的陌生感。通过技术手段将结合自身之外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体验,身体不再是自身局部运作、感知,而是一个扩散延伸的媒介身体,可以超越皮肤的边界。
2.嵌合的演变
由于免疫生物学的研究,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循环交流正在削弱内部环境和外在表现的区别,媒介的发展也使得身体本体的感官更加便捷敏感。凯瑟琳•海尔斯指出,身体不单是生命灵魂的寄生躯壳,更是以身体媒介为基础,融入意识、数据、情感的混合物。
艺术家马里恩•珍特(marion jeantet)在她的实验作品《愿马儿活在我心中》(que le cheval vive en moi,2011)中给自己注射了马的血浆和免疫球蛋白,蛋白与神经系统紧密相连,这提供了与马构建精神交流的可能;穿戴两个铰接式假肢模仿马的腿部,以便与马产生肢体语言和平等的对视。她以一种独特的艺术方法,从根本上参与了生态辩论,质疑物种之间的渗透性,探索了人、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她说“我有超越人类的感觉,我感觉脱离了原本的身体,我感觉自己更强壮,也更加敏感,精神越发偏向草食性动物的情绪,变得紧张和怯懦,我常失眠,我觉得我是一匹马”。[11]这不由人联想到不同神话中的嵌合生物:人首蛇身的女娲、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希腊神萨提尔则同时拥有人类的身体和羊角羊腿,无论是人与兽还是人与机器,它们都是在当时文化技术的背景下人在对自然认知理解后的真实反映。
荷兰美学家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在著作《命运的驯化》中的观点认为“人”的概念是受特定环境外在影响决定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背景决定着人对自己的不同认知,技术革命决定半有机体、半机器的赛博格(Cyborg)的出现。正如萨提尔源自过去人类对自然界原始力量的崇拜,它至今仍然决定着人类对生命的探索方向,源自科幻的赛博格已经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密不可分,并指明了未来的情景,人类的生命形式也终将以混合体的形态演变下去,等待新技术提出的新命名。正如哈拉维所说,我们永远都是萨提尔,且一直都是赛博格。[12]
3.模糊的边界
当我们受到原有的身体局限束缚时,可以借由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来重新扩展身体,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新媒体艺术家森万里子(Mariko Mori)的系列摄影作品则是一场以不同的“身份”穿梭在虚幻与现实之间的游历。在1994年的作品《和我玩》(Play With Me)和《情人旅馆》(Love Hotel)中以科幻女孩的形象站在繁忙的东京街头;1995年的《空梦》(Empty Dream)里她利用软件将自己的美人鱼形象置身于真实的人群当中;1996年的《最后起航时刻》(Last Departture)中则变为领航员。在系列作品中,艺术家根据*频游戏虚拟中的角色创建了扮演的模型,与现实世界交互表演来展现真实性。虚拟与现实相互入侵,她的形象象征着男性在电脑游戏世界中寻求的性幻想,表演现场观众的好奇和排斥,则映衬着人们对后人类时代新兴技术对世界重构的担忧和期望。
机器通常被描绘成“奴隶”单方面接受人类的指令,但在《A-positive》中人类却将自己的血液献给机器,与之产生平等的共生交换。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和埃德•班尼特(Ed Bennett)在芝加哥合作展出的作品《A-positive》创造了一种人机“对话”情境,机器与人类通过医疗设备相连接,生物机器人获取人类的血液,并从中提取氧气来维持火焰的燃烧,作为生命的原型象征,生物机器人将葡萄糖偿还给人体作为置换,作品呈现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机器人学的高度融合。对机械生命的探索本是基于计算机软件工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虚拟空间”研究,而《A-positive》为机器生命概念提供了“物质”的表达方式,进一步模糊真实(物理)和人造(虚拟)生物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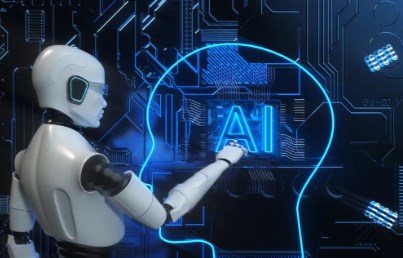
数字科技、虚拟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身体“技术化”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探讨机器人的伦理,并重审视后人类主义对各种边界不断地构建和重建,人类不再坚持追求对身体的控制,而是在这个庞大的数据系统中,将身体充当传递接收信息的“介质”。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结语
在媒体艺术中,身体与媒介的相互征用,是身体依附技术产生的必然结果。赛博格艺术改变了身体的传统鉴赏方式,技术、媒介、身体三者合而为一产生了一幅别样的情景。在后人类时代,人类的定义将不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身体结构,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植入的技术。身体作为新科技时代的媒介,通过身体媒介、机械、电子、生物技术和未来的各种科技将指引着人类的身体面向多个不同的选择:是杜绝科技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去拥抱后人类的新时代。
去中心化的人类思想时代的进步正在加速人类的蜕变,赛博格的故事随之展开,技术和虚拟感知最终会带来新的伦理可能性,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对具体社会现象分析的启示和理论视角。艺术将以一种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一个属于“后人类”的空间——任何自我的形象都离不开虚拟性、技术嵌入和肉身身体。在当下人类视野无法逾越的鸿沟中、尚未达到要求或自我否定的技术中去发现新的土壤,让我们更好地接触数字媒体并调动它的潜力,探索人类对自身身体有限的理解中而未被揭示的事物。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译林出版,2019.
[2]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 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Amelia Jones.The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al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2003.475.
[3]张之沧.“后人类”进化[J].江海学刊,2004(06):5-10+222.
[4]https://tcaproject.net/portfolio/pigs-wings/[2023年4月3日登陆].
[5]同[3].
[6]同[3].
[7]D.Hara way,Die Neuerfindung der Na tu r[M].Frankfurt:Campus,1997.
[8]杨庆峰.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9]钟舒.技术、媒介与后人类:新媒体艺术中后身体问题理论溯源[J].艺术评论,2019,186(05).
[10]Anne Pasek.Seeing yourself strangely:Media mirroring in Takehito Etani’s The Third Eye Project[J].Metaverse Creativity(new title:Virtual Creativity),2014,4(2):121-138.
[11]https://we-make-money-not-art.com/que_le_cheval_ vive_en_moi_may/[2023年3月23日登陆].
[12]约斯•德•穆尔.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