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阈下的儿童文学英译汉研究论文
2024-06-13 10:59:26 来源: 作者:caixiaona
摘要:儿童文学英译汉作品不仅借鉴了国外的优秀文化,同时对青少年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对郑荣珍《记忆传授人》译本的研究,从接受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读者中心、期待视野、未定点、召唤结构四个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该译本中的适用度,并且在这四个概念关照下分析译者使用的归化、省略、具象化翻译等翻译策略。
摘要:儿童文学英译汉作品不仅借鉴了国外的优秀文化,同时对青少年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对郑荣珍《记忆传授人》译本的研究,从接受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读者中心、期待视野、未定点、召唤结构四个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该译本中的适用度,并且在这四个概念关照下分析译者使用的归化、省略、具象化翻译等翻译策略。
关键词:接受美学;儿童文学翻译;《记忆传授人》;翻译策略
随着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需求增加,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规模也在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国际儿童文学佳作被引入了中国市场,通过翻译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应承霏(2015)指出,尽管文学翻译最早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儿童文学翻译才兴起,在进入21世纪后,国际儿童文学翻译迅速发展,与国际上的儿童文学翻译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产出仍有较大差距[1]。这一现象说明,在儿童文学翻译中,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认识。而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接受美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首先,文学翻译牵涉到语言、文化和情感的各个方面,而儿童文学作品则具有特殊的文体和读者群体。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既要保留原著的思想感情,又要尊重其文体特征,更要顾及目标读者的理解能力、语言习惯和阅读水平。深入研究接受美学,可以更好地理解儿童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点,从而更准确地传达给目标读者。其次,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交流显得愈来愈重要。儿童文学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其跨文化传播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深入研究接受美学,可以提升翻译质量,使译文更贴近原作的美学风格和情感表达,促进儿童文学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第三,儿童文学翻译的质量,对孩子们的阅读经验、提高其文学素养有很大的影响。深入研究接受美学,可以更好地把握原作的情感和文学风格,为读者带来更丰富和深刻的阅读体验。所以在这个跨文化交流和文学翻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对于英译汉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接受美学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记忆传授人》是一部由Lois Lowry所著的儿童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于1993年首次出版,并在1994年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大奖,迅速成了广受欢迎的经典儿童图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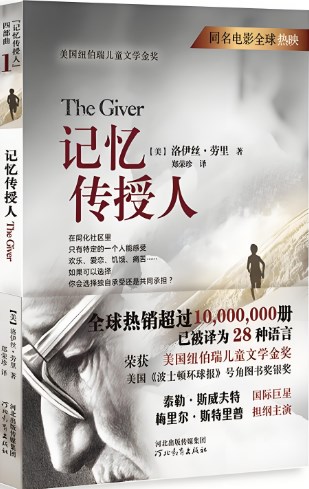
该书讲述了主角乔纳斯住在一个被严密监视着的社会里,他被挑选出来接受这个社会的一切情绪与回忆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乔纳斯逐渐发现社会中隐藏着的记忆并非完全可信,而是可以被篡改和操控的真相,并挑战了社会对记忆的信任和规范。小说涉及个体自由、情感重要性等主题,引发读者深刻思考。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哲学问题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成为儿童文学中的经典之一。本文旨在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以《记忆传授人》①为例,具体分析译本中所运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它所取得的情感共鸣效果。
一、接受美学理论综述与儿童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产生于1960年代末,七十年代发展到顶峰,出现了五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姚斯和伊瑟尔最为突出。姚斯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伽达默尔[2]。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为接受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强调了作品与观众的交互作用,指出了审美体验的相对与主观性。姚斯和霍拉勃提出“读者中心”和“期待视野”的概念,要将“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转移至“读者中心”,更加着重强调读者的阅读体验以及主观感受[3]。伊瑟尔的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那里得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伊瑟尔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本文的召唤结构》,他从英伽登关于文学的艺术作品理论中参考了文本图式化框架下的未定性这一概念[4],进一步说明了未定点和空白是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最主要的区别特点,是文学阅读中缺乏明确的、有限制的意向,这使得作品具有吸引读者的结构机制,即“召唤结构”[5]。综合来看,“读者中心”“期待视野”“未定点”“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研究中的四个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强调了文学作品中读者的重要地位,还有那些存在于作品中,能够吸引、指引读者的结构特点,从而对读者的阅读经历与理解过程产生影响。
接受美学作为理论框架强调了读者在阅读和接受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和主观体验作用。在读者阅读和接受作品时,译者对原文的情感传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将原文的感情和文体表达出来,以便让目标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获得类似的情感体验。因此,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的选择和决策直接影响着读者对原作的理解和感知。翻译儿童文学作品需要将儿童置于阅读的中心位置,考虑到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心智尚未成熟。为此,需要保留原作中的文学风格、诗意语言和图像描绘等元素,让目标语读者在阅读中理解作品所传达的知识以及情感,体验到美的享受,并培养其对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此外,个体的感知和认知过程也是审美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的审美观念和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因此理解儿童的认知和心理发展阶段对于选择元素至关重要,要确保与目标读者的发展水平相匹配。在考虑文化差异时,译者需要在传达原作各种元素的同时,尊重和保留原有文化的特色。儿童文学中也常含有幽默和情感元素,如何在翻译中保留这些元素,并使其对目标文化的儿童读者产生类似效果,是在接受美学指导下译者面临的挑战之一。
所以这就意味着译者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必须将自己的文化知识、阅读经验以及对儿童的认识都带入翻译之中。而译本的目标读者大多是目标语言的儿童,因此儿童的接受包括风格、儿童心理、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都应成为译者着重考虑的因素[6]。彭腾瑶(2014)也提出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中,译者应当将儿童读者的内心需要、语言特征、接受能力、社会心理以及审美评判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教育与趣味性并重,从而使译文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7]。
二、接受美学视阈下《记忆传授人》译本译例分析
(1)It was not a squat,fat-bellied cargo plane but a needle-nosed single-pilot jet.
译文:它不是那种外形矮壮、肚子圆鼓鼓的货机,而是一架机头尖尖、单人驾驶的喷气机。
前半句采取直译的方式,将原文中的比喻修辞直译过来,保持了原文想呈现的趣味性,将飞机生命化。“squat”“fat-bellied”“矮壮”“肚子圆鼓鼓”,该译文在激发儿童读者想象力的同时,也保留了儿童读者所需要的幽默元素。译文的目标语言为中文,目标读者为中国儿童,由于在接受美学中以读者为中心,以及中国文化中少有“尖鼻”这一说法,飞机前端在中国一般称为“头”并非“鼻”,所以译者通过采取归化法选择使用“机头尖尖”作为对needle-nosed的翻译。在本句中,译者充分考虑到了要对译文保留幽默元素以及以“读者中心”为原则而采用归化策略,确保了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更容易被儿童读者理解接受,进一步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2)But suddenly Jonas had noticed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apple……he looked at it carefully,……And again-in the air,for an instant only it had changed.
译文:但是,当苹果抛到空中的瞬间,他突然发现苹果的某一部分……老实说,到现在他也还搞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变了。不过,一落到他手中,它还是原来那个苹果,大小相同,形状相同,依旧是完美的圆形,就跟他的外衣一样。那个苹果毫不起眼,他用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扔了几遍,再把它扔给亚瑟。结果在半空中,在转瞬间,它又起了变化。
文本的难易程度对于儿童读者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译者并没有将path of the apple和looked at it carefully译出,而是采取原意替代做到将文字精简后更方便读阅读和理解,使得儿童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惊奇和好奇心,注重儿童读者的阅读体验。译文还注重保持了原文中的故事流畅度,添加了原文中并未出现的连接词,如“竟然”“不过”“依旧”“来来回回”“结果”,引导读者逐步了解主人公的观察和感受。again-in the air,for an instant only it had changed译为“在转瞬间,它又起了变化”这样的表达也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适合儿童文学中奇幻元素的传达。
(3)……All of that was forgotten now.He simply willed himself to stand,to move his feet that felt weighted and clumsy……
译文:……现在那些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光是站起来,往前走,爬楼梯,走过平台站到首席长老身旁去,都觉得举步维艰。
本段译文采用了简练而生动的语言,更贴合儿童文学的特点。例如“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巧妙地传达了原文中All of that was forgotten now的意思,使用了形象生动的表达方式。“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期待视野”指的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的依据,它确定了读者理解作品的角度、角度和方法[8]。译者在译文中保留了原文描述的主人公希望上台时的自信心境,通过“满怀自信地上台”表达了这种情感;“举步维艰”生动地表达了原文中描述主人公感觉沉重和笨拙的状态,增加了场景的形象感,用最符合读者年龄段以及最易接受的语言语调引起读者的共鸣,进而满足读者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特别是关于他面对失落和挑战时的情感变化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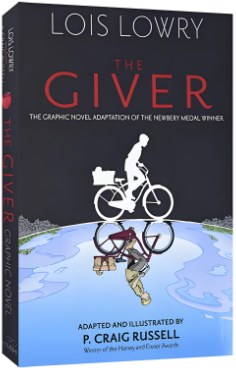
(4)……and above him the white sail of the boat billowing as he moved along in the brisk wind.
译文:乔纳斯继续有节奏地拍打着,同时想起传授人不久前转移给他的快乐航行记忆:天气晴朗、微风拂面,他架着白色帆船徜徉在清澈碧绿的湖面上,乘着清风徐徐而行。
译文使用了生动的描写,如“有节奏地拍打着”“天气晴朗、微风拂面”等,使儿童读者更容易形象地理解情景。描述中译者保留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欢乐情感,强调了传授人给乔纳斯的快乐航行记忆,突出了这段回忆的美好和愉悦,符合儿童文学注重情感体验的特点。通过描述“清澈碧绿的湖面”和“白色帆船”等自然元素,翻译传达了清新、明亮的色彩,符合儿童文学对于色彩和自然的喜好。刘秋兰(2004)说过,文学语言中存在许多未确定的意义和空白,这种未确定性和空白是文学作品产生效果并引发读者共鸣的基础[9]。接受美学中的“未定性”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将不具有明确含义的文本具体化,或是将那些具有具体意义的文本空白化。译者将the brisk wind译为“清风徐徐而行”把直译为“轻快的风”比作了人行走,从而具象化更有利于激发读者对于航行的想象。
(5)He forced his eyes open as they went downward,downward,sliding,and all at once he could see lights,……the red,blue,and yellow lights that twinkled from trees……
译文:在下滑的路程中,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他看见灯光了,他终于认出那是什么,他知道那是从窗口透出的灯光,在屋里有棵大树,树上悬挂着红灯、蓝灯和黄灯……
译文使用了直接、明亮而又具有紧张感的语言,如将“forced his eyes open”“see lights”译为“强迫自己睁开眼睛”“看见灯光了”,保留了原文中不安、紧张的情感层次,增加了场景的紧凑感,有助于引起读者共鸣。接受美学理论中提出的“召唤结构”这一概念,意在鼓励读者激发其想象力,从而发挥读者的自主能动性[10]。译者将文中的景象如将the red,blue,and yellow lights that twinkled from trees译为“树上悬挂着红灯、蓝灯和黄灯”,描述得非常具象,有助于激发儿童读者的想象力。描述中强调这些灯光是从家庭窗口透出的,是在庆祝爱的喜悦,强调了家庭共同创造美好回忆的过程,这是儿童文学中家庭和温馨元素的共鸣点。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记忆传授人》的英译汉研究,深入探讨了接受美学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在情感、描写和场景的翻译中,译者通过使用归化法、省略翻译、具象化翻译等等翻译策略结合接受美学理论下的读者中心、期待视野、未定性、召唤结构等一系列概念,成功地传达出了作品中的美感和情感共鸣。这不仅使目标语言的儿童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体验故事,同时也为儿童文学作品的英译汉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通过保留原文中的情感层次和细腻描写,译者传达出了作者所希望表达的美好和情感。其次,翻译中对于儿童感情培养、感官认知和美感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使得目标语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故事中所涉及的情感和美学元素。这些翻译方法不仅在文学传播上有着显著的影响,更在儿童教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应承霏.近30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现状与趋势[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38(03):119-127.
[2]朱健平.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华东师范大学,2003.
[3]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沃尔夫冈•伊瑟尔.金元浦译.本文的召唤结构.接受反应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42-44.
[5]刘秋兰.拓展“期待视野”发现“意义空白点”[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4.
[6]张鲁艳.接受美学与儿童文学翻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92-96.
[7]彭腾瑶.接受美学理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J].网友世界,2014(04):80.
[8]翟海霞.从接受美学视角论文学翻译[J].文教资料,2012(29):19-21.
[9]刘秋兰.拓展“期待视野”发现“意义空白点”[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4.
[10]魏晓红.接受美学视野下文学作品的模糊性及其翻译[J].上海翻译,2009(2):6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