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以重庆市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为例论文
2024-05-31 10:15:05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市民间文学类非遗的典型,二者虽然具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性,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涵盖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俗语等多个门类,在民间文学类非遗中极具代表性。传承好民间文学类非遗,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民间文学口耳相传的独特传承形式,使其在娱乐方式多样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的时代浪潮下生存状况堪忧。郑土有教授指出:“民间文学类非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演述民俗场的消失,导致演述活动不能有效进行,演述能力下降,新的传承
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市民间文学类非遗的典型,二者虽然具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性,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涵盖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俗语等多个门类,在民间文学类非遗中极具代表性。传承好民间文学类非遗,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民间文学口耳相传的独特传承形式,使其在娱乐方式多样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的时代浪潮下生存状况堪忧。郑土有教授指出:“民间文学类非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演述民俗场的消失,导致演述活动不能有效进行,演述能力下降,新的传承人不能养成。”民俗场指的是民间文学“文本”演述的文化空间,即一个“文化场域”。“文化场域”概念产生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该理论核心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广泛应用于文学现象、传媒影视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但针对非遗传承、民间文学保护等方面的应用研究相对匮乏。将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问题置于场域理论视角下,选取走马镇和广阳镇为两个个案,在分析该理论与两地民间故事的生成、当前现状与面临困境基础上,进行传承场域的模型构建,探究民间文学类非遗的有效传承路径。
场域理论视角下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的生成
场域和惯习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社会学概念。在他的表述中,场域是指代理人及其社会地位所在的环境。每个特定代理人在场域中的位置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布迪厄将社会划分为各种不同场域,如艺术、教育、法律等,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惯习是文化资本的物理体现,指的是人们因生活经历而拥有的根深蒂固习惯和技能,本质上属于“性情倾向系统”。场域从外部规定人的行为,惯习从内部影响人的实践,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就是在这众多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传承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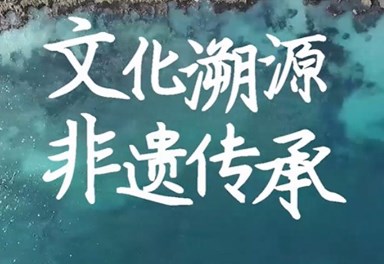
走马镇和广阳镇都隶属重庆市,在区域内都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众多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为两镇提供了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当地人对许多外来的故事进行修改,将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融入进去,逐渐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故事,从而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场域。在文化场域的客观影响下,居民纷纷加入创造和讲述故事的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惯习系统。在场域和惯习的共同作用下,两镇的民间故事产生并且得到了长久传承。
如今,两镇都不像过去那样人来人往,但由此形成的封闭环境,使两地众多的民间故事得以保存。民间故事早已成为两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由此可知,两镇民间故事的传承是一种自发行为,深深刻在两地居民的精神意识中。

场域理论视角下走马镇和广阳镇民间故事传承的现状与困境
走马镇和广阳镇民间故事的传承场域,承载了两地民间故事的传承记忆。民间故事在这样相对独立的联系网络中被传播并得到传承。然而近年来,两镇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日渐走向城市,乡村日益凋敝,两地都呈现空心化倾向。老龄化的加重和传播手段的落后,使参与民间故事传播和传承的人群大量减少,民间故事传承场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并遭到破坏。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民间故事传承资本呈现多样化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民间故事传承场域由单纯的“地域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对传承惯习的认知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乡村地域空间的缩小和网络虚拟空间的扩大,加剧了民间故事传承与其原本所在地域空间脱节的可能性,可能导致两地极具特色的民间故事失去地域性。
走马镇和广阳镇传统的认知惯习发生了变化。两镇人民在民间故事传承方面还处于较保守的阶段,使其民间故事未能完全融入现代化传承体系。
走马镇和广阳镇民间故事的传承应当建立在丰富的资源上。由于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大都重视乡村物质方面的建设,对文化资本的投入较少,使民间故事的传承缺少资本投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走马镇和广阳镇民间故事的传承场域受到了一定冲击,需要进行场域重构。
场域理论视角下走马镇民间故事与广阳镇民间故事的传承路径
任何社会场域的结构构建都按照特定的内在逻辑。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场域主要包括资源场域(基本场域)、管理场域(支持场域)、外部场域(关涉场域)、互动场域(核心场域)。
建立数字化传承平台,构筑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的基本场域。基本场域作为传承场域的资源场域,其中的资源与场域中的“资本”相类,包括民间文学资源、非遗传承人的人才资源和传承的主体——社区民众等。传统民间文学的背景是乡土式的,传播范围是以家族、民族为单位的村落或聚居地,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熟人社会”,传统民间文学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上,会受到一定时代、地域、交通等方面的限制,在保存方面同样因其传播的口头性而存在困境。笔者在对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两地能够完整讲述一个或两个民间故事的当地居民数量较少,针对民间文学类非遗这类口头文学活动,其全貌的保存及进一步的传承离不开利用不同的数字保存技术保存图像、视频、音频文件和文本等信息。应创建数字平台,整合和处理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文献,并针对具体内容和不同层次的公众需求对不同类别的民间故事资源进行整合和加工,实现文字、图像、音频、视频资料的跨媒体合成,形成全面化、多层次、立体化的民间故事资源数据库,将大量个体故事资源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网络化平台上,为公众提供普遍的信息服务。
从顶层设计入手,营造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的支持场域。支持场域作为管理场域为整个场域的有效运行起到政策支撑作用,即场域的顶层设计。按照确立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革新的要求,政府应注重政策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注重非遗传承的文化价值的保护。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促进多方面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工作的实施:对企业而言,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应建立机制,通过法律、行政和市场措施的结合来支持企业,引导社会资本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产品方面,政府机构应尽力扩大文化产品在城市地区的展示,刺激人们对适当文化消费的需求;在传承人方面,政府需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鼓励传承人积极传帮带,培养接班人,并通过建立相关培训机构和设施,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经过对照研究发现,走马镇受政策影响最为显著,正是由于政策的针对性不强、在一些专业问题上缺乏专业支撑,导致走马镇民间故事的传承情况始终难以得到真正好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某些方面的困境,如传承人群体内部关系协调问题等。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的传承政策制定,既需要政府主导,同时也需要相关领域专家的介入,使专家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为政策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提供专业支持,成为非遗传承的监护人,从而构建出一个科学性、针对性的支持场域,实现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场域的有效实现。
打破场域孤立性,融通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的关涉场域。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场域不仅与内部的子场域直接关联,还与外部的社会场域存在或强或弱的互涉关系,此处的外部场域不仅指代物理空间,还包含制度、文化、惯习等,需要创建共建共享机制,实现场域协同构建。在外部文化场域建构中,需要树立场域共同体意识,以传承场域为中心,联合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开办公益性展览活动,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让本地区以外的群体更易了解该场域的民间故事、非遗资源;同时,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构建民间文学类非遗的共建共享平台,如与相关平台合作开设官方账号,将故事会进行网络直播(如走马镇的“茶馆故事会”“周末故事会”),入驻听书App讲述民间故事等。除此之外,应强调教育对传承民间故事的重要性。对于传承场域之外的学生群体,应针对不同的层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建立民间文学类非遗文化教育生态圈。对于中小学生,主要通过开设校本课程、地方课程、非遗传承人进学校等方式;针对大学生群体,应该从兴趣和教育两个方面入手,促进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而在具体课程方面,可根据本校学生意愿开设艺术鉴赏课、通识选修课或讲座等,实现民间文学类非遗文化与校园特色文化的融合发展,从而使更多大学生积极加入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场域中,实现场域的向外扩展。除此之外,研学课程是适用于全年龄段学生群体的有效传承方式,通过为学生提供实地体验和考察的机会,使学生真正进入民间故事讲述的“原生态”场域中,亲身体验民间故事的原本面貌和无限魅力,避免因民间故事仅仅活跃于舞台表演这类“去语境化”的传承形式之中而走向僵化。
构建人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命运共同体,构建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的核心场域。核心场域围绕人与文化的双向建构展开,对其有效建构是实现场域内外社会公众彼此联动和场域扩展的重要途径。民间文学类非遗是一种基于大众共享的习俗和价值观的精神生活传统,其传承基本涉及广大公众支持和分享这一传统的能力,以及基于此形成精神和文化社区的能力,需要人民大众筑牢自身与非遗文化的共同体意识,构建人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在保护和发展民间文学类非遗方面,其主体并不局限于政府、企业和传承人群体,场域内外的普通民众是更重要的参与者和主人翁。有必要建立分享、保护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我组织机制,依靠广大公众的能力,鼓励公众对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广泛参与,依靠广大群众的能力,鼓励和吸引所有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和项目,这是民间文学类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资源。重要的有以下几点,应重视场域内社区的重要作用,加强社区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社区”“群体”和“个人”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2015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进一步强调了“社区”“群体”和“个人”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对该地区非遗的知情权和参与感。在这里,“社区”“群体”和“个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承载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因素。加强社区参与的前提是加强文化的自我意识,使社区来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到自己文化的内在价值,对当前的文化生存危机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从被动的“输血式”保护变成主动的“造血式”保护。如在当地建设民间文学类非遗传承单位,鼓励居民无偿或低偿向社会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针对社区居民中的学生群体,同样应当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使其成为民间文学类非遗文化教育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等。
要采取市场化方式,促进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乡愁”泛滥与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人民大众的文化消费行为和习惯的养成,才能真正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边缘化的困境。需要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实现文化与市场的双向互动,推动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民间文学深植于当地文化传统,并有相应的遗迹可寻,可作为地方名片彰显本地历史风光,作为旅游文化资源被开发,实现“以文促旅”这一文旅融合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生产文创产品的方式投入市场,即“非遗+旅游”“非遗+文创”两种模式。
在“非遗+旅游”的模式下,可以采用“非遗+品牌”“非遗+景区”“非遗+节庆”“非遗+研学”四种具体形式实现民间文学类非遗的活态化传承。“非遗+品牌”是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的重要途径,走马镇和广阳镇可以利用本地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积极借助先进技术,培育打造非遗旅游商品品牌,从而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非遗+景区”指的是将非遗文化全面渗透到旅游景区中,古驿道是走马镇民间故事形成的重要因素,可以借助驿道旅游开发民间故事,设计驿道主题旅游线路,挖掘与驿道相关的民间故事,广阳镇作为重要的水码头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式开辟水上旅游线路,传承民间故事。这种模式可以为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构建一个自然发生的场域,打造民间故事主体的旅游路线,从而推动非遗的动态传承,同时也推动场域向外辐射,吸引更多场域外各种类型的主体进入场域中。“非遗+节庆”是凸显原生态民俗旅游特色的重要模式,经笔者实地考察发现,走马镇和广阳镇当地均有颇具特色的节庆活动,如走马镇的走马观花旅游文化节,广阳镇的“枇杷节”“龙舟会”等,且两地均已有相关“非遗+节庆”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具有优越的条件和实践基础进一步发展“非遗+节庆”的模式,将民间故事与当地民俗节庆深度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传承。“非遗+研学”不仅助力青少年对民间故事的了解与传承,还能从经济层面助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非遗+文创”的模式是打造以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为品牌的非遗文创空间,结合现代新文化理念,以传承非遗文化而原真性为基础,对民间故事等非遗项目内容、表现形式进行再度创新,实现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如打造典型故事人物形象IP、改编创作故事绘本等,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和自我造血、自我发展。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一个重要类别,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和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社会、艺术和历史价值。重庆市走马镇和广阳镇都是中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故事村”,其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由于文化场域的消失面临严峻的传承困境。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究走马镇民间故事和广阳镇民间故事的生成过程和当今面临的现状与困境,对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承场域进行了模型构建,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传承策略,将基本场域、支持场域、关涉场域、核心场域四者结合起来,力求最大效度地使民间文学类非遗重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