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假如鲨鱼是人》为例论文
2024-05-25 10:51:41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布莱希特热衷研究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陌生化”理论,重构一种能够引导观众反思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场,推动戏剧革命。在其创作的《假如鲨鱼是人》寓言中,鲨鱼被比作统治阶级,小鱼被比作受迫的工人阶级。鲨鱼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对小鱼施压,给“剥削”披上教育、艺术、宗教的外衣,蛊惑小鱼心悦诚服地服务于鲨鱼。布莱希特以寓言的形式再现阶级矛盾和新社会等唯物史观主题,促使读者反思资本主义并推动革命。
摘要:布莱希特热衷研究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陌生化”理论,重构一种能够引导观众反思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场,推动戏剧革命。在其创作的《假如鲨鱼是人》寓言中,鲨鱼被比作统治阶级,小鱼被比作受迫的工人阶级。鲨鱼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对小鱼施压,给“剥削”披上教育、艺术、宗教的外衣,蛊惑小鱼心悦诚服地服务于鲨鱼。布莱希特以寓言的形式再现阶级矛盾和新社会等唯物史观主题,促使读者反思资本主义并推动革命。
关键词:寓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布莱希特
一、引言
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热衷于研究涵盖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终其一生将哲学理念寓于文学、戏剧之中。他突破亚里士多德“三一律”式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框架,提出“陌生化”理论,并且融入历史辩证法。此外就布莱希特而言,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在提升戏剧表演技巧方面产生重要作用。其自身的戏剧思想被布莱希特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因此他在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政治艺术家”“共产主义艺术家”[1]。布莱希特期望通过陌生化的技术处理,使得观众与演员保持距离,理性洞察戏剧情节的发展,批判剧中人物的行为,促进观众反思资本主义并推动革命。因而他创作了多部脍炙人口、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的教育剧,如《三分钱歌剧》《例外与常规》《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等。
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莱希特和其家人自1933至1948年一路从德国逃亡至苏黎世,后又到丹麦、芬兰等地。也正是这段长达十五年的流亡生涯引发布莱希特重新审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观察不同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用文学作品提醒读者挖掘真相,掀起对抗旧社会的革命,例如从1949年起陆续出版的《K先生的故事》就是布莱希特反抗旧哲学的代表作之一。《K先生的故事》是一部批判社会现实的寓言集,每则寓言的篇幅较短,但言简意赅。K先生全名为考伊纳(Keuner),由于“Keuner”的发音在布莱希特家乡奥格斯堡一带的方言里和“Keiner”的发音相近,而“Keiner”又表示“无人”,因此间接体现了这部作品的比喻性与讽刺性。其中一则寓言《假如鲨鱼是人》即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巧妙结合的例证之一。
二、理论基础
(一)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术语中,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剥夺了生产资料,不得不以出卖低廉劳动力的方式换得生存。马克思主义以被资本家压迫的无产阶级为根基,布莱希特通过对该理论的学习,树立了为劳苦人民群众进行新戏剧创作的信念。布莱希特指出,“只有摆脱幻想的人才有驾驭生活的机会。劳动者不应该在思想上,而应该是在现实中,也就是通过打倒他们的主人而变成自己的主人”[2]。
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师承卡尔•柯尔施。柯尔施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系意识形态”[3]。如若抨击资本主义,则无疑表明将摧毁这些旧意识形态,进而产生由全新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新意识形态。柯尔施的哲思被布莱希特延展至史诗戏剧,表明台下观众能够从此种不同以往的戏剧形式中领悟新的社会意识,并主动对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辨。新戏剧形式的目的在于,让观众掌握新的生活素材与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使得他们发觉这是一种在旧戏剧艺术中并没有被囊括的新方法论,“这个社会存在是由观众自己所创造”[4]。布莱希特的戏剧创新致力于凸显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将旧社会已然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公之于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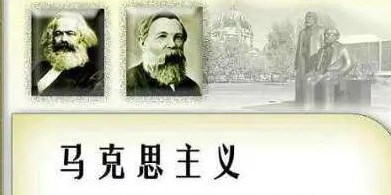
(二)“陌生化”理论
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释资产阶级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布莱希特也承认了亚里士多德“三一律”戏剧原理中的“共鸣”效果在旧时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他仍指出其在当下逐渐成为发展戏剧艺术的阻碍。为了跨越当时戏剧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布莱希特将具有鲜明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融入戏剧理论,提出“陌生化”理论,“终结剧情对思考、共鸣对反思、舞台对观众的专制”[5],以期借助戏剧展示的客观事实调动台下观众的主观能动性。
“陌生化”理论归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即将舞台上呈现的事物从观众熟知的角度抽离出来,并转变为陌生奇异形态,使观众对其产生惊讶与好奇,从而实现认识——不认识——更高层次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对旧事物产生新认识。如果观众一味沉浸于对故事情节的“共鸣”之中,就很难发现事物全貌,倘若他们从中抽身,对戏剧产生陌生感,就提高了形成批判认识的可能性,从而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
在“陌生化”理论中,布莱希特提出了“破坏剧场”的关键概念,使得人民群众足以挖掘当下社会中暗含的内在矛盾,从“在现代公共性、高度消费主义和市场主义所编织的叙事”中觉醒。“陌生化”理论的效果体现在戏剧舞台采用模仿真实事件的形式,挑明因果关系,以间离效果感动观众,提高观众的政治敏锐度。但是“破坏剧场”绝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或误读,也不是要脱去戏剧表演中所有感性的外衣,而是要让情感因素成为观众辨析的催化剂。因为“陌生化”与“共鸣”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方面布莱希特否定传统戏剧中“产生共鸣的机制”,阐明观众情绪不应当时刻被演员或作者牵引,而需要与其保持距离,坚持清醒思考,维持“主体自警”[6]。另一方面他阐明在“陌生化”的戏剧表演中需要维持观众的批判思维,“陌生化”效果可以起到娱乐大众的作用。评判戏剧的准则不再局限于是否引发台下观众的情绪起伏,还包括能否让观众对当下的社会阶级进行主动思考。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形成的苏联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明显的政治功能,剧作家必须从当下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绘社会现状,与此同时,其真实性应当与“以社会主义教育无产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它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在概括客观现实时“按照党性、人民性的原则,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在作品中再现革命进程,肯定社会主义现实,“塑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代英雄人物形象”[7]。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了让读者在自我辨析中探寻新社会的发展方向,尝试打碎旧社会体系筑起的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高墙。马克思主义对旧意识形态的驳斥与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抵抗一致诠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布莱希特持续对编剧导演和舞台技术进行创新,再次将全新的政治内涵寄予旧式戏剧,而并非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在戏剧中的艺术价值。
马克思有关环境的哲学思想给予布莱希特在戏剧创作和舞台布景方面极大的提升。在马克思的哲思中,革命的实践过程恰恰体现在环境与人类自我意识同步变化的进程中。基于这一观点,布莱希特对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表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将发展成为“在劳动中进行的、社会性的、不断变化的过程”[8]。毋庸置疑的是,在戏剧表演方面人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必须展现在舞台布景上。新戏剧的宗旨不在于让观众对戏剧中虚构的人性矛盾产生愤懑情绪,而应当使观众洞悉故事情节发展背后的阶级与社会矛盾。
三、寓言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寓言集《K先生的故事》中的《假如鲨鱼是人》体现了布莱希特政治艺术化、艺术政治化的写作手法。该寓言围绕K先生与房东小女儿的对话展开,女孩将鲨鱼想象成人类,K先生为其阐释拟人化鲨鱼的生活习性与社会体制。
(一)“陌生化”理论在寓言中的应用
该寓言的题目与开篇第一句“假如鲨鱼是人”,以及作者使用的第二虚拟式,体现了布莱希特独具特色的“陌生化”理论,把鲨鱼抽象化,剥离其动物属性,并赋予人类的情感色彩。房东的小女儿由于其天真烂漫、幼小稚嫩,把凶猛的海洋生物拟作拥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既符合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得这一想象具有合理性,又让读者对“鲨鱼”这一原本熟知的物种感到陌生并产生好奇,起到间离效果。因此,读者在理解作品时能够不局限于鲨鱼凶残冷血的猎杀属性,而多与脾性复杂的人类挂钩,用评判人类的视角审视寓言中的鲨鱼形象,从而形成对鲨鱼的更高层次的新认识。
该寓言的第一段,即房东小女儿的疑问则开门见山地把海洋鱼类分为两大阵营:鲨鱼和小鱼,从而为下文展现双方多对矛盾埋下伏笔。“陌生化”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让观众对所处的现实社会进行自觉反思,所以布莱希特在开篇就将读者置于疑问之中:如果鲨鱼拥有人类的思维方式,他们会善待小鱼吗?以期读者预先独立思考,再理解K先生所阐释的拟人化鲨鱼与小鱼的行径。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寓言中的应用
K先生在后续的对话中给房东童真的小女儿描绘了一幅鲨鱼与小鱼共存的生动图景,鱼类拥有人类的思想与意志,并且能够像人类一样生活,因而寓言中的两种鱼类就带有人类社会的阶级性,分别对应两大对立阶级,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1.鲨鱼
就鲨鱼而言,他们占支配地位,拥有较高的权力,能够管辖小鱼,为小鱼提供各类基础设施,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驯化小鱼为其服务。
(1)建造坚固笼子。虽然坚不可摧的笼子可以给小鱼提供安全保障,免受其他海洋生物的袭击,但同样也是限制自由行动的桎梏。小鱼仅仅能够在有限范围内活动,如若擅自出走将面临被捕食的风险。此外,将小鱼固定在规定空间内便于鲨鱼进行统一管理、集权控制。
(2)实施学校教育。为了进一步操控小鱼的精神与思想,鲨鱼会建造学校,给小鱼进行统一授课,传授知识的同时将其思维定式化,使其坚持以信奉鲨鱼、服务鲨鱼为本。
(3)举办大型节日。正如负伤小鱼口感不佳,郁郁寡欢的小鱼同样也会影响自身品质。为了使小鱼肉质更鲜美,鲨鱼会组织筹划大型海底庆祝活动,麻痹小鱼的意识,使其忘却烦恼,享受精神娱乐。当小鱼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时,他们的自我意识被逐渐削弱,从而极少产生抗拒或敌对情绪,主动服从于上层管理。
(4)发展“高雅”艺术。在被允许展出的画作或摄影作品中,鲨鱼的血口被描绘成五彩缤纷的乐园,从而放低小鱼的防备戒心,认为鲨鱼并非恐怖可怕的势力而是能够给小鱼带去欢乐的“大朋友”。这类“高雅”艺术能够迷惑小鱼心智,从精神层面统治小鱼为鲨鱼所用,推崇利于鲨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且使小鱼心悦诚服地游入深渊。在鲨鱼的精神统治下,小鱼逐步丧失自我意识与反抗条件,他们抱有使鲨鱼饱腹的终极目标,能够心旷神怡的虔诚赴死。
(5)发动血腥战争。鲨鱼并不满足于管理自己族群内的小鱼,并希望扩大自身的管辖区域与权力范围,因而以小鱼为棋子,向其他族群发起攻击。此外,鲨鱼时常强化不同族群小鱼之间的差异性,规避小鱼群体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组成威胁鲨鱼的坚实力量。
2.小鱼
就小鱼而言,他们占从属地位,必须履行鲨鱼规定的各项义务,并在物质与精神上依赖于鲨鱼,倾尽所有服务于鲨鱼。
(1)接受学校教育。一方面,小鱼需要学习快速游动技能和地理知识,以体型大作为衡量自身优秀与否的标准,从而为鲨鱼提供定向服务;另一方面,小鱼必须以接受道德教育为根本任务,从小培育他们绝对服从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不仅应当服务于一般鲨鱼,还要将自己奉献给具有特权甚至不作为的鲨鱼。小鱼应该遵循为鲨鱼无私奉献的道德标准,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将鲨鱼视作上帝,毫不动摇地相信鲨鱼为其勾勒的未来蓝图。同时,小鱼如果希望得到鲨鱼的保护,必须服从鲨鱼的各项指令,不得产生自我意识。
(2)排除异己小鱼。小鱼需要抵制与怀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鱼群为伍。鲨鱼认为卑劣自私的马克思主义与其期望教导小鱼“无私奉献”的品质背道而驰,反对小鱼注重自身发展,只要教条地生长为肉质鲜美的可食用鱼即可。此外,小鱼需要检举揭发拥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类,扼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萌芽。
(3)参与无情杀戮。为了实现鲨鱼争夺海域与小鱼的目标,小鱼被当作士兵派往前线,以极端暴力的手段征服其他族群。小鱼接受鲨鱼的“差异论”,只有本族群才能接纳小鱼,打击其自信心,从而一味归顺于本族群的统领,丧失齐心协力、起义反抗鲨鱼的基本条件。在战争中,杀“敌”无数、立下战功的小鱼将受到表彰,借此向其他小鱼宣扬浴血奋战的精神,希望所有小鱼都为鲨鱼所用,杀敌愈多愈受尊敬。相比之下,鲨鱼身处高位,坐享其成,“欣赏”小鱼之间血肉模糊的斗争。
(4)缺乏沟通交流。同一族群内部的小鱼不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随大流、服从命令是他们一生的归宿;不同族群间的小鱼由于缺乏通用语言,导致交流受阻,从而无法意识到虽身处不同族群,但均为在海洋生存的小鱼,甚至可能同属于一种类别,不应当自相残杀。正如《圣经》中的“巴别塔”传说,众志成城的人类欲一同构筑通向天堂的巴别塔。然而,上帝用不同语言阻碍其沟通交流,最终破坏巴别塔计划,致使人类的美好愿望落空。
(5)恪守森严等级。在除鲨鱼外的普通鱼群间仍可以分为大鱼和小鱼,并存在一套严格的统治机制,等级极为森严。在这一个世界中消灭不服从管理的小鱼,以鲨鱼利益为导向,在思想教育、军队建设、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以统治阶级为本。
综上所述,布莱希特借K先生之口,将鲨鱼比作人类社会的资产阶级,小鱼比作受到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将两大阶级生存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内在矛盾呈现在寓言中。鲨鱼在物质和精神上均对小鱼进行严格约束与控制,杜绝小鱼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小鱼身处于森严的等级机制中却毫无察觉,依旧心甘情愿为鲨鱼赴汤蹈火。布莱希特希望借该寓言针砭时弊,点明社会弊端,警醒当时社会被压榨胁迫的工人阶级,应当从统治阶级布设的囚牢中挣脱出来,奋起反抗。
四、总结
布莱希特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风格已无法满足当时民众的精神需求,只有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戏剧理念,引发新的戏剧形式,才能推动戏剧进步。在《假如鲨鱼是人》中,鲨鱼在海洋中属于霸主类型,是凶猛残忍的肉食动物,捕食比其弱小的鱼类;小鱼身处低位,被要求服务鲨鱼。反观人类社会,统治阶级欺骗蛊惑被统治阶级,要求民众坚持顺从,拒绝反抗。布莱希特通过这则寓言用鲨鱼文化反讽当时的人类社会,希望世人发现社会问题,引导读者在自觉反思中获得阶级意识,劳动人民应当联合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霸权,重获自由。
参考文献:
[1][8]包大为.布莱希特的“戏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学实践及其未竟使命[J].文学评论,2019(01):13-19.
[2][4][5][6]贝尔托•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李健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7]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