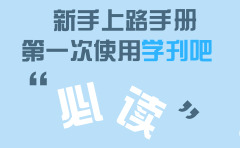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的研究回顾论文
2024-06-12 09:11:53 来源: 作者:liangnanxi
摘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其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行稳方能致远,在此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有效应对各项挑战。金融稳,经济才能稳,守住金融安全底线必须增强防范意识,准确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可能的风险隐患点早预判、早处置。近年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文章从微观度量和宏观度量两个角度分类整理了现有文献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方法,并展望了后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的成果,从而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防控提供理论依据,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定增
摘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其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行稳方能致远,在此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有效应对各项挑战。金融稳,经济才能稳,守住金融安全底线必须增强防范意识,准确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可能的风险隐患点早预判、早处置。近年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文章从微观度量和宏观度量两个角度分类整理了现有文献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方法,并展望了后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的成果,从而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防控提供理论依据,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传染;风险度量
引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抓好2023年——推动“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的社会经济工作。当前,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经济下行给我国“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带来挑战。实体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血脉通,经济才能加速回升,所以要统筹好安全和发展,完善金融监管,未雨绸缪,有效防范,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首先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特性的角度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给出的定义;其次对现有研究提出的微观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归纳各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最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当它发生的时候,却能感知到它的存在,很难用一个终极的定义对其进行刻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机构认为单个或某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受到冲击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系统性风险的交叉传染进一步诱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金融服务被迫大范围中断,最终实体经济不免遭受巨大损失。学术界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讨论,一类定义突出了其广泛性的特点,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面性的风险,在影响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同时,也波及实体经济[1],一旦爆发危机,任何个体都难以做到独善其身,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损失。另一类考察的出发点则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机构间相互紧密关联导致系统性风险多渠道交叉传染,进而引发金融机构的联合破产,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2]。还有部分学者强调较小的冲击也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从金融系统考虑,全部金融机构、市场同时遭受严重外部冲击会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复杂金融体系网络中一个或者多个节点发生故障,风险的跨机构、跨部门、跨市场交叉传染与叠加共振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3]。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认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传染快、涉及广、危害大的特征。
(二)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
为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防、解决、问责体系,守住金融安全底线,有效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准确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系统性风险的定义不统一,内涵也比较丰富,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视角提出了众多测度方法。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学者们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等方面,构建整体指标来反映系统性风险[4],但是这类测度方法存在严重的滞后性[5]。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基于信用违约互换(CDS)价差和高频股票数据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框架,即困境保费溢价(DIP),该方法显著提高了测度的准确性,同时也对CDS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后,业界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普遍采用在险价值VaR测度资产组合的风险,该方法计算简单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考虑到金融机构与整个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

Adrian等(2016)在VaR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条件在险价值CoVaR[6]。CoVaR表示一个特定机构处于某种状态的条件下,其他机构或者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价值。将特定机构处于危机状态时其他机构或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价值与处于中间状态时的风险价值作差得到的ΔCoVaR是一个方向指标,将其方向颠倒得到结果Exposure-ΔCoVaR,其测度的是其他机构或整个金融系统陷入危机时,该机构的风险敞口[3]。一致性风险测度应该满足单调性、次可加性、正齐次性和平移不变性的约束条件,CoVaR、ΔCoVaR和VaR一样不满足可加性,无法以此方法测度金融体系的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且CoVaR方法仅关注了单一分位点上的期望损失,并没有关注损失分布α分位数以下的尾部风险。
与CoVaR不同,Acharya等(2010)提出的边际期望损失MES关注的是在发生系统性危机事件时特定机构的预期损失,并且该指标具有可加性,很好地解决了CoVaR存在的问题。不过,MES方法没有考虑到金融机构自身特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7-8],测度金融机构对系统风险的贡献程度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容易夸大低杠杆率和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系统的重要性,这严重背离了金融风险监管实务。Brownlees用MES同杠杆程度综合考虑得到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来度量系统性风险,改进了MES方法没有考虑杠杆程度的局限,MES、SRISK指标都反映了金融机构的资本短缺程度,不同的是SRISK强调了更长期间内的资本短缺。Brownlees等在2017年进一步改进了SRISK方法,包含机构规模、杠杆水平和长期边际期望损失LRMES三个层面的信息[8]。关于SRISK方法的运用,许多学者直接采用Acharya等(2012)所提出的“LRMES近似等于1-exp(-18*MES)”来度量LRMES,并以此为基础计算SRISK值。但是该近似关系是基于美国金融体系数据得到的经验,并不适用于我国的金融体系[9]。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晓玫等(2014)将我国金融系统面临的危机事件定义为“上证综指在未来连续六个月内下跌40%”,LRMES就是发生该长期系统性事件时金融机构的边际期望损失[10]。现在,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MES和LMES方法需要对系统性危机事件进行定义,测度结果的准确与否高度依赖对长短系统性事件的定义。为此,Qin等(2021)提出了一种不依赖参数尾相关假设的渐近边际期望损失AMES估计方法,将系统性风险分配给各金融机构,该方法基于多元极值理论(EVT),不需要用一个系统指标来定义金融系统的压力。然而,在EVT建模过程中,阈值的确定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上述MES、CoVaR、ΔCoVaR、SRISK等指标都是基于金融市场数据来度量系统性风险,可获性和时效性强,能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监测。但是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决定了指标的可信度、准确度[11],就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并不具备较强的有效性。随着金融风险研究的不断发展,有学者利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信息计算系统性风险,此类方法不仅摆脱了使用高频市场数据的局限,还拓宽了测度对象的范围。例如,何宜庆等(2020)基于主成分分析法,从多个维度选取基础指标构建风险综合指数;Zedda等(2020)基于“去一法”衡量单个金融机构对危机的责任份额[12];曹琳等(2017)采用或有权益分析方法构建了三类上市银行CCA风险指标:隐含资产价值波动率、违约概率和违约距离。虽然基于财务数据的Z-Score法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方法,但它仍被广泛用于评价银行机构的风险。通过纳入分析师的预测,Hafeez等(2022)对Z-Score法进行改进并提出了前瞻性Z-Score法,实证结果表明前瞻性Z-Score与违约概率和系统性风险度量显著关联,可以为银行未来的盈利能力提供预测信号。前瞻性和逆周期性是检验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指标有效性的两个重要标准[13]。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积聚是传染爆发的前提,符合标准的指标应该能对风险的潜在积累进行刻画,为有效预防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支撑。Adrian等(2016)[6]提出的Forward-ΔCoVaR就兼具前瞻性和逆周期的特征,使人们能够观察到通常发生在平静时期的系统性风险积累。同时他们还利用MES的思想改善了局限,提出了CoES这一构想,该指标相比CoVaR包含了更多信息。在此基础上,为了能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实现有效的预警,李政等(2019)提出同时构建下行和上行ΔCoES指标来进行风险的同期度量和前瞻预警[3]。
(三)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度量
金融系统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从微观层面单独测度特定金融机构的风险贡献并不能反映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水平,不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宏观把控。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跨机构、跨市场的交易合作日益频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量化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
一类研究重点关注金融主体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波动溢出、尾部风险关联以及收益率关联。使用最广的研究方法是基于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构建指数来刻画金融主体两两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宫晓莉等(2020)就采用此方法建立了我国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网络。然而,上述研究仅考虑了下行金融风险的溢出冲击。为守住我国金融风险安全底线,上行风险的溢出传染也不容忽视。通过已实现的半方差方法将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之后,李政等(2022)研究发现中国行业间的好坏波动溢出存在非对称性[14]。在尾部风险方面,Nikolaus等(2015)将LASSO分位数回归与条件在险价值CoVaR模型相结合,构建了美国银行业尾部风险网络[1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常用于检验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中,有学者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金融主体的成对线性依赖关系,并结合前沿的网络分析法研究金融主体之间的风险传染。基于此方法,Billio等(2012)使用美国金融机构的数据评估了收益率的关联关系,以此考察了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然而,非线性的金融时间序列可能会使得以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基础的风险传染评估产生偏差。鉴于此,杨子晖等(2020)在非线性框架下测度了金融风险在市场之间的非对称传染[16]。当然,Copula函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等方法也可以估计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余博等(2021)采用Clayton Copula函数方法得到金融机构之间的下尾依赖系数,再结合最小生成树(MST)模型构建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尾部依赖网络[17]。基于DCC-GARCH模型得到三个金融市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之后,方意等(2019)进一步采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外部冲击事件对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影响[18]。已有研究对变量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时,往往忽略了变量频率的不同,为减少因高频率变量降频造成的信息损失,杨子晖等采用了基于MF-VAR模型的混频因果检验考察了极端风险在多个部门之间的交叉传染。
另一类研究则在探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渠道。现有文献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渠道归纳为基本面渠道和其他渠道。具体而言,基本面渠道体现为由于金融主体之间的直接贸易、市场竞争联系,面临外部冲击时金融主体之间的风险传染,而且资本流动频繁的金融主体之间风险传染更加严重[19];其他渠道和投资者行为相关,受到负面冲击时,只了解不完全信息的投资者对金融主体基本面的重新评估、风险偏好的转变等因素会改变投资者的决策结果,投资者后续的一系列行为将会引发金融风险的跨机构、跨市场、跨地区传染[20]。金融主体之间的关联性是放大外部冲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银行间债券债务直接联系,在外部冲击下破产的银行债务违约会使得本来未破产的债权银行遭受损失、面临破产风险。杨子晖等综合“去一法”和仿真模拟,考察了这种债务银行偿付能力降低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分析了风险的影响因素。与破产传染机制不同,资产抛售传染关注的是金融主体因为持有相同或者相似资产形成的间接关联。受到冲击,银行的杠杆率升高,银行被迫抛售资产以实现去杠杆达到监管要求的目的。方意等分析了微观和宏观审慎两种抛售政策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的共同作用,整合了破产传染的直接关联模型和资产降价抛售的间接关联模型,并使用整合后的银行网络模型分析了不同力度冲击下的核心风险传染机制;具体来说,破产传染是大冲击的核心机制,面临较小的冲击时银行系统主要遭受降价抛售机制带来的损失[21]。在我国现行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下,我们难以取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双边敞口的相关数据,上述研究都是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并采用最大化信息熵方法来建立银行间资产负债矩阵。
二、小结及建议

综观国内外学者在微观层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首先,从数据信息的角度来看,MES、CoVaR、SRISK等指标大都是使用高频的市场数据来确定金融机构在极端状态下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是这些方法准确度的基础,我国金融市场的弱有效性削弱了此类度量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好在学者们开始重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等信息,并将其运用到金融风险度量中,提出多种基于低频财务数据的金融风险测度指标。其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度量应当克服系统性危机事件定义、阈值选择等主观性问题。另外,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经过积累后爆发释放的极端情形,在构建金融风险度量指标时,我们应强调指标的前瞻性和预警性,避免出现顺周期问题。
从宏观视角来看,学者们构建网络模型来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主体之间的溢出传染。一方面,有学者从不同视角量化金融主体之间风险的输入输出,以此为基础定性判断系统重要性和系统脆弱性金融主体,但是此类研究没有考虑到网络模型的整体关联性,不能全面地考察由系统性冲击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学者通过建立网络模型,研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主体间的传染机制。然而研究者很难获取金融主体的内部资产和主体间债券债务的详细数据,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机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可以更有效地量化系统性金融风险。当然,金融主体之间还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网络传播,今后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网络模型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还应当考虑到不同网络之间的相互依赖。
参考文献:
[1]李绍芳,李方圆,刘晓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跨市场传染研究——基于G20国家的经验证据[J].金融评论,2022,14(3):1-38+124.
[2]郭晨,吴君民,宋清华.银行系统性风险多渠道形成机制及测度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42(5):1129-1145.
[3]李政,梁琪,方意.中国金融部门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监测预警研究——基于下行和上行ΔCoES指标的实现与优化[J].金融研究,2019(2):40-58.
[4]BORDO M D,DUEKER M J,WHEELOCK D C.Aggregate price shocks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A historical analysis[J].Economic Inquiry,2002,40(4):521-538.
[5]白雪梅,石大龙.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度量[J].国际金融研究,2014(6):75-85.
[6]ADRIAN T,BRUNNERMEIER M K.CoVaR[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7):1705-1741.
[7]宋清华,姜玉东.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基于MES方法的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35(6):2-7.
[8]BROWNLEES C,ENGLE R.SRISK:A conditional capital shortfall measure of systemic risk[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7,30(1):48-79.
[9]陈湘鹏,周皓,金涛,等.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比较与适用性分析——基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9(5):17-36.
[10]张晓玫,毛亚琪.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与非利息收入研究——基于LRMES方法的创新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2014(11):23-35.
[11]杨子晖,陈雨恬,林师涵.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献综述:现状、发展与展望[J].金融研究,2022(1):185-206.
[12]ZEDDA S,CANNAS G.Analysis of banks'systemic risk contribution and contagion determinants through the leave-one-out approach[J/OL].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20,112(C).
[13]方意.前瞻性与逆周期性的系统性风险指标构建[J].经济研究,2021,56(9):191-208.
[14]李政,石晴,温博慧,等.好坏波动、行业关联与中国系统性风险防范[J].财贸经济,2022,43(9):53-68.
[15]NIKOLAUS H,JULIA S,MELANIE S.Financial network systemic risk contributions[J].Review of Finance,2015,19(2):685-738.
[16]杨子晖,陈里璇,陈雨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的研究[J].经济研究,2020,55(1):65-81.
[17]余博,邹宇翔,管超.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重要性研究——基于Clayton Copula函数方法和MST网络模型[J].保险研究,2021(6):11-27.
[18]方意,和文佳,荆中博.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J].财贸经济,2019,40(6):55-69.
[19]BOSTANCI G,YILMAZ K.How connected is the global sovereign credit risk network?[J/OL].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20,113(C).
[20]BEKAERT G,EHRMANN M,FRATZSCHER M,et al.The global crisis and equity market contag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4,69(6):2597-2649.
[21]方意,荆中博.外部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J].管理世界,2022,38(5):19-4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