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艺术复调下的《击石舞》研究论文
2023-03-09 09:37:32 来源: 作者:lvyifei
摘要:摘要:古代西域的绿洲是东西方交往的中间枢纽,各地与之的贸易往来甚为广泛,造就 了 经济 、文化 、政治的多方面的融合交流态势,广纳了 当时东西方乐舞文化之长 。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形成了 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众多民族 。 它们不仅传承了古西域乐舞文化的精髓,而且也创新发展出了韵味悠长的绿洲文化艺术脉络 。多元 、和谐 、融汇 、纷呈的有价值的“声音”建构出了独具核心 意义的绿洲艺术复调 。如果说地理因素是绿洲艺术的物质载体,那么绿洲艺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域文化之源泉,具有不竭的动力 。 以此出
摘要:古代西域的绿洲是东西方交往的中间枢纽,各地与之的贸易往来甚为广泛,造就了经济、文化、政治的多方面的融合交流态势,广纳了当时东西方乐舞文化之长。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众多民族。它们不仅传承了古西域乐舞文化的精髓,而且也创新发展出了韵味悠长的绿洲文化艺术脉络。多元、和谐、融汇、纷呈的有价值的“声音”建构出了独具核心意义的绿洲艺术复调。如果说地理因素是绿洲艺术的物质载体,那么绿洲艺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域文化之源泉,具有不竭的动力。以此出发,本文对在绿洲文化中以维吾尔族民间舞蹈表演的“四块瓦”为雏形的“击石舞”进行了深入的考析与对比。
关键词:绿洲文化;艺术复调;击石舞;形态研究
一、绿洲艺术复调的文化溯源
“绿洲”顾名思义,就是沙漠中蕴含水源,可耕种农作物之地。它的特征无论是从广泛性还是延伸性而言,都会因其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譬如,因过分依赖土地的水源,人们的耕种条件受到了限制,农作物品种也会有所不同。当然,耕种面积也不能无条件扩大。由此,绿洲的地理环境所罗列的一些条件,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宣告出了它的阻塞性和孤助性,但是,往复循环的历史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为亚欧搭建了经济贸易交往、文化艺术沟通的桥梁,而且也使得西域绿洲文化成为了丝绸之路发展要道上的一颗璀璨星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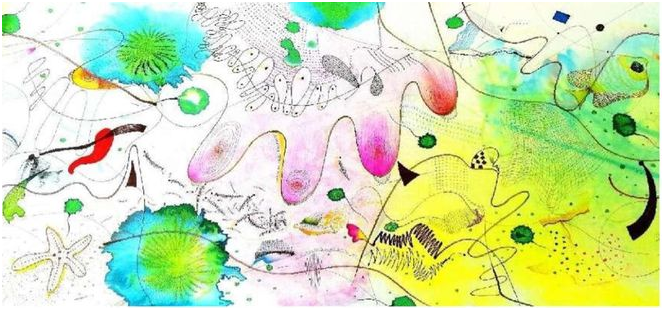
绿洲文化的形成伴随着农耕文化的开拓,以绿洲为托付的农耕文化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习俗以及社会条件,均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致。在整个文化体系的背景下,相近的劳作方式、生产条件、生活习惯凝练出了相同类别的艺术之脉。然而,基于民族信仰、生态环境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些艺术形态也是各有所长,不分伯仲。笔者借用巴赫金的言语“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呈现,有许多各有充分的价值(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将这则话应用于绿洲艺术复调的现实环境当中也是不足为过的。其实,谈及这里不由得使笔者联想到一些端倪。
例如,绿洲艺术复调的建构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是部分区域的,还是多方向、多民族发展的呢?据此,我们不妨旁征博引以西域文化类型为参考,以理性思维横纵坐标为导向去进行考析。因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生活行为、民族心理归属感以及思想表达方式等彼此相互的差异,我们将西域的文化型可以分为纵坐标上以零点为分界的北部和南部。即“北部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劳作相结合的草原游牧文化,南部则是绿洲与农耕生产共存的绿洲农耕文化,还有一种即是以屯垦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因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法制度的复合型被称为复合文化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绿洲艺术复调不是单一的文化倾向,而是复合型的客观事实。况且,今日新疆的十三个世居民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玫族、乌玫别克族等众多民族也是绿洲艺术这片沃土上的鲜明写照,绿洲艺术绝不是单一民族的一枝独秀,而是众多民族的花团锦簇。针对于绿洲艺术复调文化溯源的剖析,不仅可以让东西方文化沟通交流日益密切,彰显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相互融汇和相互吸纳,而且可以更好的发扬乐舞文化博采众长的特点。据笔者随想,绿洲艺术文化的产生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现实生活需求的必然,而是我国各区域、各民族、各文化间相互交织与共的累累硕果。如果我们换一个视域的角度去阐释绿洲艺术复调的发展,则会不假思索地考虑到两种方向性的沿革,即平行与交叉。任何“民间工艺艺术与美术的创造,始终由实用与艺术双重动机驱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双重活动创造的,从而其功能价值也是多重的,除了实用,还必定有艺术与审美价值”。所以,绿洲艺术的发展同样也普遍存在于上层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分流审美状态之中,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面临着沟壑不可逾越,也并非是可以在平行与横向间无限拓宽的。正是基于上层艺术与民间艺术的驳杂交叉发展才构建出了多元的、完整的、有机的绿洲艺术复调文化。例如,《木卡姆》乐舞的流传就恰如其分的印证了上层艺术和民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歌乐舞为一体的套曲《木卡姆》中的“麦西来甫”更是在不断的传承与变异中衍生出了多种综合娱乐活动形式,包括节日麦西来甫、音乐麦西来甫以及青苗麦西来甫等。与此同时,《木卡姆》中歌舞表演部分——麦西来普,这种跳、学、教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正是被民间艺术的雨润所恩泽才成为了绿洲艺术大花园中的一枝独秀。由其而言,这种多形式、多区域、多文化的高度融合,不也是对上层艺术和民间艺术的一种交叉与融汇之必然吗?故此,“绿洲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复调艺术”。
综上所述,绿洲艺术复调的文化溯源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绿洲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所致。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围边缘风沙裹盖,人迹罕至,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绿洲单位体。他们自成脉络互不干扰,在各自拥有的范围内自我生存、自我给予、自我发展。即使在地理环境条件不够充裕的前提下,也能使之发挥自身优势。加之,伴随着独立的绿洲艺术的审美需要,其继而升华出了绿洲艺术自我空间的吸纳意识;二是上层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不断融合。在罗雄岩学者编著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一书中就有所解释到——传统文化中的两种文化即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我们姑且避开其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风姿呈现,就其二者的关系来探讨。两者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这边就是上层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不断融合的表现;三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为绿洲艺术培育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随着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汇集,众多民族的加入使之绿洲古道颇负盛名,形成了多元和谐的局面,而绿洲艺术也在不断地调试中保持着自我发展的脚步,以民族烙印为积淀、以多元文化为厚度、以时代精神为脉搏、以历史底蕴为依托,不断发展,博采众长!
二、《击石舞》的形态阐述
击石舞又名“它石舞”“塔什舞”,流传于我国新疆南部地区的和田、阿克苏莎车、喀什一带。因由男子一两人即兴歌舞且手拿“击石”边击边舞而得名。据笔者调研得知,击石舞这种手持石片而舞的表演形式,一般由维吾尔族男子进行实地表演,不过现在的击石也大部分被钢或铝片所代替。如果追溯其道具的产生,就不得不提及素有“玉石之都”“地毯之乡”的墨玉县,它归之于和田,在古西域时期被称作为于阗。这一带物产丰厚,底蕴十足,地理位置优越特殊。着眼于西域文化区域的特点,以西域绿洲农耕文化为首的于阗文化就显得尤有格调,这种区域性的艺术表征在多种形态、多种风格、多种韵律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一种复调的动态走势。
(一)击石舞的音乐形态
舞者击石时应用力将两个石片合击,使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音,按《赛乃姆》的下述两种节奏型边击边舞(见图1):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要点是:重拍用谱曲中的“冬”来表示,根据传承艺人现场表演指导时可知,舞者一般用手单击或者是左右手同时合击的方法来显示音乐节奏型的重拍,突出其特点;弱拍用谱曲中“大”来表示,使两片击石迅速碰撞,以音乐节奏变化为多样性,在不破坏基本节奏韵律的基础上击打出花样的节奏型。谈到此处,我们对于音律可能并不陌生,不过在这里为什么要以“赛乃姆”的节奏音型取而代之呢?其实“赛乃姆”一词起源于音乐节奏变化的名称,因其节奏平缓稳健,普遍适用于各种曲式、律调,而被广大音乐舞蹈人士所接纳,且实践应用在了舞蹈表演之中,成为了自娱、礼俗、表演性较强的歌舞形式之谓。
(二)击石舞的舞蹈形态
新疆的歌舞大部分都带有表演性特征,这和古代西域乐舞遗风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人们给歌舞的表演都披上了新的裘衣,即使有一些舞蹈可能慢慢的消逝了,但其仍然会有一些形式与动作留存在民间舞蹈之中。这就使得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风格特征主要集中于节奏动律的变化、舞姿造型的特征以及技术技巧等方面。例如:“四块瓦”艺术的流变就对此做出了一定的阐释。“四块瓦”原本是“曲艺表演的道具和戏曲伴奏的击打乐曲,一般用竹片制成长约12厘米,宽约4厘米,表演者两手分握两片碰击敲打,声音清脆”。此观点的解释无疑与新疆民间舞蹈当中《击石舞》道具的描绘不谋而合。实则不然,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当中亦流存着这种“四块瓦”的舞蹈形式。譬如,回族将“四块瓦”称作为瓦子,主要实践于宴席曲当中,只不过因不同地区(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的不同风俗习惯,宴席曲的表演形式也不尽相同。不过针对于这种道具与技艺的相互结合的形式,我们仍能捕捉到那时西域乐舞的遗风韵味。
1.基本动作
击石舞的基本动作多沿革于赛乃姆,其脚下步伐主要有垫步、前后点步、跪膝等变化。手部动作更多的是两臂平伸与肩部持平或者一手在头部上方,一手在胸前,相互交换。击石舞的动作大多以节奏音律的变化而层起彼伏,复杂多样且极具魅力。不过究其程式化动作,更多的是以“踏步蹲击石”“跪蹲击石”“垫步击石”“颠跳击石”等基本动作为罗列。
踏步蹲击石:这一动作的展示是以踏步半蹲的两腿之间为重心,可以随意前后移动,同时双臂屈肘在身体之前做击石动作。在这一过程中,双手击石的力度、节奏可以跟随自我的情绪随心而动,即兴而舞。男子一般表现出洋洋得意、碎摇头之状,以表达心情愉悦之感。
跪蹲击石:在维吾尔族舞蹈中,跪蹲、跪膝等动作的衍化是最为常见的。无论是男子舞蹈还是女子舞蹈,对于跪和蹲等动作的衔接突变都是维吾尔族民间舞蹈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形式。例如,中国民间舞维吾尔族男班教材训练中就把单一训练的跪蹲元素作为了民间舞课堂教学组合的重要一环。
垫步击石:此基本动作主要是以左右横向移步,前后点步为步伐基调。加之以双臂微微弯曲,向斜前方做击石动作,同时身体朝向的点位以微度拧身作为舞蹈审美的准则。
颠跳击石:颠跳击石动作的形成并非可以一拍即合,坐地为型。而是要在衔接过程中完成的,由表演者双脚腾跃置身跳起为触点,再以落地盘腿而坐为雏形。在这样的基础上,表演者亦可前后左右颠跳移动,双手以击石相伴。
总之,舞者在表演过程中以基本动作为穿插衔接,至高潮时欢呼腾跃。正是基于此表演方式的发展,才使得击石舞的表演在民间表达中与盘子舞的结合才如此的具备细嗅蔷薇之感。谈及《盘子舞》就不得不提到绿洲文化的舞人——阿吉·热合曼的表演,他的舞蹈技艺高超,表演过程中盘子的转动和击石的打奏就像一根连接起演员与观众的纽带,动作的衔接一步步的将氛围迭至了沸腾并久漫不逝。
2.服饰特征
《击石舞》的服饰与维吾尔族《赛乃姆》的男子服饰略有相似之处,其中男子的外套可以分为长袍、短衫、长衫、坎肩等类别,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以长袖衬衫为主要演出服饰。男子的帽子因为材质不同可以分为皮质帽子和花式秀帽。然而,在舞台呈现的过程中还是以花帽为主要配置。值得一提的是,男子的腰带也有不同的装饰及说法。笔者前往阿图什地区调研时得知,因为每个表演《击石舞》的演员的年龄都是有所差异的,所以他们的服饰装扮也会略微不同。这点是笔者在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时候有所疏忽和思虑不周的地方。中老年男子在表演《击石舞》时,因其思想观念的传统化、单一化、规矩化,使之着装更多的是以长袍对襟、袖衫、靴子、皮帽、腰巾为主,颜色比较淳朴大方。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有年龄的长者一般还会要求长袖衬衫的袖长过于手背,以此表示尊崇、德高望重之感。与之区别开来的则是青年男子,他们的着装更为大众化、随意化,所以身上服饰的图案也更多种多样,衣服颜色鲜艳明丽。
三、击石舞的文化解读
宗教与艺术均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们“都是人类深邃的情感启示”。就其关系而言,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渊源、相同的题材和相同的内在体验”,这就是宗教与艺术的统一性。在《尚书·益稷》中也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道出了原始居民们击打石器,模仿各种兽类图腾而舞的形象。由此可见,绿洲艺术复调下的击石舞可能携带着原始图腾信仰的文化基因。所以,击石舞成为了维吾尔族原始先民,原始信仰在民间文化艺术行为活动中具体形象的表达呈现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随着原始舞蹈遗存现象的消亡,众多部分功能也随之更迭,文化属性的阐释也开始由原始功利性向民间世俗性转变。
(一)民间性
西域乐舞是绿洲文化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容缺失的且分子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它对中原部分乐舞的影响也很大。例如,在汉、隋唐时期的宫廷当中,都一度将西域乐舞作为宫廷乐舞的重要组成机制。正是因为宫廷乐舞的发生,才使得各阶级的审美需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以此出发,为了不同人的审美差异需求,相关人员便从民间索取乐舞来源,将民间歌舞吸纳到了宫廷乐舞当中,然后根据不同人的需要将民间歌舞加工、提炼,使之转变成了一种具有娱乐表演性质的宫廷乐舞。所以,我们通过宫廷乐舞的形成过程便可以察觉到,其是由民众所创造、为民众所承载、在民众中所流存的一种乐舞形式,均源自于民间,且深深的烙印着民间性的时代徽号。击石舞的表演以手中四块石头的敲击为特色,其中,双手各持两片石头,将两片石头分别夹于拇指、食指与中指间,仅靠手指的灵活弯曲和手腕处的不断抖动而敲击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并以此来配合表演者面部表情的丰富变化。通过将动作的演绎与舞蹈自身的美感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有趣的审美意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击石舞不仅蕴含了民间文化艺术典型的审美情趣,而且它还是一种寓于生活、融于群众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它由最初的原始性趋向了民间生活,其功能文化的转变亦从功利性过渡到了自娱自乐的表演性。我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并不能因为此功能的转变而避开其历史维度中的这层深刻涵义。总而言之,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饱满、热情洋溢、端正严谨的心态,去探索挖掘此民间文化背后的哲理韵味。
(二)传承性
《击石舞》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流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缩影。在新疆这种多元和谐、底蕴丰富的文化艺术环境之中它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意义。我们把前文所提到的“四块瓦”表演形式与击石舞相比较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表演场域、表演时间、服装打扮以及动态形象等虽有所差异化,但是,其道具的用法、边歌边舞的形式,依然保留着绿洲农耕文化的特点”。如今,从“击石舞”的表演形式当中我们依旧可以观寻到“四块瓦”的溯流沿革过程,可以看到该形式在流变的过程中不断融汇、不断变异、不断传承的文化属性的演变。具有古西域乐舞遗风的击石舞表演传承了“歌、乐、舞”三位一体的交融模式,边歌边舞的表演形式也似乎成为了维吾尔族民间舞蹈中不可忽视的一种艺术概况。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民间舞蹈的狂热喜爱之情已经扎根于血脉之中,无论是地理生态的优渥还是社会文化的雕琢,这一切因素都让民间舞蹈的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击石舞道具的转换便是民间舞蹈不断革新的文化产物。
由上述阐释可知,民间舞蹈的传承性会因时间的更替、地点的改变以及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是,在促进民间舞蹈的发展、升华人们审美的需求和推崇本民族文化的精髓时,其方向与态势是永远不会发生转移的。总之,传承不仅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灵魂、民族发展的根基、人民发展的脉搏,它还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得以延续与创新的生命之纽带。
四、结语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成就了民族舞蹈的华彩乐章。就本论文研究内容而言,我们不仅要广泛的关注多维发展的地域文化,更要聚焦于西域文化环境中的西域艺术。西域绿洲文化下的复调艺术正是基于西域文化这一载体,才可以在剥离母体的庇檐后依旧大放异彩的。因此可以说,西域绿洲文化下的复调艺术的本身就充斥着无限的魅力,无论是从民间到课堂,还是由课堂搬至舞台,它们彼此之间都反映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同一性联系。综上所述,站在多维角度的基础上去探源绿洲艺术复调下的“击石舞”研究就显的十分具有实践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泳舸.释读龟兹壁画形象再现龟兹乐舞姿容[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8(03):9-12.
[2]苗利辉.龟兹燃灯佛授记造像及相关问题的探讨[J].西域研究,2007(03):53-63.
[3]李倩.探析龟兹壁画乐舞与敦煌壁画乐舞的关系[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4年.
[4]苏北海.龟兹千佛洞壁画与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关系[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04):49-69.
[5]戴虎.哈密《黑灯舞》清源[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2年.
[6]张铭.试析当代维吾尔族“顶碗舞”的传承创新[J].艺术研究,2018(02):75-77.
[7]李季莲.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中的舞蹈艺术[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01):6-10.
[8]金秋.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现代阐释[J].中国民族,2008(02):4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