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空间的个人虚拟形象符号构建论文
2024-06-26 11:53:55 来源: 作者:caixiaona
摘要:数字空间是以互联网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为技术基础,涵盖社交媒体、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等诸多层面的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空间。其概念产生与元宇宙构想存在密切关联。“元宇宙”(Metaverse)概念一词最初来源于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通过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虚拟化身(avatar)的形式在一个以虚拟分离方式模拟的、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三维数字虚拟空间中进行社交交往。”根据马修鲍尔给出的定义,元宇宙是一个规模宏大、可交互的、实时渲染的虚拟世界网络,可以被全球无数用户同步持续使用,身
一、数字空间与个人虚拟形象
(一)数字空间的概念
数字空间是以互联网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为技术基础,涵盖社交媒体、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等诸多层面的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空间。其概念产生与元宇宙构想存在密切关联。“元宇宙”(Metaverse)概念一词最初来源于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通过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虚拟化身(avatar)的形式在一个以虚拟分离方式模拟的、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三维数字虚拟空间中进行社交交往。”根据马修鲍尔给出的定义,元宇宙是一个规模宏大、可交互的、实时渲染的虚拟世界网络,可以被全球无数用户同步持续使用,身份、权力、历史、拥有物等信息皆具有无限连续性和连贯性。通过构想中基于VR、AR技术的元宇宙空间,人和场域密切连接,形式上呈现为交互性、社会媒体、流媒体的全面融合。
北京大学陈刚教授基于互联网本质提出了“数字生活空间”概念,认为“媒体”一词无法涵盖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特质。但显然,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出现及区块链、计算机图形学等技术的整合发展以及资本市场商业模式的改变,数字空间早已不单指传统的PC互联网造就的空间,逐渐具有了“虚拟社会系统”的性质。可以说,数字空间处于人类通往元宇宙时代的轨道的中间阶段,数字空间是片段化、实验化的Meta空间,同样追求多样性、身临其境、身份化、社交性、文明感、颂扬人本精神等基本原则。2021年12月,百度发布了数字空间产品“希壤”,其介绍为“以技术为基础,以开放为理念,同客户、开发者、用户一起,打造一个身份认同、经济繁荣、跨越虚拟与现实,永久存续的多人互动虚拟世界”。用户可以在“希壤”中设定多风格类型的个人虚拟形象,并通过基础设定形成角色昵称和定位。(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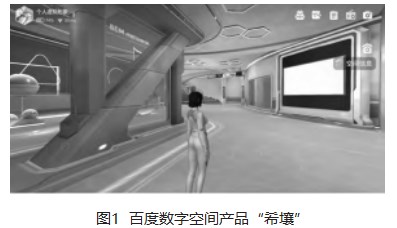
(二)数字空间中个人虚拟形象的概念
“个人虚拟形象”指在网络或其他公共领域,通过有别于真实肖像的个性化视觉效果标识个人身份的一种方式,其形式从实体美术作品到电子化设计等不一而足。在各类数字空间产品中,主要以私有化虚拟数字人的形式存在,同时作为一种数字资产。这种数字化形象可以类似本人外貌特征,也可以无关,通过采用其他拟人化等手法的视觉符号进行替代表达。数字空间中的个人虚拟形象通过提供数字IP确认身份的唯一性,并以人自身的映射方式形成交互端点,展开社交活动。
二、基于数字空间的个人虚拟形象符号构建机制
(一)自我的媒介化与符号化
第一,数字空间中虚拟形象的出现,是电子时代自我媒介化的结果。1964年,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才是文化真正的内容。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媒介形式的改变,不仅是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而且是整个文化模式的改变。文字和机械印刷的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五感的平衡,而数字空间的演进使感官重点再度回归视听。在数字空间中,真实身体的价值被弱化,作为视听对象存在的媒介价值被凸显。虚拟身躯取代自我实在,现实的自我意识部分让位于自觉作为媒介的自我意识。
第二,个人虚拟形象的构建基本依托符号化。数字空间本身即对于真实世界的三维拟像,是人为制造的纯粹意义载体。通过进行数字化编码和增强,使虚拟的建筑、商品等无限趋近甚至超越其原本具有的现实意义。但在数字虚拟形象的概念中,“数字”只是基础手段,“形象”的构建取决于对各种身份符号的创造、使用和再度文本编织。人们完全通过编辑和选择虚拟身体的属性以及外在物品,并对一切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在虚拟社会中重新创生和定位出一个符号自我。
(二)个人虚拟形象与传统社交虚拟形象的符号机制差异
在传统的大众社交媒体(如微信、QQ空间、微博等)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形象”其实并不在场。人们运用头像、签名,以及输出的观点和内容来进行自我表达。无论是基于社会元语言的社交文本撰写还是与生活相关的图片展览,都是相当碎片化、扁平化的符号性人格语言。观者只能通过完形想象实现对客体人格的认知。这些传统社交媒介的信息密度始终偏低,且在信息发出与接受之间存在显著的时、空、表意距离。内容上,语言化的符号系统更倾向于对人格内在属性进行展示,而非外在直观。以上种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留存造成的错误演绎和解释旋涡,最终使得社交形象与真实自我相去甚远。
数字空间中的虚拟形象是整体性、立体化的。
首先,其具备直接可视的外貌,如毛发、骨骼、脸型等。其次,能够运用语言、神态、动作和外在服饰和物品进行自身性格和性别的表达。最后,其具有思想和观点,并以特定的职业、复杂的身份存在于数字空间的具体场域中,与他者进行直接的社会交往。即使存在文本和图片形式的沟通,也建立在外显身体符号的基础上。通过在短时间内传递出大量的信息组合,缩短了传统社交平台的沟通时间。整体的符号互动过程相对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允许他者对自我的形象外观进行凝视和解读,同时也允许自身对形象的捏塑和更改。但是,这种形象的符号化机制带来了表面化社交的风险。更直观的传达,更快速的接触意味着更浅层的关系和更随意的社交筛选过程。
三、数字空间中个人虚拟形象符号构建策略
(一)以多层次的符号语言塑造立体化形象
根据前文探讨,数字空间中的个人虚拟形象符号文本超越了简单的图文,主要通过直观的视听对于人的身体、人格、社会身份等进行表达。这种表达在直观化的同时,引起削弱人际链接、导致关系浅化的危机。为了缓解这种可能的负面效应,个人虚拟形象的构建应力求符号语言的丰富,实现形象立体化。

第一,伴随文本的运用。数字空间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仿真空间,在个人的虚拟形象之外,还存在个人的其他拥有物、不可视的社会网络等关键信息。当这些内容在社会交往中通过可视形式存在,作为个人形象符号的伴随文本一并被接收,即实现形象的进一步丰富和立体。
第二,削减标签化效应。身份标签能够赋予人们在社群中的归属感,加强个人在社会和群体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但是,在时间的纵向来看,个人的形象和自我认知都处于不断地流动变化之中。明显的标签化手法违背现实社交规则,扁平化符号机制从长期而言不利于个人形象的立体构成。
第三,即时性与留存性信息并存。传统社交平台中,个人信息的滞后属性和累积属性对于身份塑造具有一体两面的效果。一方面可能引起误读,一方面却突破了虚拟化身之间即时性交流的弊端。在具体的三维虚拟形象构建中,可采用即时性信息为主,留存性信息为辅的符号系统,丰富人格历史,为长期性符号的存在保留空间。
(二)以多情感的可视化加强社交场域沉浸
数字空间,包括其间的社会形态和社交模式在内,都是现实理想投射的产物。强烈的情感链接是空间构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之一。通过技术手段和社交模式设计,使用户在符号审美中获取身份认同和情感能量,是数字空间社交场域建设的重要课题。
第一,社交情感是个人形象的有机组成,要将不可视的内心情感进行即时呈现,同样只能依托于符号化和情感可视化的手段。除了直接身体符号和文化聚落形成的社群身份认同,还需要对社交过程中的行为、表情进行处理。通过对社交情感信号的增强或放大,形成沉浸式的社交感受。
第二,根据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对于“沉浸”状态的描述,当人们全身心投入某一活动时,会过滤掉所有不相关的干扰,产生一种时空抽离(time distortion)的感觉。高情感沉浸式的社交体验还应对不相关的在场符号进行合理屏蔽,打造纯粹化的社交“里空间”。
四、结语
警惕虚构的符号自我加速生存意义的式微虚拟身份的人格建构,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自我呈现理论)高度相关:将社会喻为舞台,将社会中的人群喻为演员,将生活喻为表演。在数字空间社交中,虚拟人格的构建比现实具有更强的戏剧效果。借助无限庞大的、三维化的符号市场,人们施展着自身的独特性和愿望,获取对于真实自我的慰藉和补偿。然而,符号的大量在场往往意味着意义的式微,虚拟对于时空的占用可能意味着对真实肉体生命的削弱。一方面,深度的表演与深度的造伪一体。当数字空间发展成为现实生活的镜像,虚拟化的生活演进成一场几近随心所欲的创作,造成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的割裂。另一方面,虚拟生存空间生活的拟真带来大量数字快感的同时,也扩展成为人们体验世界的“无限视窗”,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个人在群体中的微小,引起生活意义的丧失。为了消减符号泡沫带来的真实生存意义的式微,在数字空间及虚拟自我形象的构建过程中,除了设计层面的符号机制探讨,还亟须更多社会伦理层面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