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模糊问题研究论文
2024-03-05 09:28:22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持有型犯罪本质上是对我国现行法益的侵害。当前,我国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已存在了多个罪名,且仍存在持续扩张的趋势。但由于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持有型犯罪的条例规定形成周期较短,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存在较多模糊地带,而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多为认定规则欠缺导致的司法认定模糊,或为认定与罪数形态理论不协调导致的司法认定模糊。因此,针对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既要明确认定持有型犯罪的认定规则,又要梳理认定持有型犯罪的罪数形态,以期让最终裁决与司法认定更具法理基础,发挥法律处罚的应有作用。
摘要:持有型犯罪本质上是对我国现行法益的侵害。当前,我国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已存在了多个罪名,且仍存在持续扩张的趋势。但由于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持有型犯罪的条例规定形成周期较短,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存在较多模糊地带,而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多为认定规则欠缺导致的司法认定模糊,或为认定与罪数形态理论不协调导致的司法认定模糊。因此,针对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既要明确认定持有型犯罪的认定规则,又要梳理认定持有型犯罪的罪数形态,以期让最终裁决与司法认定更具法理基础,发挥法律处罚的应有作用。
关键词: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罪数形态;法益侵害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加强风险的前置工作、量化法律的保护意识受到了社会群众的广泛关注。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于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共分化为9大类,如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分布在《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四个分则章节中,为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1]。但在立法层面上,持有型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仍存在较大争议,如行为人的持有是作为或是不作为,还是其他样态的认定均受到了众多法律从业者的深入分析。其中,作为说是指持有行为违反的禁止性规范,而不是命令性规范,如储存、携带等持有表现形式,都是属于作为。而如果说持有是不作为,则是需说明作为的义务内容为什么,即《刑法》规定持有犯时,旨在禁止人们持有特定物品,进而禁止人们利用特定物品侵害他人法律权益,而不是命令持有人上缴特定物品。基于此,本文以总结持有型司法认定模糊问题根本原因为切入点,探讨分析如何从认定规则和罪数形态两个维度阐述该犯罪司法认定,以期从立法考察上和司法认定上做到持有型犯罪认定的明确量化,助力司法认定。
一、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模糊问题的根本原因
持有型犯罪是我国法律从业者以《刑法》为基础,基于《刑法》中规定某类具有共同“持有”特征的犯罪行为所归纳出的概念。正如陈兴良教授在《刑事法评论》中所言,“持有型犯罪是以持有本身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客观基础的一类犯罪。”可见,“持有”是持有型犯罪进行司法认证的重要判定标准。例如,持刀盗窃罪中的盗窃罪和持刀杀人罪中的故意杀人罪,持刀行凶的原因是凶手的行为,而不是持刀。持刀抢劫的原因是犯罪人抢劫造成的犯罪,而不是持刀行为[2]。所以在刑事犯罪中,持有某种物品若仅是其他犯罪中的手段形式,则不构成持有型犯罪,这也是当前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极易走入的误区之一。因此,从认定规则与罪数形态两个维度入手,明确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模糊的主要原因,能够为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认定规则欠缺导致的司法认定模糊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对持有型犯罪的认定较为分散,认定规则欠缺是导致司法认定模糊的原因之一。一方面,针对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较不统一,存在大多情节相同案件的司法认定结果大相径庭的现实情况。例如,同样是持有毒品的案件,若行为人是以火车为交通工具运输毒品,则会被认定为持有毒品,而若行为人是以飞机为交通工具运输毒品,则会认定为运输毒品。可见在司法认定中,在认定过程中,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运输通常被视为一种运输行为,而在一个城市内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或在一个县内从一个乡到另一乡的运输则被视为持有行为,导致同类案件因司法认定的标准不同产生了不同判决结果,且因不同判决结果的惩罚措施并不相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公平性[3];另一方面,在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相对不均衡,在确定行为人的责任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应该部分倒置,行为人应该否认他们拥有的事实并提供证据;另一些学者认为,应以传统的责任划分基础,即仍由检察官应该继续提供证据,确定行为人持有事实的存在,再由行为人对事实阐述。而在现阶段的司法认定工作中,常以第二种举证方式,即由控方进行行为人持有事实的举证,虽然提高了持有型犯罪的诉讼效率,但在责任分配中控方所占责任过多,极易忽视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导致行为人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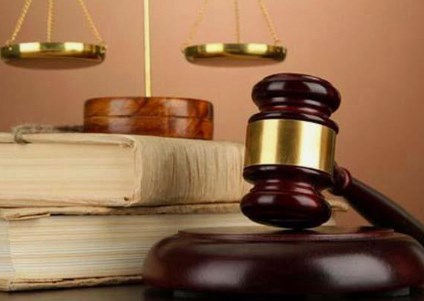
(二)认定与罪数形态理论不协调导致的司法认定模糊
一方面,从持有型犯罪的法律行为上看,通常情况下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是在无法证明持有人物品来源,也不构成与违禁品相关的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做出的法律行为,这也导致了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持有型犯罪中绝大部分属于牵连犯、吸收犯等罪数形态,所以在持有型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各罪数形态的持有性较难判定,认定实践与罪数形态理论并不协调,最终造成司法认定模糊;另一方面,从刑法理论的构成上来看,持有型犯罪的期待可能性是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过程中的争议点,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定罪的主要条件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可预测。然而,由于持有型犯罪与其他关联犯罪具有相同的转变形式,持有行为可能是为犯下其他罪行做准备,也可能是在犯下其他犯罪后的罪行延续,所以犯罪判决的既判力相互冲突导致了持有型犯罪认定与罪数形态理论的不协调,最终造成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模糊[4]。
二、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的优化策略
(一)明确认定持有型犯罪的认定规则
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的优化应从明确该犯罪的认定规则入手。
第一,需明确界定持有型犯罪中对“持有”的性质判定。基于当前刑法的拟定基础,由于持有型犯罪对于“持有”的犯罪认定,认为是兼具了行为人行为和心理状态的故意犯罪形式,并不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典型犯罪行为,所以对“持有”的性质判定可从以下方面出发,确保判定结果的合理性与可行性[5]。一方面,行为人的“持有”应具备行为事实,在不修改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仍然符合持有型犯罪基本的立法目的;另一方面,不同行为人的“占有”行为在犯罪层面上具有高度相似,虚构占有行为不影响犯罪事实的认定,从而解决了占有双重犯罪性质的模糊问题。
第二,需明确持有型犯罪中“持有”的具体性质,为判决提供说理和法理分析。一是应明确行为人“持有”的行为和持续状态,即持有不仅是一种介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第三类行为,更是一类事实状态;二是分析该持有行为所造成的犯罪危害性;三是对犯罪主体进行举证,深入讨论犯罪构成,确保持有型犯罪的司法判定是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而非只是单纯对持有型犯罪进行推断,以此保障行为人的基本人权。例如,在重婚罪认定中,虽然重婚罪是在行为人已知自身婚姻状况下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虽与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相似,即在重婚事实行为制存在的情况下,重婚行为具有非法性,但也因为它不携带具有合法隐私的危险物品,同时重婚行为也不伴随持续的非法状态。造成更为严重的风险,所以重婚罪性质虽与持有型犯罪性质相似,但也仍不足以纳入持有型犯罪的范围中来。
第三,需明确持有型犯罪的犯罪推定。一是从主体方面上来看。因持有型犯罪属于故意的罪过形态,行为人是通过主观上掌握特殊物品,从而构成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在司法认定中,对“持有”状态的证明为发现了持有事实,就为证明了持有事实,即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即为持有型犯罪的主体犯罪构成,所以在后期司法认定工作中,对于持有型犯罪中的主体犯罪认定,不能完全由行为人的供述所界定,而是需通过利用推定方式,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行为人的主观意识进行推定,目的是让持有型犯罪的主观认定和事实认定以法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保证司法认定工作的顺利推进;二是从客观方面上来看,由于持有型犯罪包含的持有行为有多种形式,如携带、藏匿等,所以客观层面上对持有型犯罪的犯罪推定应确保该持有行为不属于其他犯罪的预备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等情况,必须在不构成其他违法犯罪相关罪名的情况下才可认定为持有型犯罪。即客观地持有型犯罪推定为,如果行为人的目的是获取某种特殊物品,或因避免物品暴露而采取的隐藏和转移行为,并且在没有证据表明罪犯构成另一项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则持有该物质应被视为持有型犯罪。
(二)梳理认定持有型犯罪的罪数形态
基于我国当前的法律条文规定,持有型犯罪的危险推定可分为以下三类,即具有人身、健康侵害性的危险持有,如非法持有枪支、持有毒品等;具有财产、经济侵害性的危险持有,如持有假币、持有伪造发票等;具有国家安全利益侵害性的危险持有,如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绝密文件等。可见,持有型犯罪是以人的意识辅之特定物品导向的法益实质损坏,人的主观意识是造成实质伤害发生的关键。例如,非法毒品持有者使用毒品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尽管毒品本身具有危险性,但行为人使用毒品侵害群众人身安全更是源于行为人本身的主观意识。所以,为进一步提高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效果,也应通过梳理认定持有型犯罪的罪数形态入手,在犯罪所延伸的罪数形态上进行实质性判断,明晰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6]。
第一,持有型犯罪与吸收犯的犯罪行为认定。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是持有型犯罪行为的必经阶段、组成部分或最后结果,而被持有型犯罪行为吸收的情况。因此,在司法认定持有型犯罪过程中,应通过认定侵权行为和吸收行为来保护被告的人权。即对罪犯的行为只能评估一次,禁止重复评估,而针对严重罪行应吸收较小的罪行,并从重处罚。例如,当行为人因实施了持有的先前行为导致自身构成了犯罪,但在明确自身已触犯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却仍然对特定进行长期掌控(即持有),此时的持有虽然不在犯罪之后一定发生,但与行为人先前的犯罪行为仍有较大关联,所以依据吸收犯罪的认定原则,针对此持有行为的犯罪应被行为人上一阶段的犯罪行为吸收,确保惩罚是以重罪处之,保障认定的合理合规[7]。
第二,持有型犯罪与牵连犯的犯罪行为认定。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持有型犯罪时,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碰到了其他罪名的情况。所以在司法认定中,从主观角度来看,对行为人的认定只能是故意的,这意味着行为人仍然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有害影响,并且仍然抱有希望或容忍,以此造成的过失心态则不会构成牵连犯罪行。例如,在识别诈骗罪和非法持有信用卡罪时,行为人的非法持有信用卡罪不一定和诈骗罪有关,其处于这两种行为的同一阶段。因此,针对在判定持有型犯罪的牵连犯时,可将提供信用卡的行为人作为诈骗罪的同谋与持有型犯罪行为人,将不同的罪行认定作为评价的参考要素,实现罪责刑的相互适应[8]。
三、结语
持有型犯罪具有对“持有”判定鲜明的特征,已成为我国犯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我国对于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仍存在模糊问题,制约司法行为的正常开展。而造成认定模糊的根本原因主要为对“持有”的认定规则欠缺,以及认定与罪数形态理论不协调。因此,基于对认定模糊的原因分析,本文从认定持有型犯罪的认定规则与认定持有型犯罪的罪数形态两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持有型犯罪司法认定的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从制度入手,平衡不同类型的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用法律拟定的方法再次明确持有型犯罪中构建要点的法律性质,提高持有型犯罪的认定效率,达到立法与司法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姜敏,詹惟凯.论持有型犯罪的性质、正当性根据及其限度[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1):55-66.
[2]兰皓翔,王今朝,原伟民.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1,33(1):10-17.
[3]陈仕炜.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若干问题——以持有型犯罪为视角[J].法制博览,2020(2):58-60.
[4]刘宏沅.非法持有枪支罪出罪路径研究——以赵某华非法持枪案为例[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3(2):33-39.
[5]薛灿.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后实施帮信行为的定性分析[J].法制博览,2022(11):108-110.
[6]黄胜.非法持有、使用假币的行政与刑事责任界限[J].派出所工作,2022(3):74-75.
[7]陈银珠.论我国刑事司法机械化倾向——从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谈起[J].刑法论丛,2020,62(2):107-126.
[8]陈伯礼,顾媛元.在网络空间中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行为的司法认定——基于对16份裁判文书的分析[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0,32(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