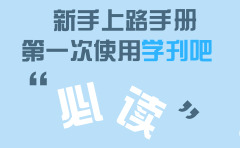论设区的市立法权对国家法制统一的破坏可能性
2019-09-27 16:02:21 来源: 作者:xuekanba
摘要:新修的宪法将立法权主体明确扩充至所有设区的市,再一次激起了人们对于破坏国家法制统一的担忧。经济与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法制化以及二次授权等似乎都在引诱地方滥用立法权。然而实践证明,一方面,我国的法律体系日益完备,地方立法趋于保守;另一方面,适法机关适用地方性法规的积极性并不高。由此,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非但没有对国家法制统一造成破坏,反而在实践中远远没有达到满足地方不同治理需求的初衷。
关键词: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国家法制统一
引言
单一制国家立法权限的纵向划分总是不免引起破坏法制统一的担忧。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尤甚。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主体由“较大的市”扩充至所有“设区的市”的举动,曾无疑将这一担忧激化到顶峰,现如今2018年新修订的《宪法》中又将这一点进行了明确,无疑将会再一次激起质疑的浪潮。然而,此次地方立法权的扩容究竟是否对国家法制统一造成了破坏,不能仅根据固有印象与臆测就妄下定论。在明了国家法制统一内涵的基础上,仔细考虑忧虑的来源,再结合立法实践的效果加以验证事实真假,最终得出结论,这才是一个理性人判断问题该遵循的思路。
一.国家法制统一的内涵
国家法制统一,仅仅六个字,我们就可以解读出如下涵义:国家、法制和统一,即,在一国的语境前提下,国内的所有有效的法律形成一个有内在秩序的统一体。换言之,“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内涵就是,在一国之内,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文件能够形成一个效力等级体系,并且不会自相矛盾”。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将地方所立之法纳入到国家整体法律体系之中。对于这一点,《立法法》以及《宪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之后,我国现如今形成了“中央-省-市”的三级立法模式。中央立法的效力高于地方立法,地方设区的市立法的效力则低于省一级立法的效力。因而,总体上来说,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只是在原有立法层级基础上进行了降级的顺延,并不会破坏原有的秩序。这就表明,国家法制统一是否遭到了破坏,关键不在于立法权的层级分配,而在于设区的市在得到这一立法权之后,其是否会滥用这一权力。对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持质疑观点的学者们,隐忧之处也集中于此。
二.担忧破坏国家法制统一的主要理由
“任何公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而立法权一旦被滥用,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国家法制的统一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现实中的确存在很多诱因。
(一)地方政府急功近利
一方面,地方立法权的扩容意味着地方治理的自由程度进一步加大,刺激了地方政府谋求地方发展的热情。众所周知,地方才是法治、经济等建设的真正舞台。中央的进一步放权,使得地方政府对于治理地方事务的总体把握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其可以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为各自地方的发展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各地方利益最大化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地方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也并不总是一致。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如果急于实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各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就有很大可能会过于注重自己地方的利益,随意立法,打着“地方特色”的幌子,随意突破上位法的边界,破坏国家法制统一。
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曾提出,要把法治建设的成效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来。到如今的十九大这一点也依旧没有改变。这就导致地方立法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难免给人一种:“似乎不谈地方立法,就不关心中国政治;不加快地方立法,就不会有政治前途”的错觉。而法治建设的成效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显现出来的,此时立法数量就成为了一个可量化的显见政绩表象。因此,各地方官员要想在法治建设上面提高自己的政绩考核分数,唯有加快推动地方立法,以希望在立法数量上取胜。由此,进一步刺激了地方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立法人才和立法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过于注重立法数量的结果只能是牺牲立法质量。此时的地方立法就可能偏离满足地方需求的初衷,反而对国家法制统一不利。
(二)部门利益法制化
众所周知,由于“强行政、弱人大”的现实,在我国地方立法的实践中,行政部门几乎垄断起草、主导的话语权,人大常常沦落到为政府行为合法性进行背书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现实,因为并非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参与起草法律的资质,因而传统的部门起草也无可厚非,而且部门起草法规草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单位和个人都无法取代。但是也不能因此认为部门起草就等同于部门利益保护,部门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部门利益存在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可能性,但是部门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利益团体,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不可能有永恒一致的利益。在除了人民利益还有部门利益存在的情形下,作为一个理性人,我想我们“不能过度相信人的忠诚”,盲目认为部门官员都会坚持舍己(部门利益)为人(人民利益)。以前的立法经验也对此进行了印证,实践中确实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而且我们也清楚,这一现象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可能会愈发明显。此外,在各地方已经大量存在“红头文件”等软性规则的现实下,此次将立法权进一步下放,是否等同于给了地方将软规则合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机会,进一步助长了部门利益法制化呢?
(三)“二次授权”泛滥
从《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主体由49个较大的市扩充到284个设区的市,到今年新修订的《宪法》对这一举动进行了宪法上的确认,历时已有3年。有些学者提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确实很多地方存在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专职委员短期内无法就位的情况,那么立法质量的担忧也就不是空穴来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曾提出的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似乎为此担忧提供了解决方向。面对日益繁重的立法任务,各地相继开启了委托“第三方”主体参与立法的探索与尝试,借以弥补立法机关自身立法资源的不足。但同样这也带来具体操作中,“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程度范围等等问题,以及“第三方”带有的理想化倾向,可能导致理论上看似中立的立法方案,实际暗藏不平等对待的危险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外,地方政府在尝到第三方参与的甜头后,可能产生推卸责任的怠懒心态,过于依赖第三方,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影响地方立法的权威。这可能导致“轻则沦为一场‘政治秀’,使立法部门推卸责任、转嫁负担;重则使立法部门打着购买服务的幌子变相扩大自身权力,产生新的‘权力寻租’,直至权钱交易,滋生‘立法腐败’”。
以上对于设区的市滥用立法权破坏国家法制统一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同时,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确实存在,这一点不能因此而被否定,就如同“反腐败的必要性是以国家公职人员存在的必要性为前提的,不能因为反腐败,最终否定国家权力的存在”一样。关键还是在于实践的具体情况,仅在理论层面的设想与担忧如果不与实践相结合的话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三.实践中的地方立法情况及成因
无论质疑者对于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有多少疑虑,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实践中地方立法的情况
通过对一些学者对立法实践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虽各学者结论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我国自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以来,地方立法有紧跟上位法的保守倾向。
一方面,地方性法规的数量虽较之前的确有所增加,但也并未达到质疑者们预期的增长程度,并没有出现不受控制的全面爆发式增长的局面,反而仅有少数方面立法较为活跃,且集中于“补充、细化和重复上位法”的规定,突破上位法创新的情形所占比率极小。
另一方面,适法机关对地方性法规的适用比率,相对于适用上位法的比率来说,也相对较低,并且多集中于具有实用性的条款,以山东省为例,其适用较多的地方立法为:《山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
(二)成因
1.我国地方立法趋于保守主要原因:
(1)法律体系完备,地方立法空间小
在2014年8月下旬和12月下旬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的两次审议中,刘政奎委员就曾对此提出过担忧:“现在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也越来越细化,地方立法的空间已经不大。”这确实是事实,在今天完备的法律体系下,上位法的规定越来越详尽,虽说仍然存在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需求,但是不可否认,下位法的活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到了上位法的限缩,毕竟下位法不能同上位法相抵触。
(2)立法权限范围及审批限制
除了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以外,《宪法》与《立法法》也同时将设区的市的立法范围限制在了“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进一步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进行了限制。此外,设区的市的立法要想生效必须先经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审批方可,如此,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的边界就被进一步限缩了。
(3)保守审慎的立法态度与习惯
一方面,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使得地方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因而地方人大的立法态度惯于审慎。另一方面,我国科层制强于民主制的特征是难以避免的现实,虽然人大机构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较为超脱,但其仍受现行干部考评体制制约。因此,与其他地方政府官员一样,为防范仕途风险,人大官员同样认同“不出事逻辑”。此外,由于我国存在长期的封建君主“言出法随”的历史,集权思想遗留较重,地方习惯于作为中央代理人的形象存在,因而地方立法潜在地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
2.地方性法规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
(1)缺乏正式的衔接机制
沈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在2016年发表的《浅谈地方性法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就曾指出地方性法规的适用存在“知之不多,适用更少”的问题。一方面,目前实践中人大与适法机关之间衔接不到位。常见法规颁布实施后,经过新闻发布会,相关机关派员参加,领回相关文件和材料,再往后就没有下文了。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并没有对上位法进行大的突破创新,在上位法基本可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广大适法人员潜意识中会形成“路径依赖”倾向,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比较学习新的地方性法规条文。
(2)适用的地域性明显
地方立法的适用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以司法机关为例,一方面,管辖更大地域范围的法院并不倾向适用辖区内某个地方的“土规定”,地方立法对“上级法院”缺乏约束力,从而引发“适用不出本地”的尴尬。另一方面,我国两审终审制之下,法院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上级法院更倾向于适用上位法的情况下,下级法院的法官们对待案子,不仅在裁判上更加审慎,而且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更加倾向于适用统一性更强的上位法,以减少因适用法律错误造成的发回重审或改判的几率。毕竟,相较于更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下位法,上位法的条文至少在上级法院能够减少质疑。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设区的市在实践中的立法情况,似乎完全相悖于质疑者所担忧的方向,不仅体现不出对国家法制统一的破坏,更存在地方立法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并未能达到“适应地方的实际需要”的立法初衷。由此,我们不仅不用过于担忧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会对国家法制统一造成破坏,反而应当主张进一步放开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限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一个良好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人民造福,而不在于不顾人民的疾苦而建立一定的秩序”,“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地方才是法治建设的真正舞台,这就要求赋予地方更大的自由权,尤其是立法权,充分调动地方自治的积极性。当然具体限度如何安排,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程庆栋.论设区的市的立法权:从权限范围与权力行使[J].政治与法律.2015(8).
[2] 葛洪义.关于我国地方立法的若干认识问题[J].地方立法研究.2017(1).
[3] 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合宪性与宪法发展[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2).
[4] 庞凌.依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法学研究.2015(4).
[5] 王书娟.样态与进路:第三方参与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J].江淮论坛,2016(4).
[6] 王仰文.限量放权后“模仿式”地方立法困局的破解之道[J].北方法学,2017(3).
[7] 郑泰安、郑文睿.地方立法需求与社会经济变迁[J].法学,2017(2).
[8] 周伟.论设区的市立法权收与放的统一[J].法学,2017(7).
[9]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