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人身权的可转让性探讨论文
2023-05-15 09:46:07 来源: 作者:xiaodi
摘要: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理论最复杂的一个分支——著作权,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著作人身权能否随同著作财产权一道转让的问题。随着近年来著作权产业的兴盛和大数据交易时代的到来,关于著作人身权转让的司法案件和社会实践问题频频发生,著作人身权不可转让的理论和相关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变迁。
摘要: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理论最复杂的一个分支——著作权,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著作人身权能否随同著作财产权一道转让的问题。随着近年来著作权产业的兴盛和大数据交易时代的到来,关于著作人身权转让的司法案件和社会实践问题频频发生,著作人身权不可转让的理论和相关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著作人身权;可转让性;转让登记制度
在20世纪初期之前,知识产权法中并没有制定有关著作人的人身权制度。而对于我国,直到20世纪末期,才规定了此内容。但是,随着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其根本问题在于著作人身权能否转让。
一、著作人身权的基本理论
从历史之轮的辙痕看,早期的一些国家在开始对著作权立法时,都没有制定创作人的人身权制度。[1]关于著作人身权的理论直到20世纪初期才逐渐发展,目前在世界国家立法中存在着三种理论,一是美英理论,特别突出创作人的财产利益;二是德国理论,特别重视创作人自身的人身内容;三是法国理论,采取的方法是二者兼顾,同时规定了创作人的人身内容和财产内容。[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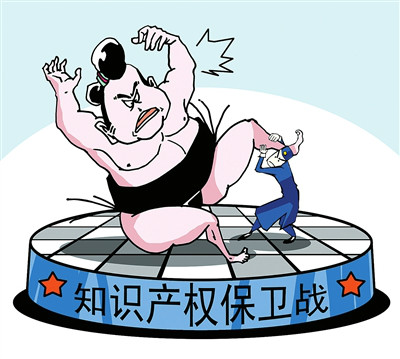
(一)著作人身权的涵义
首先,我们应知道创作品是创作者个人思想内容的流露。创作者在独创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活阅历、个人素养、观察角度甚至个人的习惯、性格无形中增添到创作品之中,使人们不单单欣赏思想载体的外表,更体会到创作品背后的思想流露。我国权威学者吴汉东教授将其界定为:创作人基于其创作品所享有的各类与人身相联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3]
(二)著作人身权的特征
通常观点指出,创作人的人身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创作人的人身权客体是创作品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二是创作人的人身权主体为创作作品的创作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三是创作人的人身权利开始的时间始于创作者撰述完成之时;四是就创作人的权利存续而言,创作人能与其客体发生分离;五是创作人的人身内容与财产内容有着密切联系。
二、著作人身权转让问题的出现及产生的原因
(一)著作人身权转让的立法现状
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认可著作人的人身权可以转移,但也并未否认其可以转移。加之上述分析,著作人身权不可转移的理论不但没有法理依据,现行法也没有给予有力支持,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打破对传统观念的“信仰”,不妨大胆探索其可转让性。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内容,对于创作者而言,由单位安排其自己在职务中撰写创作的文章,创作者可以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其他义务和权利则应当归于单位,这便导致创作权的主体与创作者发生了分离。不仅如此,根据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尽管该条并未表明此处的著作权仅指财产权利,但根据体系解释原则,其应包含创作者的人身权。此外,既然法律允许了委托作品可以商定其归属,那为何却只允许创作的财产内容可以转移,而不提及其他由创作人独创并转让其包括人身权利在内的创作品,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究竟为何?
(二)著作人身权转让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笔者拜读众多学者所著论文及期刊图书之后,发现普遍都提及创作者的人身权与民法中人身权利的区别,以及现行立法状况对此问题有着差异性的表述。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了以下原因:著作人身权的分类不恰当;署名权的概念表述不确凿;保留修改权多余,应将其删去等。
笔者认为,关于著作人的人身权转让问题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深刻认识且了解到法的内容局限性,以及认识到当前法律实施时所要求的人力资源、物质基础等现状。[4]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转让问题之辨析
(一)发表权的转让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为发表权下的定义是: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而对于其性质,目前有两种理论,一是:一元论,只具有人身单属性;二是:二元论,就是再增加一个财产属性。笔者赞同二元论学说,理由如下。
1.发表权的性质分析
首先,创作者可以决定是否将其创作品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以怎样方式公开。其次,创作者的作品一经披露,无论该作品的内容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社会对此做出的评价完全指向作者自身,对创作人的名誉、荣誉,甚至人身都会带来很大的效果。因此,发表权倒映着人身权。因此,发表权也可能附有人格利益。例如1997年发生的“钱钟书书信案”,因为书信的发表会夹杂着创作者的隐私,而隐私则是人格利益的内容。因此,发表权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身权利性质。
学者孙国瑞指出创作者的财产权应包含着发表的权利,因为发表是使用、利用行为。[5]另有学者张革新也表明,尽管发表的权利是一项创作者的人身权,但利用其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6]
2.发表权的可转让性探讨
在上述中,笔者已经论及发表权的性质,根据于此,笔者认同发表权可以转让。首先,发表权利的使用肯定要波及创作者财产权利使用。在商业领域中,没有发表权利的转移,其创作的内容是没有利用价值的。其次,针对尚未公开的作品,如果创作者将其财产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对于继受人而言,其之后要想再行使创作品的权利,都必须经原创作人的认可。这既无必要,也不合理。
(二)署名权的转让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对署名权的定义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但有学者主张署名应是指明创作者身份的一种资格。
1.署名权的性质分析
署名权是根据创作者独创的客观事实,其才有资格在创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不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其创造出的创作品就不能标为创作者的身份,更不能在创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否则,公序良俗秩序岌岌可危。因此,署名的权利应该是创作者基于其创作的行为而产生的要求其他人认可其对该创作品独创资格的一种权利。
2.署名权的不可转让性探讨
关于署名权的不可转让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由于署名权附有强烈的人身性,它一是表明对作者劳动创造的一种认同;二是作者会由此而产生社会评价和社会声望。[7]其次,署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众的购买需求,名人的作品往往要比不知名作者的作品更加容易出售。最后,值得反思的是,学术界长期滋生着请他人代写学术论文的现象,如果允许署名的权利能够转让,那将间接鼓励这种不良行为。
需要关注的是《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内容:允许创作者转移个人署名的权利。这是因为我国立法者基于计算机软件具有工具性,软件产业的发展需要程序员自由地利用现有的软件,而过度地保护作者的权利将抑制这一领域的发展。
3.特殊情况下署名权的转让
这就牵涉到作品执笔人的问题。《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内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内容:作品的执笔人并不等同于作者。另外,对于该司法解释的第十三条所说的报告到底是指什么类别的报告,该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说明。笔者认为,应将学术研究文章排除在外,因为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枪手”代笔的科研腐败行为,净化学术环境。
(三)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地转让问题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修改作品之权利,即创作人享有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第十条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利,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1.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性质
创作者与其创作品之间具有天然的人身联系,但这两项权利也并非传统内容上的人身权。因为我国法律允许修改的权利可以转移给他人行使,这就为创作者的修改权利打开一道财产之门。
2.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的联系与区别
修改权利是创作者积极利用自己权利的表现形式,属于单纯的行使权,而保护作品完整权利应理解为是一种不允许他人恶意改动创作品的权利。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相对于区别,其两者之间的联系值得学者研究。因为这两项权利好似一枚铜钱的正反面。正面是创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原创作品;反面是创作者有权阻拦他人改动或污蔑自己的原创作品。
3.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可转让性探讨首先,转移这两项权利在学术理论上的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上文所述的两项权利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身权利,并且创作者基于创作后的创作品可以产生财产内容。其次,在创作者将其创作的财产权转移给继受人的情况下,创作者便不再有任何利用创作品的权利。当受让人在利用创作品的时候,一方面针对创作品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判断是否对创作品进行改动。再者,根据创作品的特性,其往往是在他人创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而任何再加工毫无例外要对原创作品进行变动。如果这两项人身权利不允许被转移,则创作者就可以反对对其原创作品任何方式的变动,这肯定对其他创作者进行再改编带来消极影响。
四、我国著作人身权可转让的立法完善建议
(一)修正著作人身权中自相矛盾的制度
在上文论述的立法现状中,人身的权利与其个体能否分开的层面依然有着理论上和立法上的冲突。笔者认为:一方面优化立法技巧,另一方面可以针对矛盾的法律条文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二)对著作人身权合理转让加以限制
首先,立法者要制定出合理转让的范围。有学者指出这一点可以参考《美国反垄断法》的做法,即合理的原则。在这里合理是指某一商业行为给国家、社会、公民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是合理的。但笔者认为如何评估转移行为带来的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岂不是又要耗费很多精力。况且能否确定带来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利益,还需要时间上的验证。因此,笔者认为借鉴这一做法不合适。那么要怎样制定合理的转让范围,笔者认为最核心是约束转让行为不能误导公众,包括不能以署名的方式误导、不能以内容的方式误导。在此基础上,再扩展其他要求。
其次,立法者要明确规定不合理转让的法律责任。但是,除了相关责任,还要制定怎样能清除不合理转让的消极现象。举个简单例子,在胡某海诉刘某旋一案,虽然法院判决论文的署名权归原告胡某海,被告不得在论文上署名,但法院驳回了原告请求取消被告正教授职位的诉讼请求,这就遗留了一个小问题:没有正教授资质的被告,在判决之后依然有正教授的名位。所以,笔者认为在规定的法律责任之后可以加上这么一条:人民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的时候,经原告申请,发现相关机构的做法不合法或者不适当的,可以向该机构发出说明。
(三)设立著作人身权转让登记制度
比照着物权的变动方式,我们可以设立一套著作人的人身权利发生变动的制度,使他人也可以查询到变动的状况。
首先,要确立统一的转让登记机关。登记部门应该由特定的行政机构来进行负责。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转让登记的权威,也可以使得转让具有一致性和规范性。另外关于在何地设置登记机关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初步选择几个试点中心,一方面设置机构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这可以为以后登记机关的普及积累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设立试点机构可以暂时缓解现实中的矛盾。
其次,确定自愿登记和强制登记的规章。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是自愿登记原则。然而,赞同自愿的登记方式的学者强调,强制登记的方式虽然可以清除一部分违法行为,但如果这样强制要求创作者转让都进行登记,那么带来的效果不一定最佳。对此,笔者认为应以自愿性登记方式为主导,强制性登记方式为辅之。在立法中扩大自愿登记的范围,对发表的权利转让可以采用自愿登记原则,而对于修改的权利和保护作品完整的权利应当采用强制登记原则。
再次,在效力上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因为若采取登记生效主义,著作人身权转让时,双方当事人并不能立即办理登记手续,则合同便不能生效,这将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交易手续的增长。
最后,建立统一的转让登记数字化平台。利用互联网与相关技术的发展,并且利用现代计算机的技术、电子登记方式的平台、信息化数据的处理等手段,制作出一套转让登记的电子查询系统,形成“查询—转让—登记”一体化综合数字化平台。
参考文献
[1]吴汉东.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51,272,324.
[2]任燕.论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完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7(5):90-97.
[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70-71.
[4]张文显.法理学[M].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70-80.
[5]孙国瑞.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70-80.
[6]张革新.现代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61-64.
[7]庞芳.著作人身权转让问题研究[D].广州:广东财经大学,2014:52-53.










